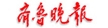|
|
- 2012年04月10日
来源:齐鲁晚报
-
 【PDF版】 【PDF版】
|
|
|
|
|
□王丹枫
十年前,来到这座城市时,于寻常巷陌间是可以轻易看到苔藓的。而现在,寻寻觅觅,再无踪影,“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之景恐怕只能在古诗词中悦人眼目了。
日复一日,机器的轰鸣就像一匹匹脱缰的野马,疯狂地深入城市的经度和纬度,“哒哒”的马蹄声,急促而慌乱,昨日的民间小巷,今日已被“人间怪物”侵犯,没有了鸡犬相闻,没有了家长里短,石板路上斑斑驳驳的苔藓早已被铲除或者被掩埋。旧人散场,新人进入,一股陌生的冷艳气息开始在周遭复制、弥漫,催生出一枝枝悲观主义的花朵,晨昏日暮编织的繁华外衣下没有风流,而“所谓风流,就是不忘露珠的寂静之味”。
缅怀一座城池,最好的线路就是沿着记忆的轨道一路往回寻找。在我人生的履历中,第一次以漂泊者的身份亲近这座城市时,我小心翼翼,没有鸿鹄之志,只求像匍匐在胡同砖墙上的苔藓,静若处子般隐秘生长。
那个时候,物价不高,房租不贵,我租住在鸡犬相闻的胡同里。日久天长,胡同里的一些本地人俨然忘记了我租客的身份,见到我像见到了熟人老远就打招呼,有时候我也忘记了我是个外来者,甚至一度误认为我的童年、少年都是在这里耍玩的。这里有我熟悉的人间草木,有我熟悉的家长里短,就连故乡处处可见的毫不起眼的苔藓,胡同里也能够天天瞅见。光阴流转,苔藓宛如岁月的皮肤,在泛旧的砖墙上一片一片蔓延。也不知哪一天,胡同里到处写满了大大的“拆”字,就连苔藓密布的砖墙上也盖上了惨白的“拆”。
不在其中不知其苦,不离其形不知其老。我曾经不止一次来到这被机器轰鸣主宰的胡同,这里已是热火朝天、烟尘滚滚。相信,我曾经的房东,还有那些大叔大婶也曾回来过吧。回到某一天,曾经的胡同少年坐在老爸的自行车上,去几站地之外的公共浴池洗澡。回到某一天,高高的烟囱黑烟滚滚,城市炼钢厂车间热火朝天,师傅们满是笑颜。那是昨天,有了他们,这座城市才有今天,他们用青春换了一座城池。这里曾经人声鼎沸,曾经有人大声吆喝叫卖糖葫芦,曾经的青砖墙上爬满了莽莽苍苍的绿色苔藓……是的,曾经,这里是“民间”的代名词,曾经……只是曾经,若过眼烟云,如今,它就像一个落魄的贵族,当年的神韵纷纷零落在尘埃里,苔藓软酥酥的况味只属于过去与记忆。
大地上的苔藓越来越少了,到处是人的潮水、人的声浪、人的侵入、人的劫掠。就在我为极易被人忽略的苔藓布道时,游历欧洲后归来的一位老友说,这次他在法国里昂的一个中世纪石头城里逛得不亦乐乎。起初进入时,乍一看还以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的乡村,斑驳旧旧的东西流淌着时光的矜贵气质,城墙和脚下的鹅卵石太有岁月感了,就连一座座石屋外吊着的盏盏路灯,也不知有多少年历史了,不知为多少人在夜里静静点亮。逛到夕阳西下,光线透过重重叠叠的枝丫,在苍绿的苔藓上留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仿若闯进了王维《鹿柴》中“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意境里。
作家郁达夫说,“最可爱的城市兼有乡村和城市的面貌。”而现实是,城市在同化,民间在消失,田园在萎缩,山水在日益脱去它天然的风骨和神韵。我们的家园在背离“可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难怪成都诗人万复不无悲怆地大声呐喊:“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让我荣耀一生。”真不忍心看到,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G城》描绘的景象就是我们城池的寓言:
在G城,你会有数不清的钥匙,但却找不到一扇门。
在这个城市,生命不是人俯瞰万象的顶峰,而是人赖以藏身的隧洞。
G城用死去的人们制造其现在,用没有“现在”的词语制造其未来。
在这个城市,时光行进着,犹如苔藓生长在一堵叫做“永恒”的墙上。
在这个城市,树木的梢头戴着钢盔,每一颗果实里都有一颗子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