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2年01月07日
作者:
-
 【PDF版】 【PDF版】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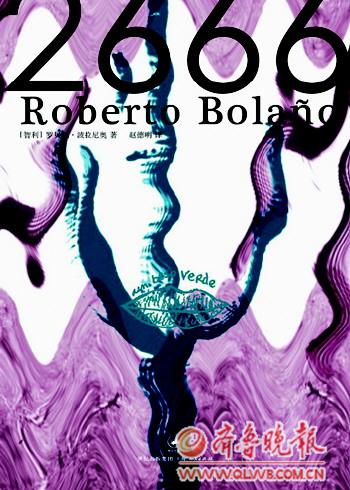 | 《2666》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出版 |
|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史上,都会有一些风云际会、大师辈出的“巅峰世代”,比方说西班牙的二七一代、俄罗斯的白银时代等等,这些“巅峰世代”往往会过度透支一片土地上的文学元气,导致其文学后裔们成为文学创造力相对匮乏的“弱世代”。就西班牙语美洲而言,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两个耀眼的“巅峰世代”(拉美先锋派和所谓“爆炸一代”)极为罕见地连续喷发,在释放出巨大的文学影响力的同时,也让后辈的西班牙语美洲作家不得不置身于一个漫长的文学“弱世代”。
随着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作品,特别是他最重要的作品《2666》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断言,至少在波拉尼奥这个独特的个体身上,宿命般的“弱世代”气场终于消除了。
在波拉尼奥50岁的短暂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像《荒野侦探》、《2666》里的各种江湖奇男子一样过着自我放逐式的盲流生活,在智利、墨西哥与欧洲国家之间,在宅男般的阅读和猛男般的寻衅滋事之间,在蟑螂一样卑微的生存条件和星空一样盛大的写作格局之间穿梭不已。他热爱阅读谱系庞杂的博尔赫斯,但他读的书基本上都是偷来的;他激赏胡里奥·科塔萨尔令现实眩晕化的文学活力,但他比酷爱拳击的科塔萨尔更加好斗。年轻时,他对已是世界级诗歌大佬的帕斯不屑一顾、大加鞭挞,后来又嘲讽文学父辈们的魔幻现实主义“臭气熏天”,讥刺加西亚·马尔克斯“热衷于和如此多的总统和大主教深度搭讪”。他极其鄙视有“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称的智利文坛大姐大伊莎贝尔·阿连德,公开宣称她“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是个商业写手”,被激怒的伊莎贝尔·阿连德也以毒舌相报,在波拉尼奥病危之时毫无怜悯之心地说,就连死亡也不会把他变成一个好人。
波拉尼奥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为了改善窘迫的生计,以惊人的加速度写下了十部长篇小说和三部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是把他推送至全球重量级作家地位的大功率引擎,但不容忽视的是,他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诗人。在《2666》的创作笔记中,波拉尼奥提到这部书的叙述者是诗人阿图罗·贝拉诺,这个阿图罗·贝拉诺也是《荒野侦探》的主人公之一,更是波拉尼奥本人的投射:贝拉诺是对波拉尼奥的改写,阿图罗则是波拉尼奥迷恋的现代诗歌鼻祖之一阿尔蒂尔·兰波的法文名字的西语转写。
波拉尼奥在《2666》中夹带了很多与诗歌相关的私货。他借一个爱读特拉克尔的打酱油学生之口说“只有诗歌还没有被污染,只有诗歌还在商业之外……只有诗歌——当然不是所有的诗歌,是健康食品,不是臭狗屎”。小说中的大学教授阿玛尔菲塔诺一直着迷于一本叫做《几何学遗嘱》的神秘著作,这本书被设定是一个数学家诗人写的,不知波拉尼奥是不是在以此向他青年时代的偶像、“反诗”的倡导者、智利数学家诗人尼卡诺尔·帕拉致敬。
理解波拉尼奥的诗人身份对于阅读《2666》来说更大的意义在于,这部小说的叙述策动力和展开方式其实和波拉尼奥的诗歌理想大有关系。波拉尼奥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和他文学上的“好基友”马里奥·圣地亚哥(也就是《荒野侦探》里的乌利塞斯·利马)发起了一个名为“现实以下主义”的诗歌运动,试图以墨西哥化的达达主义精神重新激活法国超现实主义。在他执笔的《现实以下主义者第一宣言》中,波拉尼奥写道:“真正的诗人必须持续不断地放弃,(他的关注点)从不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多时间,要像游击队战士一样、像不明飞行物一样、像终身监禁的囚徒游移不定的眼睛一样。”回过头来看《2666》,它那蛛网般不断延伸的叙事和繁复接驳的语言,正是他的“现实以下主义”诗歌诉求在小说中的加强版再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