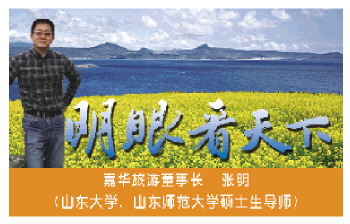云深不知处(七)
2014年04月0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爸爸,看,那里有个葫芦!”儿子的童声打断了导游的讲解。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在远处的山头上,绿色掩映中一只巨大的黄色的葫芦,像是迎宾,静静地立在那儿。葫芦的下面,群山环抱中,有一片相对平缓的洼地,收获后的梯田泛着水光。一个不大的村寨依山而建。灰黑色的屋顶,街道依稀可辨,这就是传说中的老达保村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诗句很自然地在记忆中流出。下车徒步而行,路边是开得火红的花,大簇大簇的,像一群群热情的少女,透着青春,透着活力。
终于见到李娜倮了,导游小邓把李娜倮请到我面前。李娜倮,三十来岁,个子不高,略显丰满,着一身鲜艳的拉祜族服饰。端庄的脸庞上带着高原红,一双大眼睛透着友好、朴实,甚至带点羞涩。娜倮的普通话说得不太标准,但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那份好客的诚意。我们在一株盛开着白花的树下合影留念,鲜艳的服饰,洁白的花朵,和我们身后的青山绿树融为了一体。
中午用餐安排在李娜倮家。一个两层的木制阁楼,一层客厅是客人用餐的地方。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娜倮去全国各地演出及参加十八大时的照片,还有一些明星来老达保村的留影。没有现代化的装修、家具,看得出娜倮家庭并不富裕。家里的财物,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外,就是吉他和芦笙等乐器。可口的饭菜很快端上来了,先是娜倮的父亲李石开带着几个男性村民弹着吉他给我们敬酒。李石开,那个三十多年前,卖猪换回吉他的年青人,如今已经六十来岁。皮肤黧黑,不笑不说话,精神矍铄,充满活力,像个小伙子。唱完歌还给我们解释,模仿动物又跳又叫,很是幽默。再是娜倮带着女人们给我们敬酒,娜倮的儿子,四五岁的小家伙打起了腰鼓伴奏。主人们带头喝酒,满满一大杯。欢快的吉他演奏,快乐的民族演唱,热烈的宴会气氛,让我们这些远方的客人不喝多很难!
用完中餐,我们欣赏老达保村《快乐拉祜》的演出。民族风格的舞台是近期搭建的,算是老达保村最好的建筑了。天公作美,天空湛蓝,艳阳高照,空气清新。平时的庄稼汉、村妇们,换上节日的盛装轮番登场,他们中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四五岁的孩子。《快乐拉祜》、《打猎舞》、《芦笙恋歌》……村民们唱起来跳起来……上百人的演员队伍,人数大大超过观众。天气有些炎热,演员们的热情更是高涨。每一个舞蹈,每一首歌曲都表演得那么的认真投入。“拉祜”一词中的“拉”为虎,“祜”为将肉烤香的意思。拉祜族被称为“猎虎的民族”。拉祜族源于甘肃、青海一带的古羌人,早期过着游牧生活。后来由于战乱逐渐南迁,最终定居在澜沧江流域。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不发达,但天性快乐。“因为简单,所以快乐;因为纯朴善良,所以老天眷恋着生活在澜沧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吉他弹起来,芦笙吹起来,舞蹈跳起来,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九霄云外,欢快的乐曲在群山之间回荡。这个经济上贫穷的民族,用他们的音乐舞蹈天赋,用他们骨子里面的乐观,带给自己和他人无穷的快乐。他们看似一无所有,他们却又无比富足。忽然想起陆游的《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你没看得风景/像山花一样多/还有多少思念的河/你留下的情/像火塘燃烧着/还有好多酒没喝/最盼的就是你再来/要多快乐有多快乐/舍不得吆舍不得/我实在舍不得……”送别的歌曲唱起来了,上百人的队伍为我们送行,客人们抹着眼泪依依不舍。别了李石开,别了李娜倮,别了老达保村……
下飞机回济南的路上,我问画家马子恺先生普洱哪里好,马先生起先回答:“普洱的空气好、风景好,是'妙曼普洱,养生天堂。”但不久马先生即补充道:“普洱真正的好是它能打动人心,是它的人情之美。美景可以寻找,而真情难以复制,其它地方养眼,而普洱是养心啊。”听着马先生发自内心的感叹,我忽然想起唐代贾岛的诗句:“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普洱,但愿你依旧能保留本质,给我们以美好的记忆;普洱,但愿你永远留存在人们的心中,在这个物欲喧嚣的时代,给我们以宁静,养护好我们的心灵……普洱,云深不知处……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