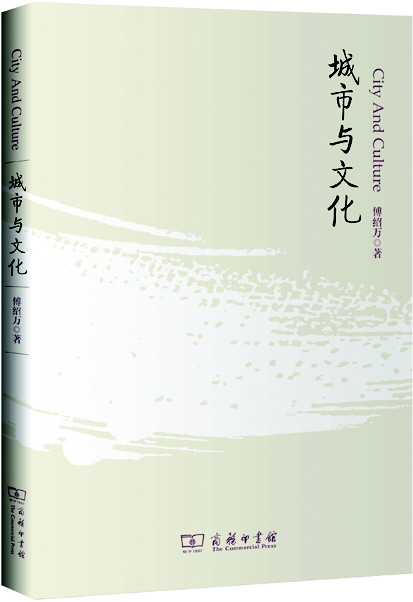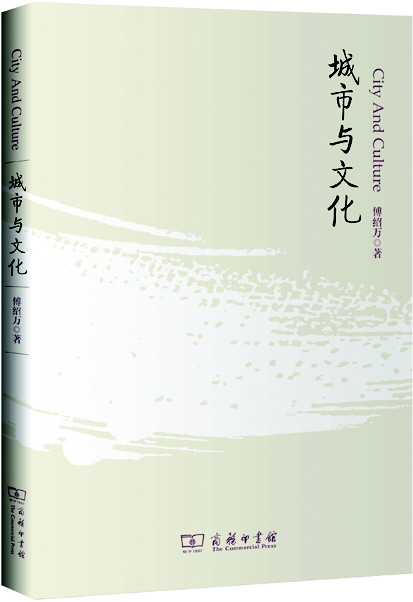
《城市与文化》
傅绍万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年6月出版
我们在加速城市化的同时,稍不小心就会加速摧毁最为珍贵的东西,即历史和记忆,斩断了文化的根性。
《城市与文化》的作者在书中抓住了一个关键词即“文化”,实在是切中要害之论。这里的“文化”并非仅指几处保存下来的古迹如老建筑之类,而是深涵了一方土地所产生的全部独特内容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迥然不同的气质。于是这种感叹就显出了深远的忧思。
书中不止一次谈到了城市的“现代疾患”。实在的情形是,越是现代大都市越是不适宜于人的居住。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实际情形是,城市人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摆脱自己的城市,尽快逃离。
关注人类的现代生存境遇,就不能不更多地关心我们的城市。这里集荣耀与痛疚于一身,复杂难言,对于许多人来说,简直是怀着怕和爱的矛盾心情。我手里的这本《城市与文化》,就是这种心情的映照和凸显。作者游走四方,视野开阔,感受良多,思虑深沉,少有泛泛发言,多是对比探究。他在城与乡、市与野、大陆与域外、现代与传统这诸多因素与语境中,驰走和驻足,留下了生动而朴实的思想印迹。
怎样经营一座美好的城市,怎样让人生活在一座幸福的城市,这始终是作者思考的核心,也是极朴素、极切近的大问题。比如,在更开阔的视野之下,我们可以从历史悠久的欧洲城市中看到什么?作者看到的是安静与葱绿,是传统的持守,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文化流脉的绵绵不绝。谈到国内新兴的大小城市,则是欣喜和遗憾并存,感叹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速度之快令人惊异,同时一切又太过相似:千篇一律,实在缺乏个性和想象力。
我们在加速城市化的同时,稍不小心就会加速摧毁最为珍贵的东西,即历史和记忆,斩断了文化的根性。
作者在书中抓住了一个关键词即“文化”,实在是切中要害之论。这里的“文化”并非仅指几处保存下来的古迹如老建筑之类,而是深涵了一方土地所产生的全部独特内容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迥然不同的气质。于是这种感叹就显出了深远的忧思。
书中不止一次谈到了城市的“现代疾患”。实在的情形是,越是现代大都市越是不适宜于人的居住。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实际情形是,城市人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摆脱自己的城市,尽快逃离——全部逃离或部分逃离。只要能够逃开,具备这个条件的,就是人生一大幸事。弄到最后,大约只会剩下没有办法的老百姓了。结果只能是他们在城里苦熬。
那些忘情地赞扬城市的城里人,大半是居住在特殊小区里的人,比如是一处有草坪、有大树还有门卫的大院里。还有一部分虽然也在熬着,却从心里喜欢城市的,那就是因为一些极特殊的个人理由了,比如特殊的癖好之类。现代人陷入的一个最可怕的困境,就是不得不居于自己亲手创造的一个怪物的体内——这是一个急剧繁衍的大都市,这里空气污浊,噪音刺耳,交通堵塞,食物陈旧,人流拥挤,已经没法体面地生活,却又一时离不开。人自己最后成了一座城市的奴隶,而不是主人。
医治城市顽症是世界性的问题。当今的世界上,几乎所有致命的错误都发生在大城市里。解决城市问题,其实就是解决人类的未来。一些棘手的现代伦理问题,也大都发生在城市里。由于缺少大自然的抚慰,城市的确集中了相当数量的现代精神疾患和生理疾患。
现在每到一个城市,给人的一个强烈感觉,就是再也不能这样了,这里需要彻底改变,我们不能再这样过下去。对于城市建设,要下一剂猛药,要有一种革命化的思维。不能仅仅是改良,而是要彻底改变它:它的节奏,它的道路,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气味和颜色。
我们扪心自问:难道我们人类几千年追求的居住文明,我们的理想,就是在一起拥挤、在一起呼吸污浊的空气吗?难道在杜甫悲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中,我们中国人就找到了今天这样的居所?
有路难走,有车难乘,有家难回——更可怕的是,我们几乎再也没有什么安静可以享受,每个人都在噪音的包围中无处躲藏。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城市、大都市。
令人惋惜的是,现在许多动手搞城市建设的人没有什么想象力,更没有追求完美之心,其结果就是,大半的城市都搞得很丑陋。在许多年里,我们这儿的人不仅对树木没有感情,而且简直就是以树为敌。所以我们年年讲造林、讲绿化,到头来还是生活在水泥堆里。没有绿色,没有空地,干燥的水泥堆砌起来,一座连一座挤在一起,这里面的大小空隙就塞了一个又一个家庭。这会有多少幸福可言?这真正是缺少人性化的生活。无数这样的形式叠加累积,最后组成了一个个区域,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在这里,绝不可能有第一流的物质和精神的创造。
树木、绿色,它们与城市的关系必须来一个颠倒。理想的居住环境,应该是楼房插在树木的空隙之中,而不是树木插在楼房的空隙之中。我们也许可以断言,这个被颠倒的关系一天不重新颠倒过来,城里人就一天没有幸福可言。
看看城乡建设,我们浪费了多少土地。我们许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在最好的耕地上建城市,而且没有任何节制。最适合种粮食的地方却不一定是最适合盖房子的地方,最后只能造成这样的恶果:吃不好也住不好。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到了一个极端危机的时刻,这绝不算是什么危言耸听。看看一座座街道相似、楼群相似、“小区”相似的城市,就会让人觉得窝囊丧气。不仅是这样,即便是在同一个所谓的“高尚别墅小区”里,每座小楼的样子也往往一模一样。
我们的想象力已经退化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夫复何言!
城市建设应该尽量节省耕地,这本来是一个实际而又浅显的问题。可是我们这些年却在走一个相反的道路,就是把最好的耕地建了房子。其实那些最不适宜耕作的地方,有时往往会是盖房子的好地方,比如海滩河滩荒地等等。有的小城本来离不能耕种的海滩不远,却愚蠢到非要在最好的农耕地上兴建新城区不可。
说到规划,我们这里一直是可有可无,没有什么常性的。过去没有城建规划,后来勉强有了,城区之间如何分布的大规划却又没有了。这同样糟糕,因为不仅有个城市怎么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有个在哪里建城市的问题。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害怕旧城改造。本来一些城区破烂得不堪入目,改造也是一种必然。问题是谁来改造、怎么改造。有的老城区在文化人看来非常美,在一些城建者那里看来却是非常丑。到底是谁错了?是文化人过于多愁善感,还是具体操作的人太粗鲁?我们观察下来,一般都是后者。一些决定拆和扒的人大半没有什么文化,有的权力不小,可惜识字不多。他们哪里谈得上什么人文素质、人文关怀,基本上属于文化方面的造反派。他们压根就不懂建筑同时也是一门艺术。
作者指出:他们一方面在改造旧城,一方面也在拆除历史。我们一般而言是没有权利拆除历史的,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权利,需要一个相当复杂的程序来赋予才行。对权利范畴的模糊无知,是一些傻大胆的愚夫干出蠢事的原因。他们哪怕面对一处几千年的古迹也敢拆,挽挽袖子骂一句粗话就可以动手。
无知的权利就一定意味着灾难,意味着腐败。那些粗鲁的开发商当中有相当数量的唯利是图者,他们一旦没有了遏制,就会给一个地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他们不会对环境负责,当然更不会对民众负责。他们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是对平民和公众利益的最大盘剥者。
我们讲依靠专家搞规划,但很少问一些关键问题,如找的是一些什么专家、专家又是怎样构成的,以及如何选择专家方案。在专家们形成了许多方案的前提下,我们的决策者很有可能从中选择一个最糟的方案,因为决策者的素质才是决定因素。还有,仅从专家而言,一些单纯的技术专家为了自己的方案被采纳,是极善于揣摸领导意图并做出许多妥协的。这样的规划结果当然值得怀疑。
有人极愿意把“发展”、把“抓住机遇快速发展”挂在嘴上,并且从来不强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为什么?就因为他们自身并不住在被糟践得一塌糊涂的环境中,他们出有豪车居有华屋,当然不顾群众怎样挣扎。
其实不计后果地、像当年搞阶级斗争一样地大搞野蛮建设,就是对这个民族最大的破坏行为。
一切不能将民众的具体利益纳于视野的所谓“发展”,都是极其可疑的。
《城市与文化》一书,给予我们的就是如上的探讨,是实在值得深长思之的大问题。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