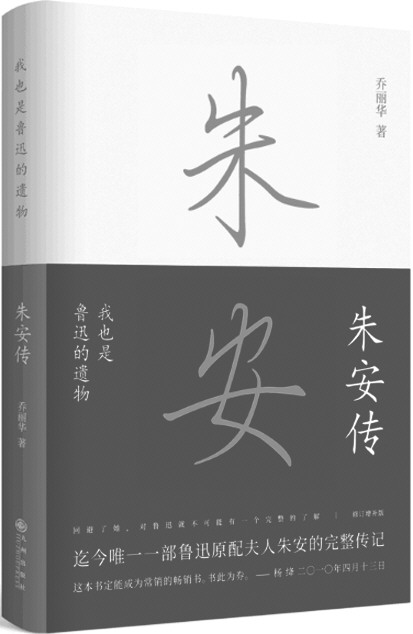朱安,约摄于19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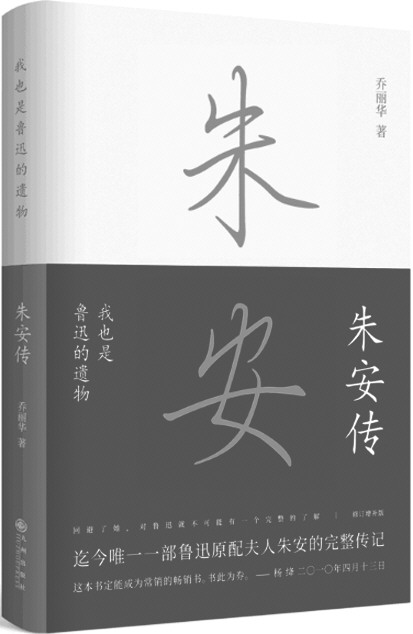
《朱安传》
乔丽华 著
九州出版社
提到鲁迅夫人,多数人只知道许广平,却不知他还有一个原配夫人朱安。关于这段婚姻,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鲁迅去世后,外界阻止出售鲁迅遗物,沉闷的朱安发出了最后一声呐喊:“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乔丽华的《朱安传》一书中,她把朱安这个旧时代的普通女性引入“公众视线”,让读者从另一个视角去观照和了解鲁迅。
>> 鲁迅谈婚姻:这是母亲给我的礼物
从1906年鲁迅与朱安成婚,到1936年鲁迅去世,朱安在巨人的身影下生活了整整30年。她生前留下的只有几段话,鲁迅在日记书信中偶尔提及她,只是含糊地用一个“妇”字,从来没有像称呼许广平或别的女性那样直呼其名,在公开的文字中更不著一字,足以看出鲁迅从心底里排斥着朱安与这桩婚姻。
母亲为鲁迅相中的朱安,和旧中国很多家庭的女儿一样,缠足,识字不多,但是懂得礼仪,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三从四德,温良贤淑。
1906年,母亲装病将鲁迅从日本骗回家与朱安成亲,时年鲁迅26岁,朱安28岁。听说新郎官喜欢大脚,朱安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讨新郎的欢心,可是在出花轿的时候,鞋子掉了,露出了三寸金莲。
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1909年回国后,鲁迅在杭州和绍兴做事,有一年半的时间夫妇俩同处于一个屋檐下,却形同陌路。鲁老太太多年之后得出沉痛结论:“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
1912年鲁迅在北京独居于绍兴会馆,1919年卖掉家中老屋,携母亲与朱安定居北京。1924年5月,鲁迅携母亲、朱安迁居到西三条胡同21号住宅,开始了在新家的生活,这使朱安重新看到了希望。
朱安一心服侍丈夫,孝敬婆婆,希望终有一天鲁迅能幡然醒悟,发现从前错待了她。朱安对鲁迅和母亲在生活上的照料,鲁迅自己是清楚的,但他仅仅同情她、供养她,却无法对她产生“爱情”。
鲁迅明白,朱安无错无罪,同样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他在《随感录四十》中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谈起朱安:“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的这句表白足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
有一次母亲问鲁迅:她到底有什么不好?鲁迅摇摇头说:不是什么不好,而是和她谈不来。母亲又问,怎么会谈不来呢?鲁迅说:和她谈话无味,无趣,不如不谈。鲁迅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他和她谈起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而且全中国也没有。她这样说或许是为了奉承鲁迅,讨好鲁迅,但鲁迅就不再和她谈下去了。三人一起吃饭,常常是母亲和鲁迅间话多,谈笑风生。要是母亲到周作人家去,只有两个人吃饭,朱安无话找话,也只能问问小菜可咸可淡,鲁迅简单地答“不咸”、“淡些”,就又相对无言了。
鲁迅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后,陆续有女学生来家中做客,朱安感觉到鲁迅待人接物的方式在悄悄发生改变:中秋节,鲁迅和女学生们一起喝酒,朦胧醉意中拍打一个个女学生的头;某晚,鲁迅替借住在家中的许广平剪头发……她发现,“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最终,鲁迅决定“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1926年8月26日,他与许广平一同离开北京去了南方。
>> 朱安的呐喊:我也是鲁迅的遗物
当得知许广平已经在上海为鲁迅生下儿子海婴时,朱安为他们高兴,她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
曾同院居住的俞芳问朱安以后怎么办,她回答:“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老太太)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朱安没有料到,先去世的不是鲁老太太,而是鲁迅。
1936年鲁迅去世,许广平继续寄钱维持朱安与鲁老太太的日常开支。在日军占领上海,许广平被宪兵逮捕的那段时间,生活费的来源就暂时断绝了。由于别无经济来源,再加上物价上涨,朱安只得借贷与变卖家产。1943年鲁老太太去世后,朱安的生活贫苦至极,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藏书。消息传到上海,许广平和进步文化界人士大为惊骇。当年10月15日,宋紫佩陪同唐弢、刘哲民去拜访朱安,劝说她万勿如此。朱安却情绪激动地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这是她一生最后的呐喊,也是她一生唯一一次为自己申诉。
“她也是鲁迅遗物,要保存她,这是天经地义,没有什么可说。”唐弢索性将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如何将海婴转移等细节说了一遍,朱安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唐弢在《<帝城十日>解》文中有记录:“她脸色缓和下来,渐渐露出笑意,说大先生只留下这点骨肉,不知现在孩子的哮喘病好了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当我回答已经痊愈的时候,她以微微责备的口气,问我为什么不将海婴带到北平来,让她看看。”气氛缓和之后,藏书出售的问题也迎刃而解。
此后,许广平千方百计给朱安筹措生活费。虽然并不宽裕,总是不够用,生活很苦,但朱安已十分感激许广平,两人之间通信不断。
抗战胜利后,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一般都是辞而不受,“宁自苦,不愿苟取”,她不想因为自己一时的温饱而丢了鲁迅的颜面。
1946年10月下旬,许广平终于来到北平,清点和整理鲁迅的藏书,顺便与朱安相见。她回上海后,朱安在信中说:“你走后,我心里很难受,要跟你说的话很多,但当时一句话也想不起来。”
1947年,朱安重病,知道自己可能来日无多,便请人列出了自己的衣物清单,特意将兰绸裤料、麻料里子各一块留赠许广平以作纪念。6月28日,临终前一天,朱安对来访的南京《新民报》记者总结性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及与鲁迅的关系:“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她还提到许广平:“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最后一个愿望,是死后能同鲁迅葬在一起。这个遗愿最终没有实现,独自葬在北京保福寺墓地,后被夷为平地,不知魂归何处了。
>> 为小人物立传:暗处的朱安也有光
新中国成立后,鲁迅被誉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动辄被神圣化,当做偶像来崇拜。然而他的婚姻却是包办婚姻,许多人认为这有损鲁迅的形象,对朱安的描述与研究被视为禁忌。
1978年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山田敬三参观鲁迅故居时,看到鲁迅的书斋和卧室与鲁迅母亲的房间都有明确的指示牌,朱安的房间却没有标识,直到1986年才恢复“朱安居室”。
1981年,薛绥之教授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卷出版,反映了“文革”后鲁迅生平史料研究的最新成果,“鲁迅家庭成员及主要亲属”的条目下列出了“朱安”一条,仅有四百余字,还有一张朱安的照片。上海鲁迅研究者倪墨炎回忆,有人曾向领导部门报告,说这是辱没鲁迅的行为。
其实早在鲁迅逝世不久,许寿裳为撰写《鲁迅年谱》给许广平写信:“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许广平当时即表示:“至于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气量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
许寿裳所辑《鲁迅年谱》中有“(鲁迅)二十六岁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字样,但有关鲁迅配偶的“正史”,都以1927年在上海与鲁迅一同生活的许广平作为主轴。
在一段时期内,朱安在鲁迅研究中是个无法安置的人物,即便有提及,“包办婚姻的罪恶”也是鲁迅故事中的一个主旋律。
鲁迅的朋友曹聚仁所著《鲁迅评传》中“他的家族”章节提到,鲁迅是被骗与朱安成婚的,是“不合理的旧式婚姻”。鲁迅常对许寿裳表示,朱安像母亲送他的一个礼物,因此他也有义务去供养她。《评传》认为,“由这沉痛的话,我们也可以想见鲁迅精神上的痛苦了”。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鲁迅研究“人性化”的回归,又有一些人以“反对神化鲁迅”为旗号,借朱安而攻击鲁迅。针对这两个极端,唯一的办法是: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因而也就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朱安。
作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乔丽华一直从事鲁迅研究方面的工作,她选择朱安这样一个人物写传记,并不是想凑名人婚恋的热闹,也不是为了争论鲁迅与朱安在婚姻中孰对孰错,只是想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女性的命运加以关注和思考,“朱安站在暗处的一生是否也有她自己的光?”
大多数当年的遗迹和人物都不复存在了,要想还原朱安的生活比登天还难。除了翻阅大量的关于鲁迅先生的资料、史料,乔丽华还专程去绍兴、北京做实地调研,去上海的弄堂拜访朱安的侄辈后人,最终以女性的细腻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杨绛生前读到了《朱安传》的初版,她在给乔丽华的信中流露出对朱安的深切同情:“朱安最后那一声凄惨的呼号,实在动人怜悯。常言‘一双小脚三升泪’,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弃物’!”
陈丹青在书中感受到了朱安对鲁迅的深刻影响,还提出了一个“有点儿过于大胆”的想法——朱安与许广平这两个鲁迅生命中的女人,若论谁对鲁迅的影响更大,不是许广平而是朱安,“正是朱安,使鲁迅体味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命运的荒诞,断了他的后路,刺激他与传统彻底决裂,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反抗封建礼教,与命运进行‘绝望的抗争’。”
朱安是一个旧时代普通的悲剧人物,只因为她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家,才受到了世人的特别关注。为朱安立传,意义何在?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指出,正是朱安这位个性色彩鲜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出“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是研究中国妇女史、伦理史的一个标本,对研究鲁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义。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