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0世纪中国消费者画像

电影《最爱女人购物狂》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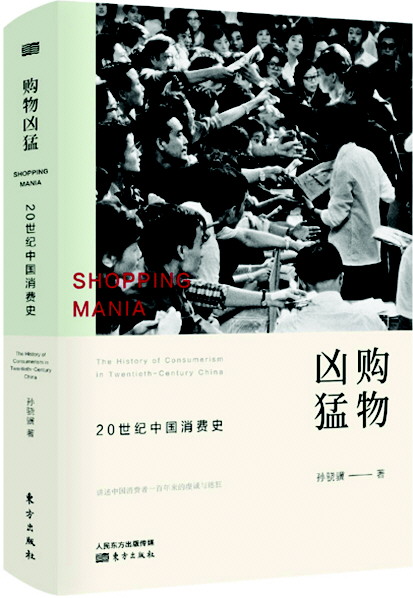
《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
孙骁骥 著
东方出版社
买买买!
一个世纪以来,消费主义的大潮已经让人无法独善其身,必须消费,只能消费,消费已经成为人们构建身份认同的渠道。然而,“消费至死”的时代,将会把我们带往何处?《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一书的作者孙骁骥,透过“中国消费者”这双集体的瞳孔,引领我们更加真切地窥见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生活的国度,并把这份真切尽可能久地留存于记忆之中。
可以购买的“现代文明”
当我们高谈阔论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辙迹时,常常忽略了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人是以何种方式踏入现代社会这扇喧嚣的大门的。中国近百年的商业史诉说着如下的故事:那些性格固执、观念陈腐、脑后拖着一条丑陋辫子的国人,自19世纪末期开始,仿佛着了魔似的,排着长长的队列,伫立于“现代文明”的大门口前。在焦虑中等待的他们渴望跨过这道门槛,到对面一窥究竟。他们手里紧紧攥着入场券——钞票,却又随时准备抛之于市,用金钱换取一件件西方工业文明所创造出的精巧商品。
购物,自此成为民众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中国的消费者在花钱购买西洋钟表、西洋烟酒、电灯电报,以及舶来的种种“奇技淫巧”的同时,实则是在为自己购买一张“现代生活”的门票,获得能像他们羡慕的西方人那样生活的机会。这个漫长的排队过程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他们今天成功了吗?
环顾四周,现代文明的众多“成果”都必须通过购买才能获得,从航天技术到网络科技,从分子材料学到食品科学……无论何等艰深晦涩的科技,在资本力量的介入之下,统统被自动化工厂生产成了各类新型的产品,在市场中,亦可以被细分归类为一系列的商业品牌。现代商业文明就像是一个奇特的漏斗,把千奇百怪的现代技术一概都“过滤”成了能被摆放在商店里售卖的、具有单一价值维度的可交换物品。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由此被蝗虫般不断涌现的商品覆盖,周而复始,终于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卖场”。(从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来看,这太容易理解了,榜单第一名赫然是沃尔玛)。然而,细加辨别,我们也会发现,摆在这个大卖场里的每一件商品都不能说是“价值中立”的。
假如消费者能戴上电影《极度空间》里那副能洞穿一切事物本质的神奇眼镜,他们将透过镜片看见,自己身处其中的这座商品大卖场门口其实悬挂着“现代文明”的隐形招牌,其中售卖的商品则无一例外地贴上了一张“现代”的隐形文化标签,并且按照品类的不同贴上了象征着诸如“社会阶层”“品位”“民族”的各色标牌。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思,在今天毫不费力地被消费者改写为“我买,故我在”的座右铭。商品消费,几乎成了一张获准进入现代社会的身份证明,而且一个人也只有通过消费这些商品,才能确认自己在现代文明的价值维度中的社会身份和位置,或者说,确认了“我是谁”这个亘古的问题。
如果你执意反其道而行,则很可能会出现身份认同上的困难。假如,一个固执的家伙坚决不肯通过购买手机或网络通信服务来向友人发送消息,而是要像古人那样写信托人转交,甚至是使用信鸽,那么他无疑会被大家视为与当下社会格格不入的“史前怪人”。
大众消费成就了商业链条顶端的“聪明人”
中国自晚清以来,追求“现代化”、甩掉小农经济“旧包袱”的步伐一刻未停,其中,商业领域改革的节奏尤为引人注目。商品经济和消费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大地上蔚为流行的两个时期,有两位在华的外商写了两部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一是民国时期卡尔·克劳的《四万万顾客》(400 Million Customers),其二是詹姆斯·麦克格雷格出版于2005年的《十亿消费者》(One Billion Customers),两部相距半个多世纪的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人复杂多变的集体形象浓缩为一个词——customers(顾客、消费者)。
“消费者”这一称谓无疑抓住了近现代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日益强大的商品购买力显然已成为国家力量崛起的一个具体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本书出版的时期,这个国家也分别经历着两次经济上的“解放”。前者是从封建王朝的小农经济下获得解放,后者是从苏式计划经济中获得解放,两次“解放”都是以市场经济为目标,都造成了商品市场的繁荣和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确立。
在我看来,20世纪初清政府发动商业革命的最大功绩并不是扶持了民族工商业,而是让百余年前的清人有机会从“臣民”的身份剥离出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商品消费者;另一个转变发生在1978年,自那一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改革,让中国人逐渐远离了过去数十年千篇一律的身份,成为了新时代的消费者。
然而,身份的倏然转变并没有立即带来“普遍的幸福”,或者实现了“经济上的民主”。如前文所说,消费者的行为和偏好总是受到各种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毫无干扰地存在于真空中。历史文献给我们的真实回馈是:鉴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辙迹,百年来,消费主义经常被政治局势和文化思潮所裹挟,消费者身上的这一抹文化的异色,在很多时候都显得异常浓烈。
今天,消费主义实际上已经是我们的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的一种方式。一个人从生至死,每一天的衣食住行,乃至医疗、教育、婚姻、生育、就业、休闲、娱乐等等巨细无遗的方面都不得不与商品消费打交道,甚或可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购物行为。商品消费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政府而言都是一个利好行为。在文化上,恰如西托夫斯基所言,消费主义用大宗商品和更炫目的生活方式“教化”了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让人们把欲望、刺激、快乐等等生存要素都同时置放在了消费主义的社会框架之下。而消费社会较之于农业社会、封建社会而言是更高层级的社会形态,为此,追求“进步”的现代人理应毫无保留地接纳消费主义,委身于商品市场,进而成为一个称职的消费者……
沿着以上貌似合理的逻辑不断往下推测,结论却会一路“跑偏”,甚至最后会变得荒诞而扭曲。难道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所说的扁平化、碎片式、快节奏、无深度感的“消费社会”就是我们所居住世界的终极形态吗?它看上去是像美丽富饶的理想国,还是更像一个“1984式”的可怕梦魇?这种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难道今天的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被商业和消费的肥皂泡包裹着的现实中吗?加拿大著名左派知识分子娜奥米·克莱恩就曾著书批判国际品牌和跨国企业对消费者的思想控制和文化洗脑,号召人们反抗消费文化对人性的“侵蚀”,抵制跨国商标和品牌。如此振臂一呼式的激进观点在读者当中颇有市场,与彻底的自由市场理论相映成趣。
(本文摘选自《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序言)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