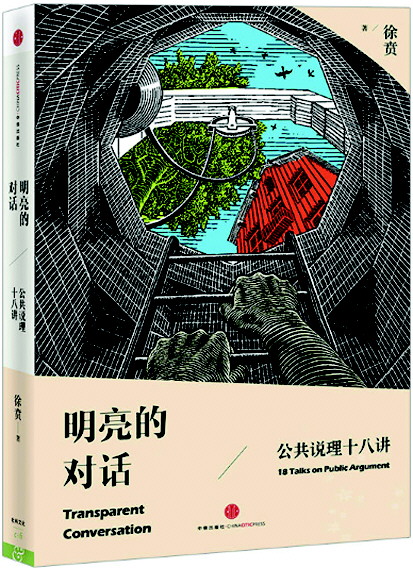说理,让对话明亮起来
齐鲁晚报 2019年04月20日
前几日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刷屏,意想不到的是有网友竟联想到了英法联军点燃的圆明园大火,所谓“苍天饶过谁”的幸灾乐祸不在少数;再早些时候视觉中国的“黑洞事件”,本该引起人们对知识产权的冷静思考,却成了网民们吐槽、发泄、哭诉的对象。互联网为公共讨论和说理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舆论空间,但明显缺乏“理性”。早在五年前,学者徐贲曾出版一本《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专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当对话明亮起来,或许我们会有共识,说理可以不只是一项活动,而且是良善的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曲鹏
一开口就是“我不高兴”
上世纪80年代,徐贲到美国求学,在马萨诸塞州大学攻读英语文学博士,随后任英语系的写作课助教。令他当初没想到的是,“说理”竟然是一门课程。如今,徐贲在美国高校教授公共说理写作已有20余年,还经常为国内几家媒体撰写时评,碰到过不少与他观点相左的说理者,这并没有令他感到不快,“我在乎那些真的说话在理的人,我也希望能碰到好的说理对手”。
2009年,一本宣扬民族主义的畅销书曾引发人们的激烈讨论,徐贲也在报纸上发表了意见。他没有争论民族主义问题,而是把焦点集中在书里出现的逻辑谬误上——过度简单化、浮泛空论、循环论证、虚假两分法、无凭据推理、不当类比,指出“公共说理不是吵架”,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不高兴”“我生气”,“公共说理要通过交流、说服来达到共识”。
由于篇幅的限制,文章中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其实书中的逻辑谬误远不止这些。许多读者看到后觉得意犹未尽,希望能把公共话语理性问题再谈得深一些。这样的反馈,使徐贲意识到国内的公共说理太少了。
同一年,朋友赠送给徐贲一本英国逻辑学家斯泰宾的《有效思维》中文版,前三分之二部分是由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翻译的。1986年,82岁的吕叔湘开始翻译《有效思维》,“我翻译这本书,是有鉴于常常看到一些说理的文字里头隐藏着许多有悖正确思维的议论,希望能通过这本书的译本使发议论的文风有所改进,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就使80多岁的老人把已经极其有限的工作时间用在这个译本上不为无益了”。吕先生“一天翻千儿八百字,断断续续三年”,1988年底停下来,后来得了一场病,再想译完也译不成了,最后由他人完成。
这件事对徐贲有所触动,专门写成了一本“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他慨叹“吕先生如此执着于此书(《有效思维》),大概是有感于‘文革’过去10年后,说理在中国仍然是一种尚未实现的有效思维吧。又过了20多年,今天我们还在谈公共说理,仍然还是一件普及和启蒙的工作。”
说理不等于巧舌如簧
中国有句俗语,“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似乎传统文化中很重视“理”。然而,贤人顿悟参透的“理”、老百姓心目中的天道这个“理”,都不是公共说理的那个“理”。
徐贲将“说理”定义为一种技能,还包括对待他人的礼仪——“尊重他人、顾及对方感受、理性、平等、不断章取义、尽量周全地理解别人的观点或看法,等等。”说到底,“说理的理不是指某种对所有人都有强制认同效能的‘真理’,而是指一个理性、逻辑说明自己看法,并争取他人认同的过程。”同时“说理”也是一种教养,不但要保持一种不去侵犯别人的心态,还要学会在表情、声音、言语、动作、姿势乃至整个外部仪态都要表现得恰到好处,让参与交谈的人感到自在愉悦。
在西方,公共说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从古希腊就有的演说修辞,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法庭辩论、公民大会和公开演说三大修辞;另一个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出来的“文明交谈”。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却不能为公共说理提供孕育和成长的条件。中国古代有发达的辩术,辩士们面对的是喜怒无常、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培养出扭曲的说话技巧,像东方朔、纪晓岚那般铁齿铜牙、巧舌如簧的比比皆是,却没有像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体良那样研究说理的人。徐贲在国内见到过一本教讲话技巧的书,也跟说理无关,而是教人说话要先学会察言观色,要“合时宜”,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对对方有没有帮助就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使你备受别人喜欢”。
公共说理的那种对话和交谈,并不是普通的说话表达,更不是辩术。据说宋代理学家朱熹遇见友人盛温如提着篮子上街,笑问:“上哪儿?”回答说:“上街买东西。”朱熹又问:“为什么不能买南北?”回答说:“不能,因为按照五行与东、南、西、北、中相配,东属木,西属金,金木类,篮子可盛;而南属火,北属水,水火类,篮子不可盛。所以只能买‘东西’,不能买‘南北’。”这个故事在常人看来,显示了古人的语言智慧,而在徐贲看来,这样的辩术中虽然有“因为”和“所以”,但并不是逻辑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许有文学、娱乐或其他价值,但对公共说理并无实质意义”。
说理是“摊开的手掌”
对于一些人不说理,徐贲认为并不是缺乏“说理基因”,关键还在受“暴力基因”困扰。
他把说理比作“摊开的手掌”,意为欢迎他人加入对话。而在现实中,说理常常是攥紧拳头,成为“占领话语阵地”“口诛笔伐”“论战”和向对方报以“投枪”和“匕首”,用争吵、对立、谩骂来压制对方,迫使对方哑口无言,这样才能取得“胜利”。“许多人从小在大批判、大辩论中学会了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言辞嚣张,长大成人后,他们仍然以为辩论或公共话语就该是这个样子,浑然不觉这种形同泼皮的纠缠根本就不是有教养、有思想的说理逻辑。”
2010年药家鑫案发生后,死刑的存废问题曾经引发过一场讨论。在一篇主张废除死刑的文章下,徐贲看到了两条留言,一条是:“像你这样的作家,我只能称你为垃圾,你已经在违背自己的道德,真不知道你学的是什么……”另一条留言则反驳道:“某位(读者)看来智力与情感有双重问题,根本不懂得如何辩论,只会情感宣泄式地喊口号……这种网络愤青只能显示自己的无知——但愿不死的药家鑫下次撞死的是你这个神经病。”
争吵、羞辱、嘲笑、谩骂,这种语言在网络和大众文化中已盛行多时。正如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所指出的,这种以网络为主要言说空间的话语,其明显特征是“哄客”们的暴力、冲动、专横、仇恨。这个网络中的“群氓社会”,与《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在100多年前论述的有形群氓社会具有相同性质的狂烈、暴戾、易受蛊惑和不理性。
上世纪30年代,学者萧公权在《大公报》上撰文讨论“言论自由”,谈到当时“意气用事之谈,褊狭无容之见”触目可见,人们更擅长党同伐异、拉帮结派,“异己者势欲打倒,同调者奉若神明,圆通宽大之风度”,由此推断并不是有了言论自由就一定会有自由的言论。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徐贲感慨“说理仍然离我们非常遥远”,萧公权所忧虑的强蛮话语仍然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随着互联网包括移动端的发展,使得跟帖、微信、微博成为普通人参与公共事务并发表自己看法的重要渠道,但因为字数有限,徐贲认为这更容易成为“不说理”的言论形式,好一点的是断言、口号、警句,差一点的便是谩骂,同样是发表意见,但都不是说理的方式。
同时,便捷的网络信息,使人们在复杂多变的事情面前,找到了方便的解答,自以为是把握形势的力量,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便是斯泰宾在《有效思维》提出的“罐头思维”——“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结果是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最终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讲理,从娃娃抓起
小孩子天生就喜欢问“为什么”,没有耐心的大人往往以“小孩子不懂”来搪塞;小孩子也喜欢用吵架的方式来“说理”,大人也常常以“闭嘴!别争了”加以干涉。殊不知,这些都是让儿童学会说理的最好方法。许多看似天生会说理的人,“他们恰巧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周围的人们都说理的环境中,因而从小受到了潜移默化的说理教育”。他们的父母尊重孩子自由表达的权利,在孩子表达意见和诉求时,鼓励他们提供理由,帮助他们比较、评估理由的好坏。
从小缺乏说理教育而没能学会说理,并不等于他在成人以后再也学不会说理。在美国,说理教育贯穿了从小学到大学整个教育阶段。在《明亮的对话》一书中,徐贲以《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十二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教学)纲要》为例,详细分析了美国加州公立学校对学生“说理”的具体要求:
一年级:“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要观点”;二年级:“重述文本中的事实和细节,说清和组织要说的意见”;三年级:“在说理文中区别主要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细节”;四年级:“区别说理文本中的‘原因’与‘结果’、‘事实’和‘看法’的区别”;五年级:“分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论’和‘看法’(尚有待证明的观点)”。六年级是最为关键的一年,公共说理分为两个部分:一、辨析逻辑谬误;二、提防宣传。那些要辨析的逻辑谬误有五种:过度简单化、浮泛空论、循环论证、虚假两分法、无凭据推理。要提防的宣传手法则有十种:人云亦云、谩骂、偏见、势利、老百姓的话、吹嘘、“科学”根据、证词、恫吓战术、株连……十一到十二年级:“说理评估”对象是“公共文件”,一切发表了的东西,只要议及公共话题,都是公共文本,也都必须接受公众的“说理评估”。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美国就开始说理教育,说理教育贯穿了美国的整个基础教育所有阶段,而且基本上都是必修课,普遍采用阅读和写作的方式来进行,比如徐贲在美国高校教授的公共说理写作课。这种写作并非人们一般印象中的写作,如诗歌、散文、游记、书信、小说等等,而是一种称为“格式化随笔”(essay)的作文。许多文采飞扬的中国学生到了美国的大学反而不会写作了,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国内的写作习惯与美国的作文要求之间是脱节的。“学会美国作文是不难的,但能不能领会这种文章背后的人文教育理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本报记者 曲鹏
一开口就是“我不高兴”
上世纪80年代,徐贲到美国求学,在马萨诸塞州大学攻读英语文学博士,随后任英语系的写作课助教。令他当初没想到的是,“说理”竟然是一门课程。如今,徐贲在美国高校教授公共说理写作已有20余年,还经常为国内几家媒体撰写时评,碰到过不少与他观点相左的说理者,这并没有令他感到不快,“我在乎那些真的说话在理的人,我也希望能碰到好的说理对手”。
2009年,一本宣扬民族主义的畅销书曾引发人们的激烈讨论,徐贲也在报纸上发表了意见。他没有争论民族主义问题,而是把焦点集中在书里出现的逻辑谬误上——过度简单化、浮泛空论、循环论证、虚假两分法、无凭据推理、不当类比,指出“公共说理不是吵架”,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不高兴”“我生气”,“公共说理要通过交流、说服来达到共识”。
由于篇幅的限制,文章中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其实书中的逻辑谬误远不止这些。许多读者看到后觉得意犹未尽,希望能把公共话语理性问题再谈得深一些。这样的反馈,使徐贲意识到国内的公共说理太少了。
同一年,朋友赠送给徐贲一本英国逻辑学家斯泰宾的《有效思维》中文版,前三分之二部分是由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翻译的。1986年,82岁的吕叔湘开始翻译《有效思维》,“我翻译这本书,是有鉴于常常看到一些说理的文字里头隐藏着许多有悖正确思维的议论,希望能通过这本书的译本使发议论的文风有所改进,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就使80多岁的老人把已经极其有限的工作时间用在这个译本上不为无益了”。吕先生“一天翻千儿八百字,断断续续三年”,1988年底停下来,后来得了一场病,再想译完也译不成了,最后由他人完成。
这件事对徐贲有所触动,专门写成了一本“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他慨叹“吕先生如此执着于此书(《有效思维》),大概是有感于‘文革’过去10年后,说理在中国仍然是一种尚未实现的有效思维吧。又过了20多年,今天我们还在谈公共说理,仍然还是一件普及和启蒙的工作。”
说理不等于巧舌如簧
中国有句俗语,“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似乎传统文化中很重视“理”。然而,贤人顿悟参透的“理”、老百姓心目中的天道这个“理”,都不是公共说理的那个“理”。
徐贲将“说理”定义为一种技能,还包括对待他人的礼仪——“尊重他人、顾及对方感受、理性、平等、不断章取义、尽量周全地理解别人的观点或看法,等等。”说到底,“说理的理不是指某种对所有人都有强制认同效能的‘真理’,而是指一个理性、逻辑说明自己看法,并争取他人认同的过程。”同时“说理”也是一种教养,不但要保持一种不去侵犯别人的心态,还要学会在表情、声音、言语、动作、姿势乃至整个外部仪态都要表现得恰到好处,让参与交谈的人感到自在愉悦。
在西方,公共说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从古希腊就有的演说修辞,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法庭辩论、公民大会和公开演说三大修辞;另一个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出来的“文明交谈”。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却不能为公共说理提供孕育和成长的条件。中国古代有发达的辩术,辩士们面对的是喜怒无常、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培养出扭曲的说话技巧,像东方朔、纪晓岚那般铁齿铜牙、巧舌如簧的比比皆是,却没有像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体良那样研究说理的人。徐贲在国内见到过一本教讲话技巧的书,也跟说理无关,而是教人说话要先学会察言观色,要“合时宜”,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对对方有没有帮助就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使你备受别人喜欢”。
公共说理的那种对话和交谈,并不是普通的说话表达,更不是辩术。据说宋代理学家朱熹遇见友人盛温如提着篮子上街,笑问:“上哪儿?”回答说:“上街买东西。”朱熹又问:“为什么不能买南北?”回答说:“不能,因为按照五行与东、南、西、北、中相配,东属木,西属金,金木类,篮子可盛;而南属火,北属水,水火类,篮子不可盛。所以只能买‘东西’,不能买‘南北’。”这个故事在常人看来,显示了古人的语言智慧,而在徐贲看来,这样的辩术中虽然有“因为”和“所以”,但并不是逻辑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许有文学、娱乐或其他价值,但对公共说理并无实质意义”。
说理是“摊开的手掌”
对于一些人不说理,徐贲认为并不是缺乏“说理基因”,关键还在受“暴力基因”困扰。
他把说理比作“摊开的手掌”,意为欢迎他人加入对话。而在现实中,说理常常是攥紧拳头,成为“占领话语阵地”“口诛笔伐”“论战”和向对方报以“投枪”和“匕首”,用争吵、对立、谩骂来压制对方,迫使对方哑口无言,这样才能取得“胜利”。“许多人从小在大批判、大辩论中学会了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言辞嚣张,长大成人后,他们仍然以为辩论或公共话语就该是这个样子,浑然不觉这种形同泼皮的纠缠根本就不是有教养、有思想的说理逻辑。”
2010年药家鑫案发生后,死刑的存废问题曾经引发过一场讨论。在一篇主张废除死刑的文章下,徐贲看到了两条留言,一条是:“像你这样的作家,我只能称你为垃圾,你已经在违背自己的道德,真不知道你学的是什么……”另一条留言则反驳道:“某位(读者)看来智力与情感有双重问题,根本不懂得如何辩论,只会情感宣泄式地喊口号……这种网络愤青只能显示自己的无知——但愿不死的药家鑫下次撞死的是你这个神经病。”
争吵、羞辱、嘲笑、谩骂,这种语言在网络和大众文化中已盛行多时。正如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所指出的,这种以网络为主要言说空间的话语,其明显特征是“哄客”们的暴力、冲动、专横、仇恨。这个网络中的“群氓社会”,与《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在100多年前论述的有形群氓社会具有相同性质的狂烈、暴戾、易受蛊惑和不理性。
上世纪30年代,学者萧公权在《大公报》上撰文讨论“言论自由”,谈到当时“意气用事之谈,褊狭无容之见”触目可见,人们更擅长党同伐异、拉帮结派,“异己者势欲打倒,同调者奉若神明,圆通宽大之风度”,由此推断并不是有了言论自由就一定会有自由的言论。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徐贲感慨“说理仍然离我们非常遥远”,萧公权所忧虑的强蛮话语仍然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随着互联网包括移动端的发展,使得跟帖、微信、微博成为普通人参与公共事务并发表自己看法的重要渠道,但因为字数有限,徐贲认为这更容易成为“不说理”的言论形式,好一点的是断言、口号、警句,差一点的便是谩骂,同样是发表意见,但都不是说理的方式。
同时,便捷的网络信息,使人们在复杂多变的事情面前,找到了方便的解答,自以为是把握形势的力量,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便是斯泰宾在《有效思维》提出的“罐头思维”——“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结果是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最终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讲理,从娃娃抓起
小孩子天生就喜欢问“为什么”,没有耐心的大人往往以“小孩子不懂”来搪塞;小孩子也喜欢用吵架的方式来“说理”,大人也常常以“闭嘴!别争了”加以干涉。殊不知,这些都是让儿童学会说理的最好方法。许多看似天生会说理的人,“他们恰巧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周围的人们都说理的环境中,因而从小受到了潜移默化的说理教育”。他们的父母尊重孩子自由表达的权利,在孩子表达意见和诉求时,鼓励他们提供理由,帮助他们比较、评估理由的好坏。
从小缺乏说理教育而没能学会说理,并不等于他在成人以后再也学不会说理。在美国,说理教育贯穿了从小学到大学整个教育阶段。在《明亮的对话》一书中,徐贲以《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十二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教学)纲要》为例,详细分析了美国加州公立学校对学生“说理”的具体要求:
一年级:“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要观点”;二年级:“重述文本中的事实和细节,说清和组织要说的意见”;三年级:“在说理文中区别主要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细节”;四年级:“区别说理文本中的‘原因’与‘结果’、‘事实’和‘看法’的区别”;五年级:“分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论’和‘看法’(尚有待证明的观点)”。六年级是最为关键的一年,公共说理分为两个部分:一、辨析逻辑谬误;二、提防宣传。那些要辨析的逻辑谬误有五种:过度简单化、浮泛空论、循环论证、虚假两分法、无凭据推理。要提防的宣传手法则有十种:人云亦云、谩骂、偏见、势利、老百姓的话、吹嘘、“科学”根据、证词、恫吓战术、株连……十一到十二年级:“说理评估”对象是“公共文件”,一切发表了的东西,只要议及公共话题,都是公共文本,也都必须接受公众的“说理评估”。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美国就开始说理教育,说理教育贯穿了美国的整个基础教育所有阶段,而且基本上都是必修课,普遍采用阅读和写作的方式来进行,比如徐贲在美国高校教授的公共说理写作课。这种写作并非人们一般印象中的写作,如诗歌、散文、游记、书信、小说等等,而是一种称为“格式化随笔”(essay)的作文。许多文采飞扬的中国学生到了美国的大学反而不会写作了,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国内的写作习惯与美国的作文要求之间是脱节的。“学会美国作文是不难的,但能不能领会这种文章背后的人文教育理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