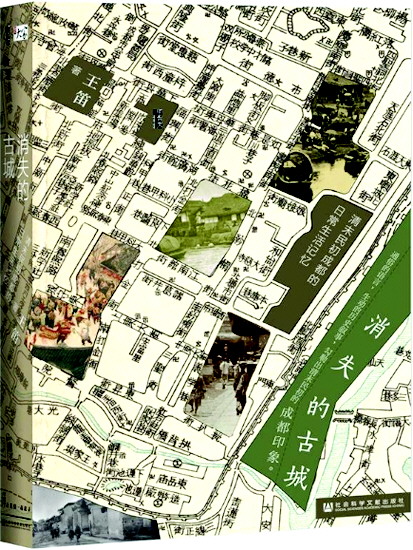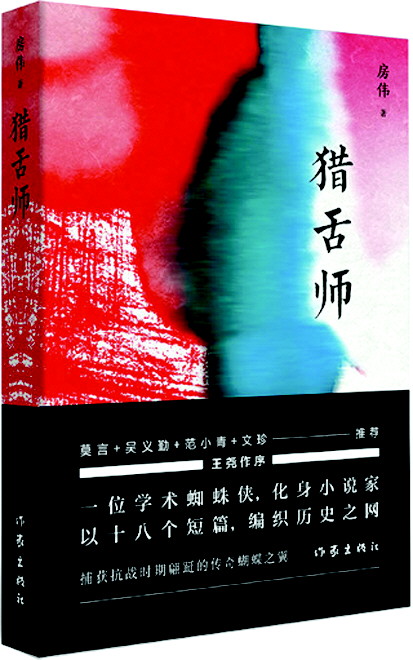用文学触摸历史的褶皱
齐鲁晚报 2019年04月20日
□房伟
几年来,学术研究之余,我一直对抗战史料保持着业余兴趣。在历史的深处,我发现了很多非常有趣、令人惊讶,也令人慨叹的细节。同时,我对当下抗战历史小说也有诸多不满。很多作品或流于戏说,止步于传奇性与戏剧性,或过于沉重乏味,成为史料的堆积,如何能写出别具一格的历史小说呢?我带着这些疑问,开始了历史小说创作。
说起来,我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和这些年对文学历史意识的思考分不开。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强调通过对中国地方性和阶层性的细分,在“移情”的基础上,形成观察思考中国历史的新的方法论。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内观态度,是对二战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冲击反应模式”“帝国主义模式”“传统-近代模式”的反思。这无疑丰富了西方观察历史的视角、观点和材料。除此之外,随着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学兴起,特别是法国年鉴派的布罗代尔、勒华·拉杜里等骁将的出现,历史学界对于历史细节性、偶然性和复杂性的关注,对多种研究方法和视野的综合(特别是文学性的引入),也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孔飞力的《叫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等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海外汉学著作,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些特点。然而,中国历史学界在这方面却是被动的,柯文的“以中国为中心”仍然有着西方主体论的坚实哲学基础,而中国学者研究自己的历史,其根基又何在呢?在国内史学界,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西方启蒙史观、后现代史观等几种观念的冲突,也出现了很多不错的作品,但总体而言,思路并不清晰,观念也并不明朗,特别是“见微知著”的能力和“文学性”的敏感捕捉能力,仍比较欠缺。
同样,从史学界说到文学界,其问题更是尴尬。俗话说,“文史哲不分家”,有活力的学术思想,更是直接影响文学创作。很多西方作家的历史小说,其实也受到了上述史学思潮的影响,如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但我们很多所谓具有后现代意味的、颠覆性的“新历史小说”,如果考察其精神内核,除了虚无之外,更靠近古代的传奇和演义。新时期以来,我们有过很多优秀历史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领域,如《少年天子》《白鹿原》《曾国藩》《胡雪岩》等。但当下中国的历史小说创作是匮乏的,尤其是抗战历史小说。
《猎舌师》这个系列开始于2016年年初,恰好我在台北的东吴大学访学。我住在幽静的阳明山下,钱穆故居旁,无人打扰,生活就是在图书馆、教室和宿舍之间进行着。写论文之余,当我在那些历史的尘埃之间飞扬思绪,就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也就一口气写出了18篇长长短短的战争历史小说。《中国野人》取材于北海道的中国劳工的原型,《幽灵军》取材于南京大屠杀后失踪的川军部队的故事。《肃魂》取材于肃托事件。《副领事》《起义》《花火》《猎舌师》《鬼子妮》等小说都有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原型。有的则只有一点历史的影子,如《红龙》之中,我试图以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香港为背景,再现宏大历史与个人的隐秘纠葛。出于对张爱玲的致敬,小说中的主人公成了易先生和蒋丽珍小姐。有的小说则完全是虚构的,甚至和现实发生某种程度的“互文性”,如《白光》《指南》。
我的笔下,有大人物,也有八路军战士、国军士兵,还有日本军官、随军僧侣,也有伪军军官、维持会的灰色人物,更有很多大历史下的普通中日民众。这里有英雄、汉奸,也有战俘、逃亡者和普通人。我试图展示一些战争横截面,有的是决定历史的时刻,有的则是普通人的生命瞬间,进而表现战争给民族国家、生命个体带来的创痛,揭示战争背后复杂的人性冲突,探究历史幽微深处的种种可能性。历史的幽魂无处不在,它们不知何时就会从历史的深处冒出,成为人世的潮水中,飘荡无定的赛壬的歌声。我不知道做得是否成功,但诚实地说,在对历史氛围的复原之中,我曾幻想带领笔下的几个小人物,真正回到历史时空,体验那些别样的氛围。它给我带来了很多隐秘的激情与快乐。我并没有什么小说名家的野心,而是学术研究之际,接触了大量史料,尤其是抗战史料,越发慨叹中国近代史的文学书写资源是如此丰厚。我们没有理由将中国历史文学的任务,都交给日本人和欧美作家,抑或穿越历史的网络作家。我们自己则在“书写现实”的旗号下,津津乐道,反复咀嚼那些“隔壁老王”的破事儿。
美国学者福山曾说:“历史已经终结。”此说法也为后现代主义塑造“终极景观”提供了灵感。虽然,福山后来又修正了看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主义,在新世纪也正发生着批评家们认为的“新转向”,即后现代性退隐,现代性重现。全球化的冲击下,人类没有走向大同。民族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的激进态度,却不断走向新冲突。英国退出欧盟,特朗普执政,泛亚和泛欧的强人政治重现,都在昭示意识形态未退出公共空间。地球上的人类,远远还不是躺在沙滩晒太阳的“最后的人”(LAST MAN)。也许,福山的最大启示,并不是预言了历史终结,而是展现了人类对未来的一种隐忧,即那些人类为之流血牺牲的概念,那些寄托人类爱恨情仇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民族优越感,是否会随着物质极大丰富走向消亡?没有了战争、冲突、政权更替,历史是不是会变成无聊的数字图表、枯燥的流水账?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对历史的文学书写,反而显得格外重要起来。因为正是历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正是那些历史的褶皱和可能性,会给人类的存在,提供更多的选择维度、生存勇气与时间的智慧。
几年来,学术研究之余,我一直对抗战史料保持着业余兴趣。在历史的深处,我发现了很多非常有趣、令人惊讶,也令人慨叹的细节。同时,我对当下抗战历史小说也有诸多不满。很多作品或流于戏说,止步于传奇性与戏剧性,或过于沉重乏味,成为史料的堆积,如何能写出别具一格的历史小说呢?我带着这些疑问,开始了历史小说创作。
说起来,我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和这些年对文学历史意识的思考分不开。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强调通过对中国地方性和阶层性的细分,在“移情”的基础上,形成观察思考中国历史的新的方法论。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内观态度,是对二战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冲击反应模式”“帝国主义模式”“传统-近代模式”的反思。这无疑丰富了西方观察历史的视角、观点和材料。除此之外,随着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学兴起,特别是法国年鉴派的布罗代尔、勒华·拉杜里等骁将的出现,历史学界对于历史细节性、偶然性和复杂性的关注,对多种研究方法和视野的综合(特别是文学性的引入),也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孔飞力的《叫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等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海外汉学著作,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些特点。然而,中国历史学界在这方面却是被动的,柯文的“以中国为中心”仍然有着西方主体论的坚实哲学基础,而中国学者研究自己的历史,其根基又何在呢?在国内史学界,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西方启蒙史观、后现代史观等几种观念的冲突,也出现了很多不错的作品,但总体而言,思路并不清晰,观念也并不明朗,特别是“见微知著”的能力和“文学性”的敏感捕捉能力,仍比较欠缺。
同样,从史学界说到文学界,其问题更是尴尬。俗话说,“文史哲不分家”,有活力的学术思想,更是直接影响文学创作。很多西方作家的历史小说,其实也受到了上述史学思潮的影响,如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但我们很多所谓具有后现代意味的、颠覆性的“新历史小说”,如果考察其精神内核,除了虚无之外,更靠近古代的传奇和演义。新时期以来,我们有过很多优秀历史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领域,如《少年天子》《白鹿原》《曾国藩》《胡雪岩》等。但当下中国的历史小说创作是匮乏的,尤其是抗战历史小说。
《猎舌师》这个系列开始于2016年年初,恰好我在台北的东吴大学访学。我住在幽静的阳明山下,钱穆故居旁,无人打扰,生活就是在图书馆、教室和宿舍之间进行着。写论文之余,当我在那些历史的尘埃之间飞扬思绪,就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也就一口气写出了18篇长长短短的战争历史小说。《中国野人》取材于北海道的中国劳工的原型,《幽灵军》取材于南京大屠杀后失踪的川军部队的故事。《肃魂》取材于肃托事件。《副领事》《起义》《花火》《猎舌师》《鬼子妮》等小说都有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原型。有的则只有一点历史的影子,如《红龙》之中,我试图以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香港为背景,再现宏大历史与个人的隐秘纠葛。出于对张爱玲的致敬,小说中的主人公成了易先生和蒋丽珍小姐。有的小说则完全是虚构的,甚至和现实发生某种程度的“互文性”,如《白光》《指南》。
我的笔下,有大人物,也有八路军战士、国军士兵,还有日本军官、随军僧侣,也有伪军军官、维持会的灰色人物,更有很多大历史下的普通中日民众。这里有英雄、汉奸,也有战俘、逃亡者和普通人。我试图展示一些战争横截面,有的是决定历史的时刻,有的则是普通人的生命瞬间,进而表现战争给民族国家、生命个体带来的创痛,揭示战争背后复杂的人性冲突,探究历史幽微深处的种种可能性。历史的幽魂无处不在,它们不知何时就会从历史的深处冒出,成为人世的潮水中,飘荡无定的赛壬的歌声。我不知道做得是否成功,但诚实地说,在对历史氛围的复原之中,我曾幻想带领笔下的几个小人物,真正回到历史时空,体验那些别样的氛围。它给我带来了很多隐秘的激情与快乐。我并没有什么小说名家的野心,而是学术研究之际,接触了大量史料,尤其是抗战史料,越发慨叹中国近代史的文学书写资源是如此丰厚。我们没有理由将中国历史文学的任务,都交给日本人和欧美作家,抑或穿越历史的网络作家。我们自己则在“书写现实”的旗号下,津津乐道,反复咀嚼那些“隔壁老王”的破事儿。
美国学者福山曾说:“历史已经终结。”此说法也为后现代主义塑造“终极景观”提供了灵感。虽然,福山后来又修正了看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主义,在新世纪也正发生着批评家们认为的“新转向”,即后现代性退隐,现代性重现。全球化的冲击下,人类没有走向大同。民族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的激进态度,却不断走向新冲突。英国退出欧盟,特朗普执政,泛亚和泛欧的强人政治重现,都在昭示意识形态未退出公共空间。地球上的人类,远远还不是躺在沙滩晒太阳的“最后的人”(LAST MAN)。也许,福山的最大启示,并不是预言了历史终结,而是展现了人类对未来的一种隐忧,即那些人类为之流血牺牲的概念,那些寄托人类爱恨情仇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民族优越感,是否会随着物质极大丰富走向消亡?没有了战争、冲突、政权更替,历史是不是会变成无聊的数字图表、枯燥的流水账?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对历史的文学书写,反而显得格外重要起来。因为正是历史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正是那些历史的褶皱和可能性,会给人类的存在,提供更多的选择维度、生存勇气与时间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