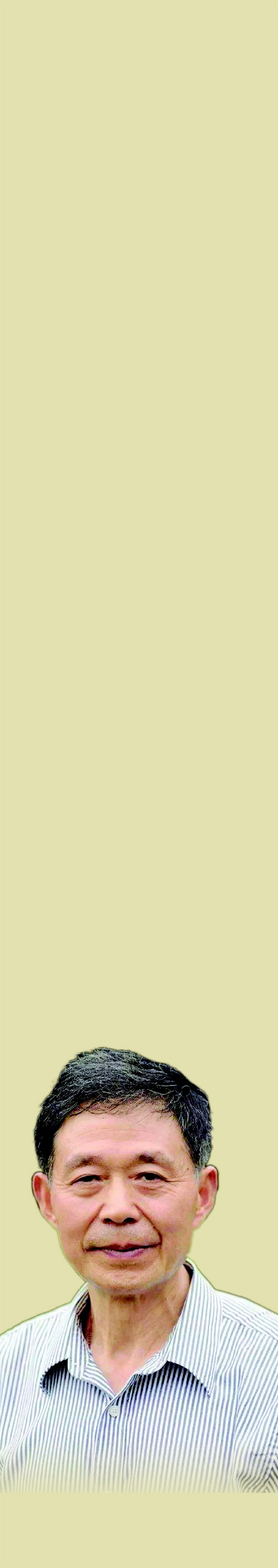赵生群:对经典的解读,通俗了才能普及
齐鲁晚报 2019年04月21日
□本报记者 范佳
4月15日,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生群作客山东大学,以“《史记》点校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为题讲述了他修订《史记》的历程与心得。“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他对当天聆听讲座、对古典传统文化深感兴趣的90后、00后学子的寄语。“在现代化的今天,文言文依然具有生命力,它是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里面存在着的。”赵生群曾磨剑八年大修《史记》,同时也致力于古籍普及,他认为经典古籍的通俗化很有必要,普及其实和提高是联系在一起的。
>> 不解决标点问题我睡不着觉
齐鲁晚报:2013年,您主持的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正式面世,为此您和南京师大的同仁投入了8年时间,改正了大量讹误、脱落、衍生、颠倒的文字。能否举个“改正”的例子以及如何做出的判断?
赵生群:修订版《史记》共撰写校勘记3400余条,处理文字涉及约3800余字,改动标点6000余处,还改正了原点校本排印错误300余处。
举个例子,《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意思是秦始皇51岁去世。钱大昕《三史拾遗》曰:“‘五’当为‘立’。秦王政二十六年始称皇帝,至三十七年而崩,计为帝十一年耳。”他的观点是秦始皇没有活到51岁,“五”应是“立”字,指的是秦始皇当了十一年皇帝。修订时我们发现了新的材料,在日本高山寺所藏的抄本中,这个字就是“立”。找到了版本的依据,再加上一些旁证的材料,就把这个错误改了过来。
还有解决标点的问题,包括冒号该不该用、上下引号引到哪里等问题,开始有先生担心工作量太大,甚至说:“是不是多此一举,没要求做这样的工作,去做有必要吗?”我当时就回答:“如果不做这项工作,我将睡不着觉。”因为标点是硬碰硬的问题,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核对标点参考的东西多了去了,很容易发现并解决问题。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做,做了之后得到的收获大大出乎我意料,通过解决标点问题还发现了大量校勘问题。
我还要提一点就是电脑资料库太重要了。现代化的工具和手法给古文献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不仅是事半功倍,功十功百功千功万都毫不夸张。
比如《四库全书》,在电脑资料库里输入一个关键词,一分钟之内需要的内容可以全部告诉你。而一个人什么事情都不做读《四库全书》要花上十年,这是什么效率?我曾经跟同学们讲,现在是读书做学问的好时候,各种各样好的版本、资料不断出现,借助现代化技术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超越前人的成就,将来的大师应该比之前的大师更厉害,如果我们没有做到,一定是因为我们努力不够。
齐鲁晚报:您曾表示史记修订的工作量大得难以想象,在修订过程中有哪些难点?
赵生群:《史记》号称“百科全书”,任何一个人终其一生,仔细研读未必能研究得非常到位,因为它涉及天文、地理、历法、甚至包括科学、音律等,范围太广。我们固然读了几十年《史记》,修订起来很多时候依然非常吃力,更多的时候碰到某一个问题需要临时恶补查阅各种资料,再通过自己研究来解决问题。
我们在修订时采取一种比较谨慎的做法,比如说前人已经有相关观点了,而我认为某一处标点可能有问题,但还没有把握的话,就暂时存疑,不去动它,可以另写成文字来探讨研究。
>> 对《史记》研读是永无止境的
齐鲁晚报:《史记》对于当代社会有哪些现实的意义和价值?
赵生群:我把《史记》总结为“三个最”:史料最复杂、版本最复杂、研究成果最多、最丰富。直到今天,它对社会的作用依然非常大。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远不止此。《史记》的内容太丰富了,其中包含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乃至科技史等诸多方面。
我说它是一道历史的长城,从皇帝写到汉武帝,这个2300多年的历史比司马迁写成《史记》直到现在的时间还要长。用钱穆的话来讲,要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的话,特别是文化人的话,不了解史记能行吗?历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比如说唐宋八大家、明前七子、明后七子,都把《史记》作为最高的典范来学,从中汲取营养。
《史记》还涉及军事政治,有人说它有诸子的性质,因为它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太大了。
当代人可以从《史记》中各取所需。例如军事家学习如何打仗,《史记》中很多战略都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例如项羽在彭城大战中以3万人对56万,而且是进攻一方,一上午的时间就把敌人收拾得干干净净,世界历史上我没找到第二个。还有伟大的军事家韩信的井陉之战、潍水之战等,里面有太多智慧经验可供我们吸取。
齐鲁晚报:接下来对《史记》的探索之路将往哪走?
赵生群:点校本《史记》修订本面世并不是一个句号。接下来比如开展对《史记》三家注复原性整理、《史记》历代版本资料库建设、《史记》汇校汇注汇考等工作,还要做一个《史记》新注甚至新的翻译本。
我认为古籍普及和整理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比如《左传》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深入浅出的读本,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太艰深了。当时我著《春秋左传新注》的目标就是尽量做到简明,在明了的基础上尽量简洁。
对《史记》来说,普及工作可能更加重要。我曾看到一个说法,引用最多的十部书中《史记》和《左传》都在其中,并且《史记》是排在第一位的,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其他著作,可见《史记》读者非常多,受众面非常大。
>> 古汉语具有永久生命力
齐鲁晚报:上世纪70年代,台静农牵头台湾一些大家作《白话史记》,把《史记》以白话形式翻译,当时有人认为通俗化翻译会损害了古籍的原来味道。如今更多的自媒体以各种形式解读经典,怎么看待对古籍的通俗化演绎?
赵生群:首先读者的群体、层次都是不尽相同的。尤其是现代白话文运动以来,文言文已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脱节。我们的教学体系中已经不像古人那样从小到大一直在读文言文,很多人已经无法完全读懂。即使是对那些中等文化程度的人,要想读《史记》这样的书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史记》里面有一些难的部分如八书,就是专家读起来也要借助注释甚至翻译,有时候还要查阅资料才能了解其中的含义,总之是非常吃力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通俗化还是很有必要的,普及其实和提高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大家都对古籍不感兴趣了,那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也就很成问题了。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正好到今年也有一百年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需要各个层次的东西,如校勘、加标点等,这些对大众阅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再普及一点,如加新的注释,像有些人读旧的注释已经不是很顺畅了,有的读了也未必搞得清楚,甚至根本读不懂了。有的注释毕竟还不能对应到每一个字,整个意思贯通起来也和字面的意思不太一样,所以需要新的注释,有时甚至需要翻译。这不一定会损坏原来的味道,因为原书毕竟还在,喜欢读原著没有标点的没有注释的,照样可以找原书来读。
齐鲁晚报:有种说法,学生有三怕,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现在又提倡传统文化的传播,可现状有的是雅俗共赏,有的是牵强附会,该怎么通俗化?
赵生群:通俗化工作我认为还是非常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普及化。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有很多人物都上去讲过,比如说影响和争议都比较大的于丹,她讲过论语心得后,现任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当时还是副总编的顾青先生到南京,和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教师做了一个座谈。在座谈中就讲到,于丹讲论语心得讲了一个星期后,中华书局的各个版本的《论语》都卖得非常好,把整个古籍热都带动起来了。
《论语》一直摆在那,为什么以前不被人关注,于丹一讲就有人读有人关注呢,甚至有人买书一买四五本,不仅自己买,还买来给孩子、老人、朋友。于丹通俗化讲完论语后,大家发现原来还有很多精神营养在里面。
而且于丹也有很多争议,比如争议她讲得好不好甚至对不对,还有人专门挑于丹的错。然而挑了错之后书卖得更火了,大家更加关注了。虽然她不是一个《论语》研究的专家,甚至不是一个古文献研究的专家,如果就《论语》谈《论语》,可能全国《论语》比她理解的更准确的,至少数以百计。但是不能否认她的普及之功,她这么一讲,社会效果反响很大,大家关注了重视了,这还是应该肯定的。
那通俗化的度怎么把握呢?我认为古籍首先是严肃的,不能把它改得低级庸俗,不能牵强附会,还是要准确地理解原著,尽可能接近原著的想法。当然有的时候,个人的理解会不一样,各个时代对同一本书的看法也会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我想也是允许的。总而言之,要以严肃、严谨的态度来对待,不是随便地去讲古籍,就像所谓的戏说,我比较反对的是一些哗众取宠的做法。
齐鲁晚报:有人认为文言文更多只是作为一种学习传统文化的人掌握的东西,一般人只要了解了就很好,现代人首先要学好现代汉语。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赵生群:其实现代汉语也是从古汉语来的。有很多东西我们天天讲却未必了解。比如说某一个地方着火了,消防车呜呜叫着开过来救火。这救火的“救”怎么讲,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如果懂一点古文字,认识就不同了。
《说文解字》上说,救,止也。也就是制止的意思,把火止住了,就叫救火。还有叫“救水”的,就是把水止住了。再比如说我们讲地老天荒,“老”和“荒”是什么意思?现代汉语里未必能讲得清楚,其实这俩字都是久远的意思。正如很边远的地方叫“荒蛮之地”,空间的久、时间的久都可以叫“荒”,比如说瓜长熟了、长老了,菜烧长了、烧老了,它也有长久的意思,所以地老天荒就是天长地久的意思。
可见,古汉语的很多东西并没有死去,因为现代的语言也是从古代的语言发展过来的,过去很多的成语、术语、典故我们当今仍然在用,这是历史文化不能隔断的,也不可以截然分开。所以文言文从这个意义而言,永远不会过时,它永远是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里面存在着,而且具有永久生命力。
4月15日,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生群作客山东大学,以“《史记》点校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为题讲述了他修订《史记》的历程与心得。“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他对当天聆听讲座、对古典传统文化深感兴趣的90后、00后学子的寄语。“在现代化的今天,文言文依然具有生命力,它是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里面存在着的。”赵生群曾磨剑八年大修《史记》,同时也致力于古籍普及,他认为经典古籍的通俗化很有必要,普及其实和提高是联系在一起的。
>> 不解决标点问题我睡不着觉
齐鲁晚报:2013年,您主持的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正式面世,为此您和南京师大的同仁投入了8年时间,改正了大量讹误、脱落、衍生、颠倒的文字。能否举个“改正”的例子以及如何做出的判断?
赵生群:修订版《史记》共撰写校勘记3400余条,处理文字涉及约3800余字,改动标点6000余处,还改正了原点校本排印错误300余处。
举个例子,《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意思是秦始皇51岁去世。钱大昕《三史拾遗》曰:“‘五’当为‘立’。秦王政二十六年始称皇帝,至三十七年而崩,计为帝十一年耳。”他的观点是秦始皇没有活到51岁,“五”应是“立”字,指的是秦始皇当了十一年皇帝。修订时我们发现了新的材料,在日本高山寺所藏的抄本中,这个字就是“立”。找到了版本的依据,再加上一些旁证的材料,就把这个错误改了过来。
还有解决标点的问题,包括冒号该不该用、上下引号引到哪里等问题,开始有先生担心工作量太大,甚至说:“是不是多此一举,没要求做这样的工作,去做有必要吗?”我当时就回答:“如果不做这项工作,我将睡不着觉。”因为标点是硬碰硬的问题,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核对标点参考的东西多了去了,很容易发现并解决问题。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做,做了之后得到的收获大大出乎我意料,通过解决标点问题还发现了大量校勘问题。
我还要提一点就是电脑资料库太重要了。现代化的工具和手法给古文献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不仅是事半功倍,功十功百功千功万都毫不夸张。
比如《四库全书》,在电脑资料库里输入一个关键词,一分钟之内需要的内容可以全部告诉你。而一个人什么事情都不做读《四库全书》要花上十年,这是什么效率?我曾经跟同学们讲,现在是读书做学问的好时候,各种各样好的版本、资料不断出现,借助现代化技术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超越前人的成就,将来的大师应该比之前的大师更厉害,如果我们没有做到,一定是因为我们努力不够。
齐鲁晚报:您曾表示史记修订的工作量大得难以想象,在修订过程中有哪些难点?
赵生群:《史记》号称“百科全书”,任何一个人终其一生,仔细研读未必能研究得非常到位,因为它涉及天文、地理、历法、甚至包括科学、音律等,范围太广。我们固然读了几十年《史记》,修订起来很多时候依然非常吃力,更多的时候碰到某一个问题需要临时恶补查阅各种资料,再通过自己研究来解决问题。
我们在修订时采取一种比较谨慎的做法,比如说前人已经有相关观点了,而我认为某一处标点可能有问题,但还没有把握的话,就暂时存疑,不去动它,可以另写成文字来探讨研究。
>> 对《史记》研读是永无止境的
齐鲁晚报:《史记》对于当代社会有哪些现实的意义和价值?
赵生群:我把《史记》总结为“三个最”:史料最复杂、版本最复杂、研究成果最多、最丰富。直到今天,它对社会的作用依然非常大。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远不止此。《史记》的内容太丰富了,其中包含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乃至科技史等诸多方面。
我说它是一道历史的长城,从皇帝写到汉武帝,这个2300多年的历史比司马迁写成《史记》直到现在的时间还要长。用钱穆的话来讲,要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的话,特别是文化人的话,不了解史记能行吗?历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比如说唐宋八大家、明前七子、明后七子,都把《史记》作为最高的典范来学,从中汲取营养。
《史记》还涉及军事政治,有人说它有诸子的性质,因为它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太大了。
当代人可以从《史记》中各取所需。例如军事家学习如何打仗,《史记》中很多战略都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例如项羽在彭城大战中以3万人对56万,而且是进攻一方,一上午的时间就把敌人收拾得干干净净,世界历史上我没找到第二个。还有伟大的军事家韩信的井陉之战、潍水之战等,里面有太多智慧经验可供我们吸取。
齐鲁晚报:接下来对《史记》的探索之路将往哪走?
赵生群:点校本《史记》修订本面世并不是一个句号。接下来比如开展对《史记》三家注复原性整理、《史记》历代版本资料库建设、《史记》汇校汇注汇考等工作,还要做一个《史记》新注甚至新的翻译本。
我认为古籍普及和整理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比如《左传》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深入浅出的读本,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太艰深了。当时我著《春秋左传新注》的目标就是尽量做到简明,在明了的基础上尽量简洁。
对《史记》来说,普及工作可能更加重要。我曾看到一个说法,引用最多的十部书中《史记》和《左传》都在其中,并且《史记》是排在第一位的,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其他著作,可见《史记》读者非常多,受众面非常大。
>> 古汉语具有永久生命力
齐鲁晚报:上世纪70年代,台静农牵头台湾一些大家作《白话史记》,把《史记》以白话形式翻译,当时有人认为通俗化翻译会损害了古籍的原来味道。如今更多的自媒体以各种形式解读经典,怎么看待对古籍的通俗化演绎?
赵生群:首先读者的群体、层次都是不尽相同的。尤其是现代白话文运动以来,文言文已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脱节。我们的教学体系中已经不像古人那样从小到大一直在读文言文,很多人已经无法完全读懂。即使是对那些中等文化程度的人,要想读《史记》这样的书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史记》里面有一些难的部分如八书,就是专家读起来也要借助注释甚至翻译,有时候还要查阅资料才能了解其中的含义,总之是非常吃力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通俗化还是很有必要的,普及其实和提高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大家都对古籍不感兴趣了,那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也就很成问题了。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正好到今年也有一百年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需要各个层次的东西,如校勘、加标点等,这些对大众阅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再普及一点,如加新的注释,像有些人读旧的注释已经不是很顺畅了,有的读了也未必搞得清楚,甚至根本读不懂了。有的注释毕竟还不能对应到每一个字,整个意思贯通起来也和字面的意思不太一样,所以需要新的注释,有时甚至需要翻译。这不一定会损坏原来的味道,因为原书毕竟还在,喜欢读原著没有标点的没有注释的,照样可以找原书来读。
齐鲁晚报:有种说法,学生有三怕,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现在又提倡传统文化的传播,可现状有的是雅俗共赏,有的是牵强附会,该怎么通俗化?
赵生群:通俗化工作我认为还是非常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普及化。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有很多人物都上去讲过,比如说影响和争议都比较大的于丹,她讲过论语心得后,现任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当时还是副总编的顾青先生到南京,和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教师做了一个座谈。在座谈中就讲到,于丹讲论语心得讲了一个星期后,中华书局的各个版本的《论语》都卖得非常好,把整个古籍热都带动起来了。
《论语》一直摆在那,为什么以前不被人关注,于丹一讲就有人读有人关注呢,甚至有人买书一买四五本,不仅自己买,还买来给孩子、老人、朋友。于丹通俗化讲完论语后,大家发现原来还有很多精神营养在里面。
而且于丹也有很多争议,比如争议她讲得好不好甚至对不对,还有人专门挑于丹的错。然而挑了错之后书卖得更火了,大家更加关注了。虽然她不是一个《论语》研究的专家,甚至不是一个古文献研究的专家,如果就《论语》谈《论语》,可能全国《论语》比她理解的更准确的,至少数以百计。但是不能否认她的普及之功,她这么一讲,社会效果反响很大,大家关注了重视了,这还是应该肯定的。
那通俗化的度怎么把握呢?我认为古籍首先是严肃的,不能把它改得低级庸俗,不能牵强附会,还是要准确地理解原著,尽可能接近原著的想法。当然有的时候,个人的理解会不一样,各个时代对同一本书的看法也会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我想也是允许的。总而言之,要以严肃、严谨的态度来对待,不是随便地去讲古籍,就像所谓的戏说,我比较反对的是一些哗众取宠的做法。
齐鲁晚报:有人认为文言文更多只是作为一种学习传统文化的人掌握的东西,一般人只要了解了就很好,现代人首先要学好现代汉语。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赵生群:其实现代汉语也是从古汉语来的。有很多东西我们天天讲却未必了解。比如说某一个地方着火了,消防车呜呜叫着开过来救火。这救火的“救”怎么讲,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如果懂一点古文字,认识就不同了。
《说文解字》上说,救,止也。也就是制止的意思,把火止住了,就叫救火。还有叫“救水”的,就是把水止住了。再比如说我们讲地老天荒,“老”和“荒”是什么意思?现代汉语里未必能讲得清楚,其实这俩字都是久远的意思。正如很边远的地方叫“荒蛮之地”,空间的久、时间的久都可以叫“荒”,比如说瓜长熟了、长老了,菜烧长了、烧老了,它也有长久的意思,所以地老天荒就是天长地久的意思。
可见,古汉语的很多东西并没有死去,因为现代的语言也是从古代的语言发展过来的,过去很多的成语、术语、典故我们当今仍然在用,这是历史文化不能隔断的,也不可以截然分开。所以文言文从这个意义而言,永远不会过时,它永远是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里面存在着,而且具有永久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