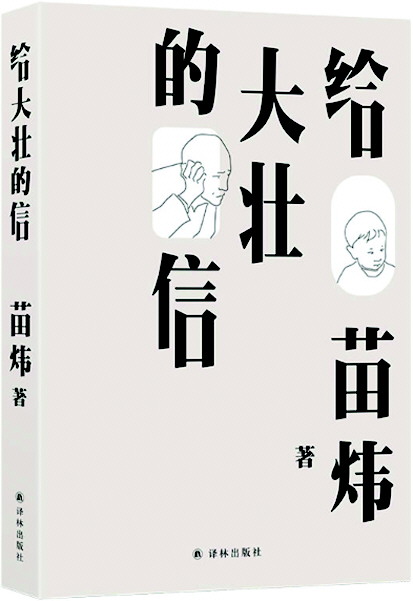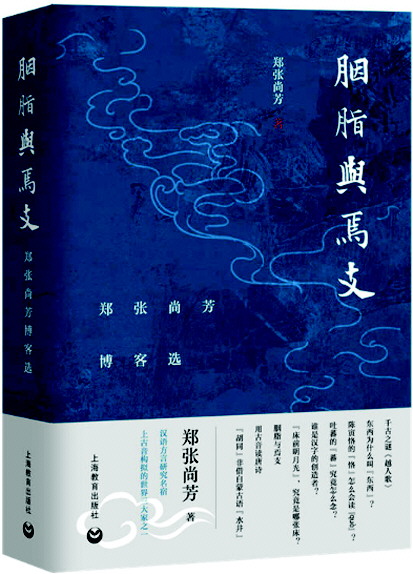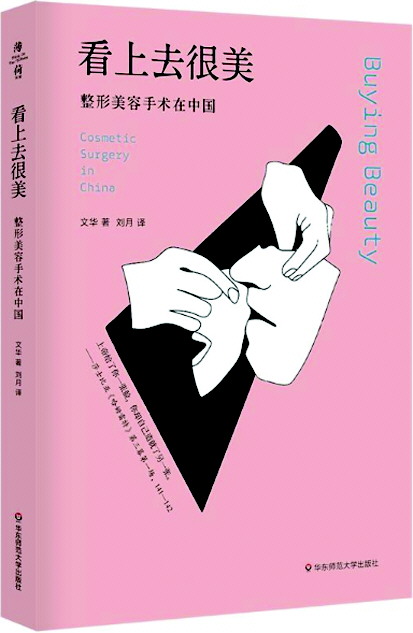以节日的名义
齐鲁晚报 2019年06月29日
□曲鹏
这个即将过去的六月,感觉每天都在过节——儿童节、父亲节、端午节……无论是舶来品,还是传统风俗,总有几本应景的图书吸引着读者。
前《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苗炜因中年得子而变得温柔,会一边趴在地上看着孩子玩一边傻乐。他对儿子最大的期许是当个体育明星,身体健壮压倒一切,所以给儿子起名大壮。三年前,还在陪夫人在月子中心时,苗炜写下了第一封给儿子的信,后来陆陆续续写了三十八封,舒缓从容地讲自己的故事:在少年宫望着跳《小天鹅》的少女,向儿子介绍家里的猫哥哥,讲自己看过的书和仍想要看的书……如今这些文章结成一本集子,就叫《给大壮的信》。这本书不只是写给孩子的,也是写给家长的,“我们这代人都是在传统家庭长大,讲究父母的尊严,讲究孝顺,然后我们当了父母,又觉得应该做那种西方式的开明的父母。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体验,一方面做传统式的儿子闺女,一方面做新式的父母。”这些信也是写给年轻人的,苗炜讲的这些道理,有时看起来是矛盾的——比如要快乐地成长,可悲伤又不可避免,比如要考虑他人的感受,又不用特别在乎他人——我们每个人不都生活在这样的矛盾中吗?
端午之俗早在屈原之前就存在了,是上古时代拜龙图腾的祭典。语言学大家郑张尚芳先生的博客文章《“端午”漫话》从语言学的角度解释了端午节的起源。郑张先生熟稔音韵学、方言学、周边民族语言,对古代历史、古代文学、训诂学、古文字、简帛、历史地理及《周易》等经籍都有研究,他甚至对古人类学也一直保持非常浓厚的兴趣。青年时代,他以一个语言学爱好者的身份刻苦自学,获得王力、袁家骅、吕叔湘、李荣、王辅世等前辈学者的青睐提携,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的古音之旅。2006年,73岁的郑张先生开通博客,以语言文字为主轴,在多个领域内纵横驰骋,各种材料信手拈来,熔于一炉。许多博文破除旧说,正本清源,如《“床前明月光”,究竟是哪张床?》《吐蕃的“蕃”究竟怎么念?》《朝韩语朴姓不读“Piáo”》《“胡”人的原语》《东西为什么叫“东西”?》《张爱玲传播的通俗语源》等篇,纠正了一些流传甚广、影响颇深的谬说。今年为郑张先生逝世一周年,博客选《胭脂与焉支》的出版以为纪念。
对中国传统文化,日本人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十九世纪后半期,大清帝国日益溃败,任凭各式西洋人和东洋人长驱直入。对中国好奇的东洋、西洋学者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其中就有做中国古迹考察的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建筑史专家关野贞来中国较早,1906年至1918年三次到访中国,考察河南、山西、天津、山东、陕西、北京以及江南各地,佛寺道观、皇宫、殿堂、陵墓、民居也都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佛教史专家常盘大定对中国的宗教遗迹格外关注,1920年至1928年进行了五次中国考察,遍及中国南北十几个省市的佛教文化遗迹。志趣相投的关野贞与常盘大定汇集两人考察所得,编了一部有关中国佛教遗迹的图片集,即《中国文化史迹》,近期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引进,翻译整理为十二册《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出版。全书共有2531幅高清图片、120万字解说,囊括当时保存尚好的名胜古迹,很多照片堪称中国史迹、文物存留人间的最后一张写照。梁思成曾把此书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在讲义、著作中多有引用。令人痛心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古迹的考察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关野贞在考察山西天龙山石窟后仅七八年时间,由于日本山中商会的大肆搜购转卖,石窟造像几乎惨遭灭顶之灾。
何为美?2003年,“中国首位人造美女”郝璐璐的整形经历被媒体大量报道,引发公众热烈讨论。第二年,“人造美女”成为流行词汇。那一年,文华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人类学博士,专业是人类学,一位德国朋友看到BBC的报道后问她:太不可思议了!中国发生了什么?文华说那一刻,她无言以对:朋友的震惊态度,映射了当今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外部形象之间的脱节。2006年至2007年,她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关于整容行业的田野调查,写出了博士论文《看上去很美: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整形美容市场之一,整形背后是消费主义对欲望的塑造这一本质依然没变。尽管选择整形美容手术往往被认为是女人虚荣爱美的肤浅表现,但文华认为,这种貌似肤浅的身体实践里嵌入了最彻底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共同书写,隐喻着社会剧变中人们精神上的不安和焦虑以及身体行动上的顺从和抗争。
这个即将过去的六月,感觉每天都在过节——儿童节、父亲节、端午节……无论是舶来品,还是传统风俗,总有几本应景的图书吸引着读者。
前《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苗炜因中年得子而变得温柔,会一边趴在地上看着孩子玩一边傻乐。他对儿子最大的期许是当个体育明星,身体健壮压倒一切,所以给儿子起名大壮。三年前,还在陪夫人在月子中心时,苗炜写下了第一封给儿子的信,后来陆陆续续写了三十八封,舒缓从容地讲自己的故事:在少年宫望着跳《小天鹅》的少女,向儿子介绍家里的猫哥哥,讲自己看过的书和仍想要看的书……如今这些文章结成一本集子,就叫《给大壮的信》。这本书不只是写给孩子的,也是写给家长的,“我们这代人都是在传统家庭长大,讲究父母的尊严,讲究孝顺,然后我们当了父母,又觉得应该做那种西方式的开明的父母。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体验,一方面做传统式的儿子闺女,一方面做新式的父母。”这些信也是写给年轻人的,苗炜讲的这些道理,有时看起来是矛盾的——比如要快乐地成长,可悲伤又不可避免,比如要考虑他人的感受,又不用特别在乎他人——我们每个人不都生活在这样的矛盾中吗?
端午之俗早在屈原之前就存在了,是上古时代拜龙图腾的祭典。语言学大家郑张尚芳先生的博客文章《“端午”漫话》从语言学的角度解释了端午节的起源。郑张先生熟稔音韵学、方言学、周边民族语言,对古代历史、古代文学、训诂学、古文字、简帛、历史地理及《周易》等经籍都有研究,他甚至对古人类学也一直保持非常浓厚的兴趣。青年时代,他以一个语言学爱好者的身份刻苦自学,获得王力、袁家骅、吕叔湘、李荣、王辅世等前辈学者的青睐提携,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的古音之旅。2006年,73岁的郑张先生开通博客,以语言文字为主轴,在多个领域内纵横驰骋,各种材料信手拈来,熔于一炉。许多博文破除旧说,正本清源,如《“床前明月光”,究竟是哪张床?》《吐蕃的“蕃”究竟怎么念?》《朝韩语朴姓不读“Piáo”》《“胡”人的原语》《东西为什么叫“东西”?》《张爱玲传播的通俗语源》等篇,纠正了一些流传甚广、影响颇深的谬说。今年为郑张先生逝世一周年,博客选《胭脂与焉支》的出版以为纪念。
对中国传统文化,日本人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十九世纪后半期,大清帝国日益溃败,任凭各式西洋人和东洋人长驱直入。对中国好奇的东洋、西洋学者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其中就有做中国古迹考察的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建筑史专家关野贞来中国较早,1906年至1918年三次到访中国,考察河南、山西、天津、山东、陕西、北京以及江南各地,佛寺道观、皇宫、殿堂、陵墓、民居也都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佛教史专家常盘大定对中国的宗教遗迹格外关注,1920年至1928年进行了五次中国考察,遍及中国南北十几个省市的佛教文化遗迹。志趣相投的关野贞与常盘大定汇集两人考察所得,编了一部有关中国佛教遗迹的图片集,即《中国文化史迹》,近期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引进,翻译整理为十二册《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出版。全书共有2531幅高清图片、120万字解说,囊括当时保存尚好的名胜古迹,很多照片堪称中国史迹、文物存留人间的最后一张写照。梁思成曾把此书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在讲义、著作中多有引用。令人痛心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古迹的考察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关野贞在考察山西天龙山石窟后仅七八年时间,由于日本山中商会的大肆搜购转卖,石窟造像几乎惨遭灭顶之灾。
何为美?2003年,“中国首位人造美女”郝璐璐的整形经历被媒体大量报道,引发公众热烈讨论。第二年,“人造美女”成为流行词汇。那一年,文华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人类学博士,专业是人类学,一位德国朋友看到BBC的报道后问她:太不可思议了!中国发生了什么?文华说那一刻,她无言以对:朋友的震惊态度,映射了当今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外部形象之间的脱节。2006年至2007年,她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关于整容行业的田野调查,写出了博士论文《看上去很美: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整形美容市场之一,整形背后是消费主义对欲望的塑造这一本质依然没变。尽管选择整形美容手术往往被认为是女人虚荣爱美的肤浅表现,但文华认为,这种貌似肤浅的身体实践里嵌入了最彻底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共同书写,隐喻着社会剧变中人们精神上的不安和焦虑以及身体行动上的顺从和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