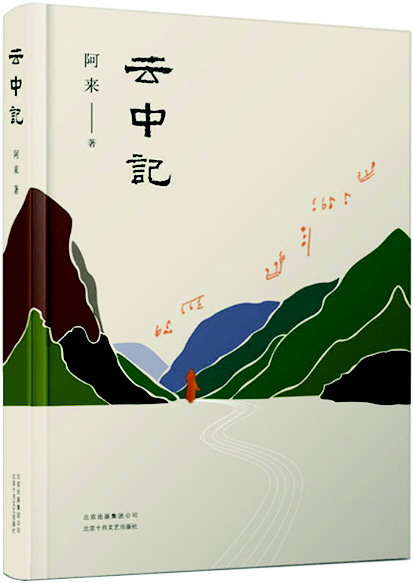阿来:今天谈文学,已经变得很混乱
齐鲁晚报 2019年07月13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师文静
“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云中记》是阿来酝酿十年,为“5·12”汶川地震写的长篇。他说时隔10年,才敢提笔写这一段伤痕,是因为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上拉开距离,才会酝酿出思想和文本的精髓。
阿来说,写作不能写到住院,更不能写到累死,事业的成功是附丽于生命的,生活、生命才是重要的。他还认为,今天谈文学,已经变得很混乱,很多人说成功就讨论这个人挣了多少钱、获了多少奖,这两个都不是文艺本身的标准。
面对死亡,我们把悲伤交给什么
“大地震这种灾难给我间接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阿来不想轻易去写大地震这个题材,如果写不出死亡中升华出来的更高尚的意义、更有价值的生命观,就不要写。
直到大地震十周年,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让阿来突然泪流满面。“半小时后,情绪才稍微平复。我关闭了写了一半的文件。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从开始,我就明确地知道,这个人将要消失,这个村庄也将要消失。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从五月到十月,阿来写完了这个故事。“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了。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一种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
在《云中记》中,汶川地震后,拥有上千年传说的云中村移民到平原,年复一年过去,祭师阿巴感到身上的力气在消散,他要回到那个即将消失的村子,与亡灵为伴。然而,神迹出现了,他创造了一片世外桃源……写灾难,写死亡,但阿来写的不一样,他的文字明朗又通透。祭师阿巴是非遗传承人,他朴实、自然、不神秘,心怀责任。在空无一人的云中村,万物有灵气,阿巴用祭祀的方式安慰亡魂,他对死亡的一切感知都融入自然。云中村消失,阿巴也随之消失,最终与村庄一起归于自然。
阿来认为,死亡应该产生某种价值,应该对仍然活在世上的这些人的生命形成一个洗礼。“我们对死亡除了哭泣、悲伤之外,应该发出另外一种声音。它比死亡的悲痛更高级,是对我们生命有一种洗涤性的神圣的、庄重的、纯净的、美丽的东西。死亡带给人不只痛哭,还有对生命内在的了悟,或是自我深刻的认知。”
上升到死亡的文学书写上,阿来认为,中国文学还存有巨大空间。
在阿来看来,中国文化有一个小缺陷,就是我们其实并不能真正庄重地对待死亡,孔子不愿意讨论死亡,儒家不愿讨论当下除了现实之外、切身之外的任何东西。“《论语》里,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能否讨论一下死亡,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他还有点生气。《论语》中还有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奇怪的东西,神神鬼鬼的东西,孔子是不讨论的,他讨论的是人的生活,儒家有非常务实的情怀。”
但是,阿来认为这种文化传统造成中国人不能真正地观照死亡,充分地对生命本身加以理解。“如果出生值得歌颂,成长值得歌颂,那么死亡作为生命的一个必然的结尾部分,为什么它就不值得歌颂?我们都是唯物主义史观,死亡之后有没有灵魂存在,没有必要讨论,但这种东西却给文学书写带来了一种非常巨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升华生命本身,把生命的体认上升到诗学、哲理性的思考。”阿来认为这种尝试可能是提升他个人文学书写的一个途径,也是提升中国文学某些方面缺陷的途径。
没有职业,作家就会游离于社会
很多作家年轻时就成了职业作家,主要以写作为生,而阿来却从来不是职业作家。开始写小说时,他是四川马尔康县的一名中学教师;在上世纪90年代写《尘埃落定》时,他是文化局的行政干部;而到了写《机村史诗》时,是《科幻世界》杂志的总编辑;《云中记》出版,阿来已任职四川省作协主席六年。有自己的职业,写作对阿来来说一直就是业余状态。“但这并不等于我没有认真写作,不等于我没认真对待其他工作。”
回忆过去的人生,阿来感慨:当老师很有名气,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给他教;当干部差点儿,没有得到很快的提升机会;做杂志的十年间,他带领《科幻世界》杂志打造了产业链和过硬的品牌,并“发现”了当下最好的科幻作家,如刘慈欣、韩松等。
阿来说,一个作家肩负着自身的职业再去写作,并不矛盾,因为作家需要生活,需要真正地在生活中体验。“都说作家要深入生活,但别人的生活怎么深入?别人的钱让你花?若只是在旁边观察别人做什么,拍纪录片即可,不用写小说。文学一定是作家首先自己在生活当中。作家有一个可靠的职业,就是有一个在生活中的可靠的方式。不然,作家就与社会有点儿游离。”
与其他作家七八年、十来年出一部长篇不同,阿来的长篇作品很密集。2000年,41岁的阿来凭《尘埃落定》获茅奖后,又出版长篇地理文化散文《大地的阶梯》,出版80万字长篇小说《空山》(即《机村史诗》),2009年创作完成145万字的“重述神话”系列之《格萨尔王》,此后又完成长篇“非虚构小说”《瞻对》,其间还出版自然文学三部曲《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并且还完成了电影《攀登者》的编剧工作。
工作之余也不全是写作。出生于四川藏区大山中的阿来对于大自然有近乎狂热的爱,经常跋山涉水拍植物,对大自然了然于心,已攒了几万张照片。他说,不认识几十种植物,不要说自己热爱大自然。
而在其他人眼中,阿来的写作富有神性,且无所不能。作家邱华栋把阿来看作一尊“四面佛”,诗歌、散文、小说、非虚构写作信手拈来。作家李舫也说,“阿来总说他喜欢观察,喜欢行走,喜欢勘探,也喜欢在沉吟中思考,还说这是笨办法。其实这是一种写作中还原现场的方式。”
阿来真正写小说的时间并不多,都是下了班之后写的。他还透露,自己写小说往往还要为自己的爱好让路。写《尘埃落定》时,正值美国世界杯,他停下一个多月看足球,比赛结束了再继续写。“我每天写作不超过三个小时。写这么久干什么?这世界上有太多有意思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值得苦哈哈地去完成。有人说,写作写到生病住院,有人说死就是写书写死的。这确实不值得。”
阿来认为,生命本体才最重要,事业的成功是附丽于生命的,生活、生命才是重要的;工作也是重要的,但对于结果,要有正常的、不偏执的认知,“这样在写作中,才能得到一种自在的状态,一旦自在了,就不需要平衡,不需要焦虑,可以随缘、随机。”
钱和奖都不是文艺本身的标准
十年前,“作家富豪榜”刚兴起时,阿来就是榜单上的常客,这种用“年收入”来衡量一个作家价值的方式,让阿来觉得“今天谈文学,已经变得很混乱”。
阿来指出,谈一个作家,首先会介绍他得过什么奖,拿到多少钱,但是文学产生的时代、中国文学产生的时代,都没有版税,没有钱,没有榜单,什么都没有,就是文学本身。“苏东坡写诗歌的年代,写作者自己有钱自己印刷,没有钱,会有朋友赞助,印几百本手抄本,小范围赠送。但很多作品会在整个中国文化圈里不胫而走,不单是穿越当时的空间,而且穿越几千年,流传到今天。还有,《诗经》、《楚辞》、汉乐府诗、《古诗十九首》等,也都不得了。”
阿来坦承自己的情绪有时也会受到评奖、榜单的干扰,但会迅速地换一个思路去想问题。“苏东坡、杜甫靠什么呢?他们还好,至少有名字传世。但《诗经》、汉乐府诗的作品是没有作者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歌唱?凭什么要书写?我相信,我们有对于文辞之美、辞章之美,及背后隐藏的情感之美、认知力量的追求。”
阿来很赞同一位美国作家的观点:好的文学作品,有三个标准,第一是审美的光芒,第二是认知的力量,第三是领悟生命世界秘密的能力。“你说我写作追求什么?我追求的是这些东西。钱只是顺便挣的,不要专门去挣。文艺包含的真善美,是美的形式、善的愿望,通向真,即真理和真相。实现了,就是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今天我们在远离这个标准。很多人说成功就讨论这个人挣了多少钱,获了多少奖,这两个都不是文艺本身的标准。”
谈及对科幻文学的助推和探索的十年经历,阿来也谈了他对文学创作与文化环境的一些认识。阿来表示,做文化市场总有一些人认为必须粗鲁、庸俗、搞笑、暴力,甚至靠色情才能赚钱,无论电影、电视还是文学,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中,成为很多人的信念。“我不太愿意相信文化该是这种情形,通过《科幻世界》最终发行量达到40多万份,我们证明好东西、正面的东西也是赚钱的。”
从文学谈及文化,阿来说,我们比全世界的人都追求物质上的极致,为什么文化上大部分是反的呢?“如果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产生动摇、不相信,这是很恐怖的。满大街捏脚的店比书店还要多,就说明大家不学习,更多是在追求感官享受。”阿来认为,我们的文化修为是从别的途径得不到的,只能从好书中获取。“一定要读好书,因为今天大量的书有着坏的影响。我们需要真正从文化品格上进行阅读、进行思考。”
“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云中记》是阿来酝酿十年,为“5·12”汶川地震写的长篇。他说时隔10年,才敢提笔写这一段伤痕,是因为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上拉开距离,才会酝酿出思想和文本的精髓。
阿来说,写作不能写到住院,更不能写到累死,事业的成功是附丽于生命的,生活、生命才是重要的。他还认为,今天谈文学,已经变得很混乱,很多人说成功就讨论这个人挣了多少钱、获了多少奖,这两个都不是文艺本身的标准。
面对死亡,我们把悲伤交给什么
“大地震这种灾难给我间接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阿来不想轻易去写大地震这个题材,如果写不出死亡中升华出来的更高尚的意义、更有价值的生命观,就不要写。
直到大地震十周年,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让阿来突然泪流满面。“半小时后,情绪才稍微平复。我关闭了写了一半的文件。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从开始,我就明确地知道,这个人将要消失,这个村庄也将要消失。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从五月到十月,阿来写完了这个故事。“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了。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一种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
在《云中记》中,汶川地震后,拥有上千年传说的云中村移民到平原,年复一年过去,祭师阿巴感到身上的力气在消散,他要回到那个即将消失的村子,与亡灵为伴。然而,神迹出现了,他创造了一片世外桃源……写灾难,写死亡,但阿来写的不一样,他的文字明朗又通透。祭师阿巴是非遗传承人,他朴实、自然、不神秘,心怀责任。在空无一人的云中村,万物有灵气,阿巴用祭祀的方式安慰亡魂,他对死亡的一切感知都融入自然。云中村消失,阿巴也随之消失,最终与村庄一起归于自然。
阿来认为,死亡应该产生某种价值,应该对仍然活在世上的这些人的生命形成一个洗礼。“我们对死亡除了哭泣、悲伤之外,应该发出另外一种声音。它比死亡的悲痛更高级,是对我们生命有一种洗涤性的神圣的、庄重的、纯净的、美丽的东西。死亡带给人不只痛哭,还有对生命内在的了悟,或是自我深刻的认知。”
上升到死亡的文学书写上,阿来认为,中国文学还存有巨大空间。
在阿来看来,中国文化有一个小缺陷,就是我们其实并不能真正庄重地对待死亡,孔子不愿意讨论死亡,儒家不愿讨论当下除了现实之外、切身之外的任何东西。“《论语》里,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能否讨论一下死亡,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他还有点生气。《论语》中还有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奇怪的东西,神神鬼鬼的东西,孔子是不讨论的,他讨论的是人的生活,儒家有非常务实的情怀。”
但是,阿来认为这种文化传统造成中国人不能真正地观照死亡,充分地对生命本身加以理解。“如果出生值得歌颂,成长值得歌颂,那么死亡作为生命的一个必然的结尾部分,为什么它就不值得歌颂?我们都是唯物主义史观,死亡之后有没有灵魂存在,没有必要讨论,但这种东西却给文学书写带来了一种非常巨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升华生命本身,把生命的体认上升到诗学、哲理性的思考。”阿来认为这种尝试可能是提升他个人文学书写的一个途径,也是提升中国文学某些方面缺陷的途径。
没有职业,作家就会游离于社会
很多作家年轻时就成了职业作家,主要以写作为生,而阿来却从来不是职业作家。开始写小说时,他是四川马尔康县的一名中学教师;在上世纪90年代写《尘埃落定》时,他是文化局的行政干部;而到了写《机村史诗》时,是《科幻世界》杂志的总编辑;《云中记》出版,阿来已任职四川省作协主席六年。有自己的职业,写作对阿来来说一直就是业余状态。“但这并不等于我没有认真写作,不等于我没认真对待其他工作。”
回忆过去的人生,阿来感慨:当老师很有名气,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给他教;当干部差点儿,没有得到很快的提升机会;做杂志的十年间,他带领《科幻世界》杂志打造了产业链和过硬的品牌,并“发现”了当下最好的科幻作家,如刘慈欣、韩松等。
阿来说,一个作家肩负着自身的职业再去写作,并不矛盾,因为作家需要生活,需要真正地在生活中体验。“都说作家要深入生活,但别人的生活怎么深入?别人的钱让你花?若只是在旁边观察别人做什么,拍纪录片即可,不用写小说。文学一定是作家首先自己在生活当中。作家有一个可靠的职业,就是有一个在生活中的可靠的方式。不然,作家就与社会有点儿游离。”
与其他作家七八年、十来年出一部长篇不同,阿来的长篇作品很密集。2000年,41岁的阿来凭《尘埃落定》获茅奖后,又出版长篇地理文化散文《大地的阶梯》,出版80万字长篇小说《空山》(即《机村史诗》),2009年创作完成145万字的“重述神话”系列之《格萨尔王》,此后又完成长篇“非虚构小说”《瞻对》,其间还出版自然文学三部曲《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并且还完成了电影《攀登者》的编剧工作。
工作之余也不全是写作。出生于四川藏区大山中的阿来对于大自然有近乎狂热的爱,经常跋山涉水拍植物,对大自然了然于心,已攒了几万张照片。他说,不认识几十种植物,不要说自己热爱大自然。
而在其他人眼中,阿来的写作富有神性,且无所不能。作家邱华栋把阿来看作一尊“四面佛”,诗歌、散文、小说、非虚构写作信手拈来。作家李舫也说,“阿来总说他喜欢观察,喜欢行走,喜欢勘探,也喜欢在沉吟中思考,还说这是笨办法。其实这是一种写作中还原现场的方式。”
阿来真正写小说的时间并不多,都是下了班之后写的。他还透露,自己写小说往往还要为自己的爱好让路。写《尘埃落定》时,正值美国世界杯,他停下一个多月看足球,比赛结束了再继续写。“我每天写作不超过三个小时。写这么久干什么?这世界上有太多有意思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值得苦哈哈地去完成。有人说,写作写到生病住院,有人说死就是写书写死的。这确实不值得。”
阿来认为,生命本体才最重要,事业的成功是附丽于生命的,生活、生命才是重要的;工作也是重要的,但对于结果,要有正常的、不偏执的认知,“这样在写作中,才能得到一种自在的状态,一旦自在了,就不需要平衡,不需要焦虑,可以随缘、随机。”
钱和奖都不是文艺本身的标准
十年前,“作家富豪榜”刚兴起时,阿来就是榜单上的常客,这种用“年收入”来衡量一个作家价值的方式,让阿来觉得“今天谈文学,已经变得很混乱”。
阿来指出,谈一个作家,首先会介绍他得过什么奖,拿到多少钱,但是文学产生的时代、中国文学产生的时代,都没有版税,没有钱,没有榜单,什么都没有,就是文学本身。“苏东坡写诗歌的年代,写作者自己有钱自己印刷,没有钱,会有朋友赞助,印几百本手抄本,小范围赠送。但很多作品会在整个中国文化圈里不胫而走,不单是穿越当时的空间,而且穿越几千年,流传到今天。还有,《诗经》、《楚辞》、汉乐府诗、《古诗十九首》等,也都不得了。”
阿来坦承自己的情绪有时也会受到评奖、榜单的干扰,但会迅速地换一个思路去想问题。“苏东坡、杜甫靠什么呢?他们还好,至少有名字传世。但《诗经》、汉乐府诗的作品是没有作者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歌唱?凭什么要书写?我相信,我们有对于文辞之美、辞章之美,及背后隐藏的情感之美、认知力量的追求。”
阿来很赞同一位美国作家的观点:好的文学作品,有三个标准,第一是审美的光芒,第二是认知的力量,第三是领悟生命世界秘密的能力。“你说我写作追求什么?我追求的是这些东西。钱只是顺便挣的,不要专门去挣。文艺包含的真善美,是美的形式、善的愿望,通向真,即真理和真相。实现了,就是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今天我们在远离这个标准。很多人说成功就讨论这个人挣了多少钱,获了多少奖,这两个都不是文艺本身的标准。”
谈及对科幻文学的助推和探索的十年经历,阿来也谈了他对文学创作与文化环境的一些认识。阿来表示,做文化市场总有一些人认为必须粗鲁、庸俗、搞笑、暴力,甚至靠色情才能赚钱,无论电影、电视还是文学,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中,成为很多人的信念。“我不太愿意相信文化该是这种情形,通过《科幻世界》最终发行量达到40多万份,我们证明好东西、正面的东西也是赚钱的。”
从文学谈及文化,阿来说,我们比全世界的人都追求物质上的极致,为什么文化上大部分是反的呢?“如果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产生动摇、不相信,这是很恐怖的。满大街捏脚的店比书店还要多,就说明大家不学习,更多是在追求感官享受。”阿来认为,我们的文化修为是从别的途径得不到的,只能从好书中获取。“一定要读好书,因为今天大量的书有着坏的影响。我们需要真正从文化品格上进行阅读、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