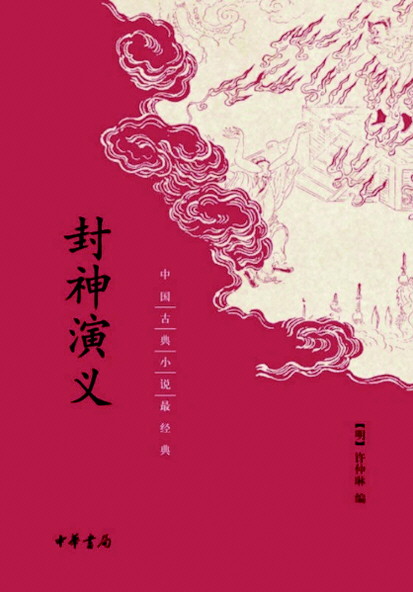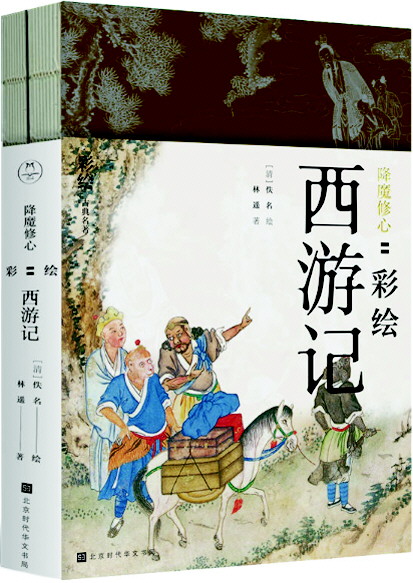哪吒:少年心事
齐鲁晚报 2019年08月10日
□李北山
我和15岁的乐天去看《哪吒之魔童降世》。第二天,他带着妈妈和四岁半的弟弟乐施又去看了一遍。乐天说:“挺好的。”他又找来一段视频给乐施看——
江流儿冲进洗手间撒尿。孙悟空紧随其后。
江流儿:“哪吒是男孩吗?”
孙悟空:“女的。”
这时,哪吒踏着风火轮从他们背后缓缓滑过,站在江流儿右边的小便池旁……
“大圣……”江流儿无限质疑地凑近悟空,小声唤他。
“站着就是男的啦?”被打脸的孙悟空假装不屑地辩解。
江流儿又无限好奇地歪头瞄正在撒尿的哪吒……
这段镜头让乐施笑得岔气。乐施晚上的另一个重要节目,就是抓一个人来,塞给他一把宝剑或者一把大刀,他则耍一阵金箍棒,然后跟人说:“你是妖怪,你要喊孙悟空,上来和我打。”这人就摆好架势喊:“孙悟空!”他却突然冒出一句——
“你孙爷爷在此!”
这是00后的孙悟空和哪吒。
从文学的角度看,《封神演义》远没有《西游记》经典,但它却贡献了哪吒这一经典神话形象,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口口相传,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讲法。有生命力的故事才会成为经典,深藏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它能随世事变迁而生长演化,故事不断被重述,哪吒不断被重塑。
北宋时苏辙就写过一首《那吒》诗——
北方天王有狂子,
只知拜佛不拜父。
佛知其愚难教语,
宝塔令父左手举。
诗中告诉我们,哪吒是佛教中的神祇,而且当时已经有后世哪吒故事的底色,即父子矛盾和天王托塔以镇哪吒。从有关记载中也可发现,在当时已经有哪吒“析骨还肉”的传说。其实到苏辙的时代,哪吒已在佛教中流传几百年,显然已经开始在民间流传,并具备了后世哪吒故事的种种设定。
将哪吒故事最终完善并最终走入民间的,是《西游记》和《封神演义》这两部成书于明代的神魔小说。
《西游记》第八十三回中用白话概略交代了哪吒的来历。其内容与元代所载《三教搜神大全》基本一致,增加说明了哪吒的得名原因,是因为他出生时左手掌上有个“哪”字,右手掌上有个“吒”字。
到了稍晚的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则对哪吒的一生有了更为详细、深入的叙述。书中说哪吒是商朝末期陈塘关总兵李靖的第3个儿子,其妻生下一肉球,李靖以为是妖怪,用剑劈开,里面正是哪吒。哪吒后来被太乙真人收为门徒,因在东海玩水,打死东海龙王的三太子敖丙,龙王兴师问罪。为了不连累父母,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而死。之后托梦其母为其立庙享受烟火,被李靖毁掉庙宇,打烂泥胎。太乙真人用莲花、莲藕助其重生。哪吒后来便助姜子牙兴周灭纣,战功卓著。从此,哪吒由佛入道,亦佛亦道,实现了彻底的民间化。作者大概借用了《西游记》里红孩儿的人设,哪吒从成年人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手持火尖枪的粉雕玉琢的小孩模样,正式成为民间熟知的少年英雄形象。
无论大闹天宫还是哪吒闹海,如果我们细究原著,会发现,孙悟空和哪吒都是具有神异力量的“顽童”,彼时他们是一张白纸,心中还没有规则二字,甚至也没有是非观念,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就是不讲道理,为所欲为。
尽管哪吒在原著《封神演义》中的形象充满了残忍、暴戾、狭隘、睚眦必报、蛮不讲理,但他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一方面,他是如一张白纸的孩子,人们能够容忍一个孩子胡作非为,另一方面,人们发自内心所热爱的,是哪吒所展现出的自我的释放和对权威的挑战。无论天宫还是龙宫,所代表的是权威、秩序和压迫,现在终于有人能够对此不屑一顾,并且大开杀戒,它满足了长期处于人性压抑和生活压迫中的中国人的幻想。在《封神演义》中,老龙王要哪吒偿命,他自刎于陈塘关,但从人性的角度而论,这是“自由”的代价,为所欲为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哪吒闹海》公映,电影中的哪吒已经从那个一张白纸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不屈的英雄。彼时,天旱地裂,东海龙王滴水不降,还命夜叉去海边强抢童男童女。哪吒见义勇为,用乾坤圈打死夜叉,又杀了前来增援的龙王之子敖丙。这既是英雄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电影里矛盾冲突的顶点,是陈塘关的滂沱大雨中,少年哪吒剔骨还父割肉还母,舍命与家庭大决裂:“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这部动画赋予哪吒形象的精神与灵感被竞相解读,也是几代人悲剧美学最重要的教育课程之一。哪吒成了和家庭决裂的“逆子”,他出走的导火索是为了站在苦难的大多数一边,去对抗骄奢淫逸的权贵。他历尽劫波,彻底和伪善的父亲切割关系,到人民中去了。这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呼应。
在40年后的今天,又一部动画电影重述哪吒的故事。这一次,哪吒褪去英雄的光环,还原为原著中的魔童。他凶蛮的内心依然埋着善的种子——其实这粒种子埋藏于每个人的内心,区别在于你能否发现它,让它生根发芽。
这个时代的哪吒故事重新回归中国人的家,似乎在讲一个关于“爱的教育”的现代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最高明的改变,是父权的消解,原本的伪善和冰冷一并被自然地消解了,严父外表下那永恒的宽广的爱展现出来,一切尽在那一句“他是我儿”之中。对一个父亲而言,这一句比“我命由我不由天”更直指人心。在这部暗黑风格的故事中,我们依然喜欢这个满身缺点的孩子,因为他真实,因为我们发现,哪吒的反叛中,其实是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自我的寻找。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何尝不是在这无休止的反叛和和解中寻找自由、塑造自我?哪吒的心事重重,其实是我们每个人不管多大都无法放弃的少年心事。而在一千多年来哪吒的故事中,我们也逐渐体会到,所谓自由,不是在欲望和力量的驱使下为所欲为,而是驾驭自己的欲望和力量去完成使命。所谓自我,就是那个不断自我寻找的过程。
哪吒自它进入民间,成为一个故事开始,就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自由和自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始终围绕着父子之间的矛盾展开,自我与权威、压制与反抗,赋予了这个故事成为经典的张力。哪吒曾经是一个神,那时候他只是他自己;后来,哪吒重新成为一个神,他成为每个人内心的自我之神。
我和15岁的乐天去看《哪吒之魔童降世》。第二天,他带着妈妈和四岁半的弟弟乐施又去看了一遍。乐天说:“挺好的。”他又找来一段视频给乐施看——
江流儿冲进洗手间撒尿。孙悟空紧随其后。
江流儿:“哪吒是男孩吗?”
孙悟空:“女的。”
这时,哪吒踏着风火轮从他们背后缓缓滑过,站在江流儿右边的小便池旁……
“大圣……”江流儿无限质疑地凑近悟空,小声唤他。
“站着就是男的啦?”被打脸的孙悟空假装不屑地辩解。
江流儿又无限好奇地歪头瞄正在撒尿的哪吒……
这段镜头让乐施笑得岔气。乐施晚上的另一个重要节目,就是抓一个人来,塞给他一把宝剑或者一把大刀,他则耍一阵金箍棒,然后跟人说:“你是妖怪,你要喊孙悟空,上来和我打。”这人就摆好架势喊:“孙悟空!”他却突然冒出一句——
“你孙爷爷在此!”
这是00后的孙悟空和哪吒。
从文学的角度看,《封神演义》远没有《西游记》经典,但它却贡献了哪吒这一经典神话形象,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口口相传,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讲法。有生命力的故事才会成为经典,深藏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它能随世事变迁而生长演化,故事不断被重述,哪吒不断被重塑。
北宋时苏辙就写过一首《那吒》诗——
北方天王有狂子,
只知拜佛不拜父。
佛知其愚难教语,
宝塔令父左手举。
诗中告诉我们,哪吒是佛教中的神祇,而且当时已经有后世哪吒故事的底色,即父子矛盾和天王托塔以镇哪吒。从有关记载中也可发现,在当时已经有哪吒“析骨还肉”的传说。其实到苏辙的时代,哪吒已在佛教中流传几百年,显然已经开始在民间流传,并具备了后世哪吒故事的种种设定。
将哪吒故事最终完善并最终走入民间的,是《西游记》和《封神演义》这两部成书于明代的神魔小说。
《西游记》第八十三回中用白话概略交代了哪吒的来历。其内容与元代所载《三教搜神大全》基本一致,增加说明了哪吒的得名原因,是因为他出生时左手掌上有个“哪”字,右手掌上有个“吒”字。
到了稍晚的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则对哪吒的一生有了更为详细、深入的叙述。书中说哪吒是商朝末期陈塘关总兵李靖的第3个儿子,其妻生下一肉球,李靖以为是妖怪,用剑劈开,里面正是哪吒。哪吒后来被太乙真人收为门徒,因在东海玩水,打死东海龙王的三太子敖丙,龙王兴师问罪。为了不连累父母,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而死。之后托梦其母为其立庙享受烟火,被李靖毁掉庙宇,打烂泥胎。太乙真人用莲花、莲藕助其重生。哪吒后来便助姜子牙兴周灭纣,战功卓著。从此,哪吒由佛入道,亦佛亦道,实现了彻底的民间化。作者大概借用了《西游记》里红孩儿的人设,哪吒从成年人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手持火尖枪的粉雕玉琢的小孩模样,正式成为民间熟知的少年英雄形象。
无论大闹天宫还是哪吒闹海,如果我们细究原著,会发现,孙悟空和哪吒都是具有神异力量的“顽童”,彼时他们是一张白纸,心中还没有规则二字,甚至也没有是非观念,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就是不讲道理,为所欲为。
尽管哪吒在原著《封神演义》中的形象充满了残忍、暴戾、狭隘、睚眦必报、蛮不讲理,但他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一方面,他是如一张白纸的孩子,人们能够容忍一个孩子胡作非为,另一方面,人们发自内心所热爱的,是哪吒所展现出的自我的释放和对权威的挑战。无论天宫还是龙宫,所代表的是权威、秩序和压迫,现在终于有人能够对此不屑一顾,并且大开杀戒,它满足了长期处于人性压抑和生活压迫中的中国人的幻想。在《封神演义》中,老龙王要哪吒偿命,他自刎于陈塘关,但从人性的角度而论,这是“自由”的代价,为所欲为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哪吒闹海》公映,电影中的哪吒已经从那个一张白纸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不屈的英雄。彼时,天旱地裂,东海龙王滴水不降,还命夜叉去海边强抢童男童女。哪吒见义勇为,用乾坤圈打死夜叉,又杀了前来增援的龙王之子敖丙。这既是英雄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电影里矛盾冲突的顶点,是陈塘关的滂沱大雨中,少年哪吒剔骨还父割肉还母,舍命与家庭大决裂:“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这部动画赋予哪吒形象的精神与灵感被竞相解读,也是几代人悲剧美学最重要的教育课程之一。哪吒成了和家庭决裂的“逆子”,他出走的导火索是为了站在苦难的大多数一边,去对抗骄奢淫逸的权贵。他历尽劫波,彻底和伪善的父亲切割关系,到人民中去了。这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呼应。
在40年后的今天,又一部动画电影重述哪吒的故事。这一次,哪吒褪去英雄的光环,还原为原著中的魔童。他凶蛮的内心依然埋着善的种子——其实这粒种子埋藏于每个人的内心,区别在于你能否发现它,让它生根发芽。
这个时代的哪吒故事重新回归中国人的家,似乎在讲一个关于“爱的教育”的现代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最高明的改变,是父权的消解,原本的伪善和冰冷一并被自然地消解了,严父外表下那永恒的宽广的爱展现出来,一切尽在那一句“他是我儿”之中。对一个父亲而言,这一句比“我命由我不由天”更直指人心。在这部暗黑风格的故事中,我们依然喜欢这个满身缺点的孩子,因为他真实,因为我们发现,哪吒的反叛中,其实是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自我的寻找。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何尝不是在这无休止的反叛和和解中寻找自由、塑造自我?哪吒的心事重重,其实是我们每个人不管多大都无法放弃的少年心事。而在一千多年来哪吒的故事中,我们也逐渐体会到,所谓自由,不是在欲望和力量的驱使下为所欲为,而是驾驭自己的欲望和力量去完成使命。所谓自我,就是那个不断自我寻找的过程。
哪吒自它进入民间,成为一个故事开始,就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自由和自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始终围绕着父子之间的矛盾展开,自我与权威、压制与反抗,赋予了这个故事成为经典的张力。哪吒曾经是一个神,那时候他只是他自己;后来,哪吒重新成为一个神,他成为每个人内心的自我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