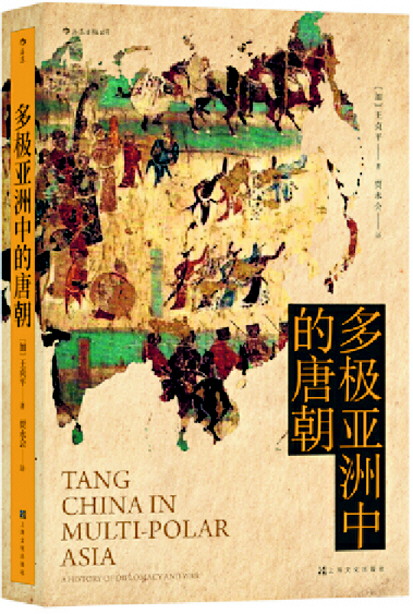唐朝的外交智慧
齐鲁晚报 2020年07月25日
□王贞平
在多极世界中,直接以武力处理对外关系收效有限,而以软实力解决相关问题则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唐廷官员因此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外交战略。他们将“知己知彼”作为首要原则,以反映唐与外部世界的变化。他们竭力避免前人因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犯下的种种错误,如想象而不是理解四邻,认为四邻不是敌视中原王朝的价值观,就是对其不屑一顾;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当成一出道德剧,舞台上只有拥护或反对中原王朝两种角色。
唐朝君臣在审视对外关系时,试图跨越文化隔阂,不带道德偏见地看待事实。高祖和太宗最先摒弃了对突厥的刻板印象。他们在了解了突厥的政治制度、各部首领间微妙的权力关系后意识到,突厥联盟本质上是流动、多变的,权力分散在各部首领手中,而非集中在可汗手里。因此,当突厥武力进犯中原时,各部多各行其是,缺乏步调一致的行动。虽然突厥可汗往往对中原抱有极大野心,但他无法向其他部落首领保证每次由他发起的军事行动都一定会取得成功。如果行动遭遇挫折或失败,他的领导地位就会动摇。由于无法犒赏和保护其追随者,他很容易受到内部摩擦或内战的影响。唐廷重视突厥各部的细微差别,避免视其为一体,并充分利用突厥联盟的弱点,瓦解其阵营。唐廷曾数次离间突厥各部或是突厥与其盟友的关系,阻止其采取联合行动,从而化解了突厥的攻势。
唐代统治精英十分了解游牧民族和边疆社会。游牧民族四处迁徙,逐水草而居。他们根据自身与唐的实力对比,时而臣服唐廷,协助唐的军事行动,时而反叛唐廷或调整与其他游牧部落的关系。唐人与游牧民族杂居的边疆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的人比中原百姓受到的约束更少。他们相当自由地从一地迁居到另一地,经常对各个试图统治他们的政权都表示效忠。无序流动和多重效忠因而成为边疆社会及其民众的特点。唐代统治精英非常清楚,流动性是边疆游牧社会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常态,因为他们的祖先就出自那里。不过,他们常常以贬低性的言辞来表达对游牧民特有的流动性的认识。他们声称,游牧民贪婪、鲁莽,不知忠诚和友谊为何物,对礼仪更是一窍不通。
对辽阔边疆地区及其民众流动性的洞识成为唐朝防御战略的基础。唐朝官员清醒地认识到,游牧民的流动性和唐廷有限的资源导致唐无法永远维持对边疆地区的直接控制。与其划疆定界,不如对边疆地区实行松散管理,只在战略要地修城筑墙。不过,修筑防御工事不是要将敌人拒之于门外,而主要是监视敌人的动向,并提醒朝廷可能的入侵。如果确实是入侵,唐军便退入城中固守,并伺机组织反击。
这种防御战略预示着唐朝的对外关系会经常处于“不战不和”的不稳定状态。由于唐和它的敌人都既无力承担旷日持久的战争,也无法维持永远的和平,因此即便在唐占据相对优势时,双方也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唐廷为确保更大的外围地区的安全而设置了“羁縻州”,由降附或被击败的部落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这些部落首领依然保有对本部落的统治权,但须接受唐朝官员的监督。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间接统治策略,基于精明的计算——既然唐廷对边境部落的军事胜利和失败的部落首领的政治效忠都是暂时的,那么无论是将这些地区正式纳入唐朝的区划,还是用唐朝的行政管理体制取代当地的统治机构,都是不明智的。唐军虽然能取得一时的胜利,但未必可以永远取胜。而“羁縻”制度则可以使唐廷灵活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使投降的部落再次反叛,唐廷也能从容应对。
唐朝君臣按照“知己”的原则仔细评估自身的优势和拥有的资源,并因此确定了外交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他们还得出结论,唐朝若对四邻的利益置之不理,则不可能有效促进自身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和谐”,或称“相互的一己利益”。这一观念强调,唐朝官员必须对某个时期唐与四邻的实力对比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宜的对外政策。这样的政策是最有效的,因为它可以带来相关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这种强调“合宜”“功效”的处理外交问题的方式,看似违背了唐廷一贯用来为自己的外交动机和行为辩护的“德”“义”等普遍道德原则;但实际上,唐朝战略思维的“合宜”“功效”和作为道德诫命的“德”“义”是并行不悖的,因为适用于某时某地某个具体情况的对外政策正是“德”“义”等抽象道德原则的表现。在这种政策指导下的国家行为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因为它体现了政治的最高道德——在行动之前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毕竟,政治道德是以结果来评价政策的。
从上述讨论可见,唐朝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实用多元主义,而不是某一位皇帝对世界的宏大道德构想,这种教条式的构想显然不足以成为观察多元世界的工具。尽管唐廷惯于用一种普世性的道德目的论来包装其对外政策,但这些政策实际上是以理想主义为表,以务实主义为里,是道德原则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是逐渐改变和调整的产物。这些改变与意识形态偏好无关,其本质是演进的,目的是使唐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因此,我们如果想要了解唐在处理与四邻复杂多变的关系时,如何制定出协调、均衡的对外政策,以达到双赢的结果,就必须从多极、相互的一己利益、相互依存、合宜的视角考察唐与四邻的关系。
(节选自《多极亚洲中的唐朝》,标题为编者所加)
国际知名唐史专家王贞平教授解读大唐三百年军事外交的《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中文版近日出版。唐王朝在将近两百九十年的统治期间,与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突厥、回鹘(原名回纥,788年改为回鹘)、吐蕃及南诏的关系跌宕起伏,经历了从和平共处到公开交战的种种变化。这些政权相继崛起,除了回鹘,其他转而成为唐朝的主要对手。王贞平教授以“多极”作为研究唐朝复杂外交关系的分析工具,考察了唐与四邻的关系。
在多极世界中,直接以武力处理对外关系收效有限,而以软实力解决相关问题则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唐廷官员因此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外交战略。他们将“知己知彼”作为首要原则,以反映唐与外部世界的变化。他们竭力避免前人因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犯下的种种错误,如想象而不是理解四邻,认为四邻不是敌视中原王朝的价值观,就是对其不屑一顾;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当成一出道德剧,舞台上只有拥护或反对中原王朝两种角色。
唐朝君臣在审视对外关系时,试图跨越文化隔阂,不带道德偏见地看待事实。高祖和太宗最先摒弃了对突厥的刻板印象。他们在了解了突厥的政治制度、各部首领间微妙的权力关系后意识到,突厥联盟本质上是流动、多变的,权力分散在各部首领手中,而非集中在可汗手里。因此,当突厥武力进犯中原时,各部多各行其是,缺乏步调一致的行动。虽然突厥可汗往往对中原抱有极大野心,但他无法向其他部落首领保证每次由他发起的军事行动都一定会取得成功。如果行动遭遇挫折或失败,他的领导地位就会动摇。由于无法犒赏和保护其追随者,他很容易受到内部摩擦或内战的影响。唐廷重视突厥各部的细微差别,避免视其为一体,并充分利用突厥联盟的弱点,瓦解其阵营。唐廷曾数次离间突厥各部或是突厥与其盟友的关系,阻止其采取联合行动,从而化解了突厥的攻势。
唐代统治精英十分了解游牧民族和边疆社会。游牧民族四处迁徙,逐水草而居。他们根据自身与唐的实力对比,时而臣服唐廷,协助唐的军事行动,时而反叛唐廷或调整与其他游牧部落的关系。唐人与游牧民族杂居的边疆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的人比中原百姓受到的约束更少。他们相当自由地从一地迁居到另一地,经常对各个试图统治他们的政权都表示效忠。无序流动和多重效忠因而成为边疆社会及其民众的特点。唐代统治精英非常清楚,流动性是边疆游牧社会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常态,因为他们的祖先就出自那里。不过,他们常常以贬低性的言辞来表达对游牧民特有的流动性的认识。他们声称,游牧民贪婪、鲁莽,不知忠诚和友谊为何物,对礼仪更是一窍不通。
对辽阔边疆地区及其民众流动性的洞识成为唐朝防御战略的基础。唐朝官员清醒地认识到,游牧民的流动性和唐廷有限的资源导致唐无法永远维持对边疆地区的直接控制。与其划疆定界,不如对边疆地区实行松散管理,只在战略要地修城筑墙。不过,修筑防御工事不是要将敌人拒之于门外,而主要是监视敌人的动向,并提醒朝廷可能的入侵。如果确实是入侵,唐军便退入城中固守,并伺机组织反击。
这种防御战略预示着唐朝的对外关系会经常处于“不战不和”的不稳定状态。由于唐和它的敌人都既无力承担旷日持久的战争,也无法维持永远的和平,因此即便在唐占据相对优势时,双方也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唐廷为确保更大的外围地区的安全而设置了“羁縻州”,由降附或被击败的部落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这些部落首领依然保有对本部落的统治权,但须接受唐朝官员的监督。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间接统治策略,基于精明的计算——既然唐廷对边境部落的军事胜利和失败的部落首领的政治效忠都是暂时的,那么无论是将这些地区正式纳入唐朝的区划,还是用唐朝的行政管理体制取代当地的统治机构,都是不明智的。唐军虽然能取得一时的胜利,但未必可以永远取胜。而“羁縻”制度则可以使唐廷灵活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使投降的部落再次反叛,唐廷也能从容应对。
唐朝君臣按照“知己”的原则仔细评估自身的优势和拥有的资源,并因此确定了外交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他们还得出结论,唐朝若对四邻的利益置之不理,则不可能有效促进自身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和谐”,或称“相互的一己利益”。这一观念强调,唐朝官员必须对某个时期唐与四邻的实力对比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宜的对外政策。这样的政策是最有效的,因为它可以带来相关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这种强调“合宜”“功效”的处理外交问题的方式,看似违背了唐廷一贯用来为自己的外交动机和行为辩护的“德”“义”等普遍道德原则;但实际上,唐朝战略思维的“合宜”“功效”和作为道德诫命的“德”“义”是并行不悖的,因为适用于某时某地某个具体情况的对外政策正是“德”“义”等抽象道德原则的表现。在这种政策指导下的国家行为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因为它体现了政治的最高道德——在行动之前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毕竟,政治道德是以结果来评价政策的。
从上述讨论可见,唐朝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实用多元主义,而不是某一位皇帝对世界的宏大道德构想,这种教条式的构想显然不足以成为观察多元世界的工具。尽管唐廷惯于用一种普世性的道德目的论来包装其对外政策,但这些政策实际上是以理想主义为表,以务实主义为里,是道德原则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是逐渐改变和调整的产物。这些改变与意识形态偏好无关,其本质是演进的,目的是使唐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因此,我们如果想要了解唐在处理与四邻复杂多变的关系时,如何制定出协调、均衡的对外政策,以达到双赢的结果,就必须从多极、相互的一己利益、相互依存、合宜的视角考察唐与四邻的关系。
(节选自《多极亚洲中的唐朝》,标题为编者所加)
国际知名唐史专家王贞平教授解读大唐三百年军事外交的《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中文版近日出版。唐王朝在将近两百九十年的统治期间,与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突厥、回鹘(原名回纥,788年改为回鹘)、吐蕃及南诏的关系跌宕起伏,经历了从和平共处到公开交战的种种变化。这些政权相继崛起,除了回鹘,其他转而成为唐朝的主要对手。王贞平教授以“多极”作为研究唐朝复杂外交关系的分析工具,考察了唐与四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