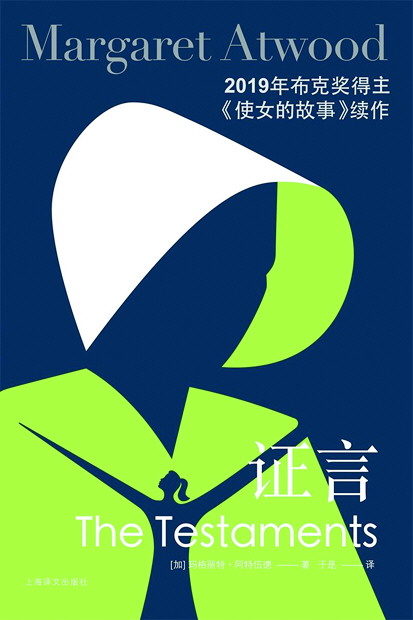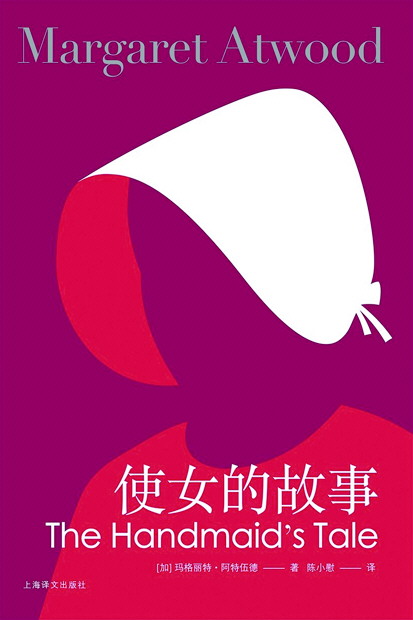总有无法被驯服的人
齐鲁晚报 2020年08月29日
全球畅销书《使女的故事》出版35年后,80岁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2019年发布的新作《证言》(The Testaments),并凭借《证言》再度摘获布克奖,成为布克奖历史上获奖年龄最高的作家。
作为《证言》的前身,《使女的故事》讲述了20世纪末美国在一起政变之后成了由男性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基列共和国”(简称“基列国”),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通过录音叙述自己被迫成为生育机器“使女”后的种种经历。根据《使女的故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已上映三季,数以亿计的观众和读者开始关注《使女的故事》原著,试图探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当年写作的想法,包括基列共和国到底是如何运作的等细节性问题。这些成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新作《证言》的灵感来源。
□于是
《证言》和三十五年前的《使女的故事》具有同样的结构:小说主体由一个世纪以后的历史学家发现的手写材料组成;材料本身是以第一人称重述二十一世纪初的基列共和国的内幕。《证言》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由丽迪亚嬷嬷手写的。这不出人意料,因为只有嬷嬷还能看书写字,基列剥夺了其他女性的一切知识权,连超市购物都是用图片说明的,明令禁止女人接触语言、文字、书本,但教学依然进行——教的是花艺、女红之类的内容,以及政教合一的体制必定会灌输给下一代的宗教意识形态;他们会篡改、添加《圣经》原文,不难想象,对下一代的教育不可能是启蒙性的,而势必是遮人耳目的洗脑式教育。
奥芙弗雷德会在口述事实的同时加入回忆和想象,因而使《使女的故事》拥有丰富性:她身为使女受苦的同时也在自省和观察,感受到身为大主教、主教夫人、马大和守卫的各种人的压抑和凄楚;她既是“行走的子宫”,同时也在奴隶、反抗者、统治者的各种他者中间体察到了愧疚、无奈、麻木和欲望;她不是一味地屈从,心里始终在寻找出路,相信她会走出这个世界;她认知到自己的渴望和软弱……借她一人之眼,作者披露了基列的日常生活,而诸如“过去这里有过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但现在再也见不到律师,大学也关闭了”这样的巨变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使女的故事》用诗意的、残酷的语言讲述了被生殖器化的女性在精神上、身体上的痛苦。
《证言》则以丽迪亚嬷嬷之口,重述了那样的巨变是如何发生的,记录真相的方式也与使女有所不同:奥芙弗雷德的自述更感性,视野相对封闭;而身为开国元勋、拥有大权的丽迪亚嬷嬷的叙述更理性,格局相对开阔,爆料更多,要应对的矛盾也更复杂。她的正义源自复仇,而非意识形态;她的狠毒源自理性,而非天性;而她的善良不得不掩藏在最深处,是盔甲里最薄弱的软肋——但只要综观前后两本书就会发现,她始终不曾卸下那层盔甲。套用格里尔《女太监》中的概念来说,这个经历了大反转、亦正亦邪的人物既是被男权专制机器暴力统治的被阉割的女性,也不得不扮演了阉割她人的角色,制定女界规范,哪怕其本意旨在于有限范围内对女性群体加以保护,实质上也确实是专制机器的帮凶。
《证言》还有另外两个第一人称的叙述声音:一个是在基列长大的艾格尼丝,另一个是在加拿大长大的妮可。就代际而言,三代女性对应了“前基列—基列—后基列”时代,就此扩展了名为“基列”的虚构时空。
妮可似乎生活在另一个平行世界:没有二十一世纪的互联网,没有我们所知的那些高科技玩意儿,更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春期的妮可担负了重任:不仅是信使、是证人,还承担了让本书有亮色、有欢笑的职责。妮可代表了民主自由教育下的健康少女,但不是假大空的脸谱人物,她的胆怯、善良、天真、正义最终融汇成一种生猛的力量,催生出了勇敢。
与妮可相比,艾格尼丝的性格就要复杂多了。丽迪亚嬷嬷在前作中就讲过,“到你们下一代就容易多了。她们会心甘情愿接受自己的职责”。艾格尼丝就是基列的“新一代”,从小受的就是基列的教育,但她并不心甘情愿,反而备受困扰,因为基列的婚姻制度根本只是暴政的工具,只会让每个家庭分崩离析,每个家庭成员都不可能得到幸福。
在艾格尼丝生活的时代里,基列有外忧——在打仗,但表面上没有内患——显然是在几次大肃清之间,她看到的是正常的,甚至也有爱的家国。艾格尼丝的重要性还在于,我们能以她的视角看到马大们、年轻女生、准新娘们、嬷嬷们等一众女性的生活实况:她们全都压抑着真正的身心感受,在自我审查、自我保护中如履薄冰。她们的状态最能映衬出基列是何等畸形——但坦白地说,那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那些女性间的互相倾轧存在于任何形态的社会,是从属于人性本身的卑劣。
基列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因为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终究是容易满足的:文盲可以生活得很好,甚至可以通过婚姻(无论真假)得到财富、荣誉和其它特权;平庸的恶人不仅能幸存,还可能存活得最久……有智力的人未必有理性,现代未必是文明的保证;判断力往往会屈服于生存的基本需求,但理性会让一个人在幸存所意味的屈辱隐忍乃至违背本心的同时,在内心保持自己的判断力,在受到迫害、继而规避迫害的同时策划反抗或复仇。
看到这一页的读者应该已知道了:基列必亡。阿特伍德给出了终点,这显然是包括尼尔·盖曼在内的很多读者这次感觉到“希望”的原因。只是,亚里士多德说过:“以后的确定性在于从以前的迷惑中解脱出来,我们如果不知道症结在什么地方,就无法从中解脱出来”;而丽迪亚嬷嬷曾说过:“从前那个社会毁就毁在有太多选择。”这个症结在《证言》结束前尚未得到解决方案——但小说至少用排除法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即便“从前那个社会”破坏生态、生育力低下、有各种各样的堕落问题,但终究是比基列要好一点。小说不负责给出现实世界的解决方案,但愿新一代读者能找出避免走向“从前那个社会”的道路。
(本文选自《证言》译者序,内容有删节)
作为《证言》的前身,《使女的故事》讲述了20世纪末美国在一起政变之后成了由男性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基列共和国”(简称“基列国”),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通过录音叙述自己被迫成为生育机器“使女”后的种种经历。根据《使女的故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已上映三季,数以亿计的观众和读者开始关注《使女的故事》原著,试图探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当年写作的想法,包括基列共和国到底是如何运作的等细节性问题。这些成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新作《证言》的灵感来源。
□于是
《证言》和三十五年前的《使女的故事》具有同样的结构:小说主体由一个世纪以后的历史学家发现的手写材料组成;材料本身是以第一人称重述二十一世纪初的基列共和国的内幕。《证言》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由丽迪亚嬷嬷手写的。这不出人意料,因为只有嬷嬷还能看书写字,基列剥夺了其他女性的一切知识权,连超市购物都是用图片说明的,明令禁止女人接触语言、文字、书本,但教学依然进行——教的是花艺、女红之类的内容,以及政教合一的体制必定会灌输给下一代的宗教意识形态;他们会篡改、添加《圣经》原文,不难想象,对下一代的教育不可能是启蒙性的,而势必是遮人耳目的洗脑式教育。
奥芙弗雷德会在口述事实的同时加入回忆和想象,因而使《使女的故事》拥有丰富性:她身为使女受苦的同时也在自省和观察,感受到身为大主教、主教夫人、马大和守卫的各种人的压抑和凄楚;她既是“行走的子宫”,同时也在奴隶、反抗者、统治者的各种他者中间体察到了愧疚、无奈、麻木和欲望;她不是一味地屈从,心里始终在寻找出路,相信她会走出这个世界;她认知到自己的渴望和软弱……借她一人之眼,作者披露了基列的日常生活,而诸如“过去这里有过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但现在再也见不到律师,大学也关闭了”这样的巨变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使女的故事》用诗意的、残酷的语言讲述了被生殖器化的女性在精神上、身体上的痛苦。
《证言》则以丽迪亚嬷嬷之口,重述了那样的巨变是如何发生的,记录真相的方式也与使女有所不同:奥芙弗雷德的自述更感性,视野相对封闭;而身为开国元勋、拥有大权的丽迪亚嬷嬷的叙述更理性,格局相对开阔,爆料更多,要应对的矛盾也更复杂。她的正义源自复仇,而非意识形态;她的狠毒源自理性,而非天性;而她的善良不得不掩藏在最深处,是盔甲里最薄弱的软肋——但只要综观前后两本书就会发现,她始终不曾卸下那层盔甲。套用格里尔《女太监》中的概念来说,这个经历了大反转、亦正亦邪的人物既是被男权专制机器暴力统治的被阉割的女性,也不得不扮演了阉割她人的角色,制定女界规范,哪怕其本意旨在于有限范围内对女性群体加以保护,实质上也确实是专制机器的帮凶。
《证言》还有另外两个第一人称的叙述声音:一个是在基列长大的艾格尼丝,另一个是在加拿大长大的妮可。就代际而言,三代女性对应了“前基列—基列—后基列”时代,就此扩展了名为“基列”的虚构时空。
妮可似乎生活在另一个平行世界:没有二十一世纪的互联网,没有我们所知的那些高科技玩意儿,更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春期的妮可担负了重任:不仅是信使、是证人,还承担了让本书有亮色、有欢笑的职责。妮可代表了民主自由教育下的健康少女,但不是假大空的脸谱人物,她的胆怯、善良、天真、正义最终融汇成一种生猛的力量,催生出了勇敢。
与妮可相比,艾格尼丝的性格就要复杂多了。丽迪亚嬷嬷在前作中就讲过,“到你们下一代就容易多了。她们会心甘情愿接受自己的职责”。艾格尼丝就是基列的“新一代”,从小受的就是基列的教育,但她并不心甘情愿,反而备受困扰,因为基列的婚姻制度根本只是暴政的工具,只会让每个家庭分崩离析,每个家庭成员都不可能得到幸福。
在艾格尼丝生活的时代里,基列有外忧——在打仗,但表面上没有内患——显然是在几次大肃清之间,她看到的是正常的,甚至也有爱的家国。艾格尼丝的重要性还在于,我们能以她的视角看到马大们、年轻女生、准新娘们、嬷嬷们等一众女性的生活实况:她们全都压抑着真正的身心感受,在自我审查、自我保护中如履薄冰。她们的状态最能映衬出基列是何等畸形——但坦白地说,那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那些女性间的互相倾轧存在于任何形态的社会,是从属于人性本身的卑劣。
基列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因为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终究是容易满足的:文盲可以生活得很好,甚至可以通过婚姻(无论真假)得到财富、荣誉和其它特权;平庸的恶人不仅能幸存,还可能存活得最久……有智力的人未必有理性,现代未必是文明的保证;判断力往往会屈服于生存的基本需求,但理性会让一个人在幸存所意味的屈辱隐忍乃至违背本心的同时,在内心保持自己的判断力,在受到迫害、继而规避迫害的同时策划反抗或复仇。
看到这一页的读者应该已知道了:基列必亡。阿特伍德给出了终点,这显然是包括尼尔·盖曼在内的很多读者这次感觉到“希望”的原因。只是,亚里士多德说过:“以后的确定性在于从以前的迷惑中解脱出来,我们如果不知道症结在什么地方,就无法从中解脱出来”;而丽迪亚嬷嬷曾说过:“从前那个社会毁就毁在有太多选择。”这个症结在《证言》结束前尚未得到解决方案——但小说至少用排除法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即便“从前那个社会”破坏生态、生育力低下、有各种各样的堕落问题,但终究是比基列要好一点。小说不负责给出现实世界的解决方案,但愿新一代读者能找出避免走向“从前那个社会”的道路。
(本文选自《证言》译者序,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