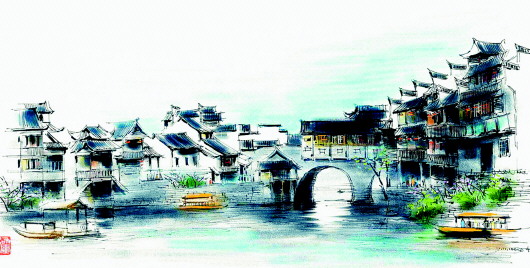敞开的心灵和人生教育
——张新颖讲沈从文《从文自传》
齐鲁晚报 2020年09月14日
1932年,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国文系做讲师,暑假期间用三个星期写了一本书,叫《从文自传》。这一年他三十岁,这本书写的是他二十一岁以前的事情,写到他离开湘西闯荡进北京就戛然而止。
《从文自传》可以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的背景在小城凤凰,主要是一个小学生的生活,重点却不是读书,而是逃学读社会这本大书,作者自己说这一部分可以称作“顽童自传”;后一部分是一个小兵的生活,他十五岁离开了凤凰和家庭,进入更大也更加严酷的社会,随部队辗转,在各种各样的见闻和遭遇中成长。
沈从文把他所有的经历都看作是对他的人生“教育”,而他的心灵状态,是敞开来去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其中最重要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一是自然现象,二是人生现象,三是人类智慧的光辉。
沈从文从小就有强烈的兴趣和冲动去读自然和社会这部大书。他说,“同一切自然相亲近”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他叙述自己逃学的“顽劣事迹”,不仅仅是要表现一个“顽劣”的性格,而是要描述和说明自己因此而得到的教育。这种教育,要宽阔得多,也更根本,更深入骨髓。它是以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为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大书而进行的不停息的自我教育过程。“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
从一开始,这颗向宽广世界敞开的小小心灵,就被这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带进了永远不会满足也就永远停不下来的探寻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小小的心灵变得越来越充实,越来越阔大。“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答解。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在叙述人生现象的“教育”时,沈从文描述了一种特别的经验:看杀人。他说:“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个作家这么多次地写到这么大规模的砍头式杀人,也没有哪个作家能控制得这么“不动声色”地写看杀人。
他这样写,是冷漠和麻木吗?如果看杀人只是看杀人而没有对自己实实在在的影响,真正地无动于衷,那么,他就是一个鲁迅所说意义上的“看客”;而沈从文想表达的却是,看杀人深刻地“教育”了自己,成为建构自己人生观念的重要因素;有这样的因素参与建构的一个人,与没有此类因素参与建构、没有受过同样“教育”的其他人,当然有着无法泯灭的区别。
所以,他在叙述怀化镇的生活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情况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
除了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建构生命的另一种东西,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变换着形式出现,而且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和沉潜的影响力,这种东西,沈从文把它称为人类智慧的光辉。
他在当兵时期接触到外国文学,姨父家中有两大箱商务印行的《说部丛书》。他谈到这些书时曾这样说:
这些书便轮流作了我最好的朋友。我记得迭更司的《冰雪姻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书,反复约占去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我欢喜这种书,因为它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它不如别的书说道理,它只记下一些现象……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
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特质。
沈从文一个月大概有三四块钱,可是随身带的包袱里,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这份产业现在说来,依然是很动人的。”在《从文自传》里面,这个细节特别打动我。
后来,他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
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那时候从长沙来了个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印刷工人,带来些新书新杂志,沈从文很快就对新书“投了降”,“喜欢看《新潮》《改造》了。”“为了读这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
他做出一个决定,到北京去。没过多久,他就在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簿上,写下——“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我们回头来看沈从文离开湘西时初步形成的知识文化结构。
这其中,有中国古代的历史和艺术,他把在陈渠珍身边做书记的军部称为“学历史的地方”;当然有中国古代文学,也有意外碰到的西洋“说部”;还有刚刚开始接触便产生实际影响的“新文化”。
我们在讲沈从文的传奇时,特别喜欢说到沈从文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好像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可是当我们看到他有着这样一个知识结构的时候,我们太爱好传奇了,可能要把他实际有的知识结构缩小到很小,才使那个传奇更加传奇。可是实际情形可能不是这样的。
特别是,当二十一岁的军中书记从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中感受人类智慧的光辉时,当三十岁的小说家自传写到“学历史的地方”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他一定没有想到,他的后半生,是历史博物馆的馆员,一个最终取得辉煌成就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和学者。我们或许应该想到生命的奇妙,想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为未来的历史埋下的伏笔。
当这部自传结束的时候,传主的形象已经确立起来,他经历的一切构成了一个独立、独特的自我。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
基本上可以说,通过《从文自传》的写作,沈从文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之后,最能代表个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边城》和《湘行散记》接踵而来。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说《从文自传》是“一本奇妙的书”,“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接受哪些‘教育’。”
我们回看沈从文的一生,不必把这本自传的意义局限在文学里面。
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张新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从文自传》可以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的背景在小城凤凰,主要是一个小学生的生活,重点却不是读书,而是逃学读社会这本大书,作者自己说这一部分可以称作“顽童自传”;后一部分是一个小兵的生活,他十五岁离开了凤凰和家庭,进入更大也更加严酷的社会,随部队辗转,在各种各样的见闻和遭遇中成长。
沈从文把他所有的经历都看作是对他的人生“教育”,而他的心灵状态,是敞开来去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其中最重要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一是自然现象,二是人生现象,三是人类智慧的光辉。
沈从文从小就有强烈的兴趣和冲动去读自然和社会这部大书。他说,“同一切自然相亲近”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他叙述自己逃学的“顽劣事迹”,不仅仅是要表现一个“顽劣”的性格,而是要描述和说明自己因此而得到的教育。这种教育,要宽阔得多,也更根本,更深入骨髓。它是以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为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大书而进行的不停息的自我教育过程。“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
从一开始,这颗向宽广世界敞开的小小心灵,就被这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带进了永远不会满足也就永远停不下来的探寻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小小的心灵变得越来越充实,越来越阔大。“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答解。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在叙述人生现象的“教育”时,沈从文描述了一种特别的经验:看杀人。他说:“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个作家这么多次地写到这么大规模的砍头式杀人,也没有哪个作家能控制得这么“不动声色”地写看杀人。
他这样写,是冷漠和麻木吗?如果看杀人只是看杀人而没有对自己实实在在的影响,真正地无动于衷,那么,他就是一个鲁迅所说意义上的“看客”;而沈从文想表达的却是,看杀人深刻地“教育”了自己,成为建构自己人生观念的重要因素;有这样的因素参与建构的一个人,与没有此类因素参与建构、没有受过同样“教育”的其他人,当然有着无法泯灭的区别。
所以,他在叙述怀化镇的生活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情况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
除了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建构生命的另一种东西,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变换着形式出现,而且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和沉潜的影响力,这种东西,沈从文把它称为人类智慧的光辉。
他在当兵时期接触到外国文学,姨父家中有两大箱商务印行的《说部丛书》。他谈到这些书时曾这样说:
这些书便轮流作了我最好的朋友。我记得迭更司的《冰雪姻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书,反复约占去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我欢喜这种书,因为它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它不如别的书说道理,它只记下一些现象……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
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特质。
沈从文一个月大概有三四块钱,可是随身带的包袱里,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这份产业现在说来,依然是很动人的。”在《从文自传》里面,这个细节特别打动我。
后来,他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
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那时候从长沙来了个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印刷工人,带来些新书新杂志,沈从文很快就对新书“投了降”,“喜欢看《新潮》《改造》了。”“为了读这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
他做出一个决定,到北京去。没过多久,他就在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簿上,写下——“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我们回头来看沈从文离开湘西时初步形成的知识文化结构。
这其中,有中国古代的历史和艺术,他把在陈渠珍身边做书记的军部称为“学历史的地方”;当然有中国古代文学,也有意外碰到的西洋“说部”;还有刚刚开始接触便产生实际影响的“新文化”。
我们在讲沈从文的传奇时,特别喜欢说到沈从文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好像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可是当我们看到他有着这样一个知识结构的时候,我们太爱好传奇了,可能要把他实际有的知识结构缩小到很小,才使那个传奇更加传奇。可是实际情形可能不是这样的。
特别是,当二十一岁的军中书记从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中感受人类智慧的光辉时,当三十岁的小说家自传写到“学历史的地方”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他一定没有想到,他的后半生,是历史博物馆的馆员,一个最终取得辉煌成就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和学者。我们或许应该想到生命的奇妙,想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为未来的历史埋下的伏笔。
当这部自传结束的时候,传主的形象已经确立起来,他经历的一切构成了一个独立、独特的自我。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
基本上可以说,通过《从文自传》的写作,沈从文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之后,最能代表个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边城》和《湘行散记》接踵而来。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说《从文自传》是“一本奇妙的书”,“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接受哪些‘教育’。”
我们回看沈从文的一生,不必把这本自传的意义局限在文学里面。
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张新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