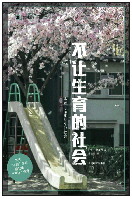妻子母亲背后,那些“看不见”的女人
齐鲁晚报 2020年11月14日
“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前些日子,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的一番言论,将“全职太太”推上风口浪尖,一些身为家庭主妇的网友深感受到了冒犯。家务劳动难道就不算工作吗?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的社会学著作《看不见的女人》首次将“家务”这件看似个体化的事情,放置在广泛的公共领域进行讨论,书中记录了40名家庭主妇的调研访谈,道尽了家庭内的徒劳琐碎与女性的倦怠孤独。尽管著作初版于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四十多年过去了,关于家务的许多现实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今天的女性拥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却依然不可避免地陷入琐碎繁杂的家务之中,由此看来,时空区隔下这本书仍有其价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被视而不见的女人
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这样形容家务劳动:“很少任务比家庭主妇的劳动更像西西弗的酷刑了;日复一日,必须洗盘子,给家具掸灰,缝补衣物,这些东西第二天又会重新弄脏,满是灰尘和裂缝了……她没感到获得积极的善,而是无休止地与恶作斗争。这是一种每天重新开始的斗争。”
这些名为“家庭主妇”的女人,承担着家务劳动、养育子女的任务,被裹挟在女性化的角色里,或是妻子,或是母亲——她们是“看不见的女人”。
在西方社会学奠基的五位“元老”——马克思、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和韦伯之中,仅有马克思和韦伯持有女性解放的观点,但只是基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婚姻模式,因此并未真正看到女性在整体社会活动中的价值。安·奥克利指出,男性主导的社会领域里,更多关注的是男性的兴趣和活动,女性在诸多领域中处于卑微且被视而不见的从属地位。
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的博士论文着眼“女性与家庭事务”这一话题,将家务作为研究对象,回到女性本身,通过她们的眼睛来看待家庭主妇这一职业。研究结果在1974年集结为《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一书出版,第一次将“家务”这件表面上个体化的事情,放置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进行讨论。
安·奥克利的研究始于1971年初,她选择了40名年龄20岁—30岁、家中至少有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的伦敦家庭主妇作为研究对象,把家务劳动视作一项工作进行调查访谈,发现主妇们对家务的不满意普遍存在,孤独感是常有的抱怨,那些担任过高级职位的女性如美甲师、时装模特、计算机程序员等,都对做家务不满意。在从事过职场工作的女性看来,无论是何种性质的工作都能带来家务工作所不具备的陪伴感、社会认可和经济效益。而张桂梅校长所担心的,正是“全职太太”对社会联结、自我追求的丧失。
在被调查的家庭主妇印象中,她们在童年时期即被教育要将“女性气质与家庭生活等同起来”。她们小时候就开始参与成人的家务劳动——帮妈妈洗碗、整理床铺或摆放餐桌等,家中的男孩则不必去做。至成年后,她们还会以母亲为榜样,以母亲的家务标准作为自己做家务的参照。这种观念由女性一代代传承下去。
在安·奥克利的研究对象中,本森夫妇都是建筑师,两人都在家工作。本森夫人的某个工作日安排是这样的:
7:55提醒儿子起床
8:45缝补女儿的睡裙
9:15组织聚会,洗当天的衣服
9:45去洗衣房、商店、药店
11:05来杯工作咖啡,把洗好的衣服晾晒起来
11:40开始工作
而这一天,本森先生却可以九点起床,十点钟开始他的工作。
对自身家庭主妇角色的认同,让从事职场工作的女性更加辛苦。女人认为职场女性给人冷酷好强的男性化印象,作为弥补,会在“负责任的家庭主妇”一职上继续奉献。
尽管这项研究是在“女性解放”滥觞之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代的《卫报》依然会在头条宣称:“女权主义运动发展四十年了,女人仍然从事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和抚养子女的主要负责人的角色,仍继续存在并受到重视。
安·奥克利指出,家庭主妇对自身传统女性气质的强烈的心理身份认同,会将自己牢牢固定在传统女性气质的世界里不得动弹,“这个世界的系统越封闭,看见它之外的大千世界的可能性就越小”。女性只有从意识上彻底觉醒,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解放。
困于生育
家务劳动往往与养育孩子结合在一起,男性去家庭外自由地工作,抚养子女的责任更多地落在女性肩上。
就职于日本东京某咨询公司的女员工怀孕后,因为孕吐而频频请假。待孕吐缓解,为了补上之前落下的工作进度,她拼命加班,却险些流产,住进了医院。部门同事为了替她分担工作,忙得叫苦不迭。出院后,看到同事们加班,自己却因身体原因需要提前下班,她心中很是愧疚。
同部门的单身女同事向领导抱怨:“就因为她工作时间太短,害得大家都很辛苦。听说她还想休一年的产假,难道她不知道自己给同事添了多少麻烦吗?”男同事则态度冷淡:“要是不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的话,还是拜托她辞职吧。”
为了表现重视女性的姿态,提高生育率,2013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曾提出“三年育儿假,尽情抱孩子”的口号。然而,作为专职报道年轻人职场、婚育问题的日本记者小林美希认为,三年育儿假并不会缓解女性差别待遇在职场的泛滥,还会更加固化性别角色分工理论,女性与其想要小孩却“无法生育”,不如说是社会“不让生育”。
日本社会长期流行着“三岁儿神话”的理论,认为在孩子三岁之前,如果母亲不专注于育儿,就可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良影响。于是,育儿成了女性的任务,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约有四成女性会选择“生育离职”,很难实现再就业,不得已成为全职主妇。
日本女性生产之后想回到工作岗位,最常见的办法就是送孩子去幼儿园或托儿所,而幼托机构缺少位置这个事实,生生地把她们困在了家里。既要工作又要育儿的惠子怀第一胎时便遭到了同事的排挤,被人在背后议论“派不上用场”“没有战斗力”,怀上二胎后她干脆把自己母亲从老家接了来——“要想兼顾育儿和工作,自己母亲的存在必不可少”。日本国内的一项调查显示,是否与父母同住直接影响女性产后的就业率:与父母同住的女性产后就业率为30.7%,不予父母同住的女性产后就业率只有17.7%。
日本的工作合同分为正式工和合同工,合同工签约有时间限制,而且相对廉价,有些情况下合同工的工作内容与正式工没有区别,但收入却不及正式工的一半。雇主出于对于女性的偏见,认为女性不能长期工作,工作不了多久就要结婚辞职,遂多将女性定位为合同工角色。即便许多年轻妈妈能够重新回到职场,她们的工资水平仅处于补贴家用的范围,仍然要靠丈夫的收入生活,于是大多数男人便把女人照顾家庭和孩子当成了理所让然的事。
但也有例外。达雄先生在妻子结束育儿假回归职场后,对抗世俗的偏见和单位因循守旧的“惯例”,执着地申请男性育儿假,几经周折终于获批。他不仅从中收获了育儿的乐趣,也切实感受到育儿的辛苦,“职场上如果有越来越多的长辈能对此予以理解的话,优秀的年轻女员工便会更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从长远来看,受益的也是整个单位或公司”。小林美希在《不让生育的社会》一书中指出,男性改变自身意识,是解决许多固有问题的切入点,才有可能将“不让生育的社会”转变为“能够生育的社会”。
好员工还是好妈妈
职场妈妈是当今职场女性中既普遍又特殊的群体,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孩子,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还需要轮“第二班岗”。她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和其他职场人一样,从事全职工作,直面高强度工作和竞争的压力,但同时还要承担起绝大部分育儿和家务职责。那些花了太长时间照顾家人的职业女性,会被认为亵渎了工作;那些避开家庭责任或者将家庭责任委托给他人的女性,则被认为违背了家庭,从而陷入工作—家庭冲突的困境。
如何兼顾职场工作与家务育儿?近日,美国社会学者凯特琳·柯林斯出版专著《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以职场妈妈的困境为出发点,选取了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非常不同的四个国家——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对其中的135位中产阶级职场女性进行访谈,调研她们想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缓解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从而从国家制度、市场配置、文化氛围等角度,试图勾画一种对职场妈妈更为公平并能够提供更为充分的支持的社会图景。
瑞典推行“双职工/双照顾者模式”,施行16个月性别中立的带薪育儿假,包括不用即作废的“爸爸月”,再加上健全的公立幼托体系,职场妈妈可以从伴侣、雇主、同事和政府那里获得支持,兼顾工作和孩子并不困难。
德国推行“一人挣钱/一人顾家模式”,施行12个月的带薪育儿假。虽然兼职工作在德国较为普遍,但妈妈们想要在事业上更进一步是很困难的。受强烈的母爱主义价值观影响,放下孩子出门工作的妈妈会被指责为“乌鸦妈妈”,有事业心的妈妈则会被蔑称为“事业狗”。
意大利推行“家庭/亲族互助模式”,施行5个月的产假(发放80%的薪资)加6个月的育儿假(发放30%的薪资),移民的涌入则为意大利带来了非正规、低收费的照顾服务。然而,理论上有用的家庭政策在实际中并未见效,甚至给妈妈们带来极大的压力。职场妈妈既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妈宝男”般的老公。她们往往无法超越职场上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成为一名“理想员工”。
相比之下,美国的职场妈妈能获得的福利待遇最少,常因为自己的孤立无援与内忧外患而焦头烂额。联邦政府并不提供带薪产假,她们需要自己去解决问题。职场环境更欢迎能够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的员工,女性在那些高收入的职位面前相较男性竞争力更低,职场妈妈也很容易被边缘化,或调岗到所谓的“妈妈岗”,即更不重要的岗位或兼职。
柯林斯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中指出,单靠政策无法解决女性的问题,缓解她们的外在冲突与内在矛盾需要对各国社会有关性别平等、就业和母职的文化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她调查所涉的四个国家中,女性都处于不切实际的“好妈妈”标准之下,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要求社会文化重新定义母亲、工作和家庭,如:育儿的责任不应由女性独自背负、理想员工的形象不应由男性代表等等。工作—家庭冲突看起来是属于个体的、私密的困境,背后其实暗藏着一种性别不平等的权利的斗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被视而不见的女人
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这样形容家务劳动:“很少任务比家庭主妇的劳动更像西西弗的酷刑了;日复一日,必须洗盘子,给家具掸灰,缝补衣物,这些东西第二天又会重新弄脏,满是灰尘和裂缝了……她没感到获得积极的善,而是无休止地与恶作斗争。这是一种每天重新开始的斗争。”
这些名为“家庭主妇”的女人,承担着家务劳动、养育子女的任务,被裹挟在女性化的角色里,或是妻子,或是母亲——她们是“看不见的女人”。
在西方社会学奠基的五位“元老”——马克思、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和韦伯之中,仅有马克思和韦伯持有女性解放的观点,但只是基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婚姻模式,因此并未真正看到女性在整体社会活动中的价值。安·奥克利指出,男性主导的社会领域里,更多关注的是男性的兴趣和活动,女性在诸多领域中处于卑微且被视而不见的从属地位。
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的博士论文着眼“女性与家庭事务”这一话题,将家务作为研究对象,回到女性本身,通过她们的眼睛来看待家庭主妇这一职业。研究结果在1974年集结为《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一书出版,第一次将“家务”这件表面上个体化的事情,放置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进行讨论。
安·奥克利的研究始于1971年初,她选择了40名年龄20岁—30岁、家中至少有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的伦敦家庭主妇作为研究对象,把家务劳动视作一项工作进行调查访谈,发现主妇们对家务的不满意普遍存在,孤独感是常有的抱怨,那些担任过高级职位的女性如美甲师、时装模特、计算机程序员等,都对做家务不满意。在从事过职场工作的女性看来,无论是何种性质的工作都能带来家务工作所不具备的陪伴感、社会认可和经济效益。而张桂梅校长所担心的,正是“全职太太”对社会联结、自我追求的丧失。
在被调查的家庭主妇印象中,她们在童年时期即被教育要将“女性气质与家庭生活等同起来”。她们小时候就开始参与成人的家务劳动——帮妈妈洗碗、整理床铺或摆放餐桌等,家中的男孩则不必去做。至成年后,她们还会以母亲为榜样,以母亲的家务标准作为自己做家务的参照。这种观念由女性一代代传承下去。
在安·奥克利的研究对象中,本森夫妇都是建筑师,两人都在家工作。本森夫人的某个工作日安排是这样的:
7:55提醒儿子起床
8:45缝补女儿的睡裙
9:15组织聚会,洗当天的衣服
9:45去洗衣房、商店、药店
11:05来杯工作咖啡,把洗好的衣服晾晒起来
11:40开始工作
而这一天,本森先生却可以九点起床,十点钟开始他的工作。
对自身家庭主妇角色的认同,让从事职场工作的女性更加辛苦。女人认为职场女性给人冷酷好强的男性化印象,作为弥补,会在“负责任的家庭主妇”一职上继续奉献。
尽管这项研究是在“女性解放”滥觞之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代的《卫报》依然会在头条宣称:“女权主义运动发展四十年了,女人仍然从事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和抚养子女的主要负责人的角色,仍继续存在并受到重视。
安·奥克利指出,家庭主妇对自身传统女性气质的强烈的心理身份认同,会将自己牢牢固定在传统女性气质的世界里不得动弹,“这个世界的系统越封闭,看见它之外的大千世界的可能性就越小”。女性只有从意识上彻底觉醒,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解放。
困于生育
家务劳动往往与养育孩子结合在一起,男性去家庭外自由地工作,抚养子女的责任更多地落在女性肩上。
就职于日本东京某咨询公司的女员工怀孕后,因为孕吐而频频请假。待孕吐缓解,为了补上之前落下的工作进度,她拼命加班,却险些流产,住进了医院。部门同事为了替她分担工作,忙得叫苦不迭。出院后,看到同事们加班,自己却因身体原因需要提前下班,她心中很是愧疚。
同部门的单身女同事向领导抱怨:“就因为她工作时间太短,害得大家都很辛苦。听说她还想休一年的产假,难道她不知道自己给同事添了多少麻烦吗?”男同事则态度冷淡:“要是不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的话,还是拜托她辞职吧。”
为了表现重视女性的姿态,提高生育率,2013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曾提出“三年育儿假,尽情抱孩子”的口号。然而,作为专职报道年轻人职场、婚育问题的日本记者小林美希认为,三年育儿假并不会缓解女性差别待遇在职场的泛滥,还会更加固化性别角色分工理论,女性与其想要小孩却“无法生育”,不如说是社会“不让生育”。
日本社会长期流行着“三岁儿神话”的理论,认为在孩子三岁之前,如果母亲不专注于育儿,就可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良影响。于是,育儿成了女性的任务,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约有四成女性会选择“生育离职”,很难实现再就业,不得已成为全职主妇。
日本女性生产之后想回到工作岗位,最常见的办法就是送孩子去幼儿园或托儿所,而幼托机构缺少位置这个事实,生生地把她们困在了家里。既要工作又要育儿的惠子怀第一胎时便遭到了同事的排挤,被人在背后议论“派不上用场”“没有战斗力”,怀上二胎后她干脆把自己母亲从老家接了来——“要想兼顾育儿和工作,自己母亲的存在必不可少”。日本国内的一项调查显示,是否与父母同住直接影响女性产后的就业率:与父母同住的女性产后就业率为30.7%,不予父母同住的女性产后就业率只有17.7%。
日本的工作合同分为正式工和合同工,合同工签约有时间限制,而且相对廉价,有些情况下合同工的工作内容与正式工没有区别,但收入却不及正式工的一半。雇主出于对于女性的偏见,认为女性不能长期工作,工作不了多久就要结婚辞职,遂多将女性定位为合同工角色。即便许多年轻妈妈能够重新回到职场,她们的工资水平仅处于补贴家用的范围,仍然要靠丈夫的收入生活,于是大多数男人便把女人照顾家庭和孩子当成了理所让然的事。
但也有例外。达雄先生在妻子结束育儿假回归职场后,对抗世俗的偏见和单位因循守旧的“惯例”,执着地申请男性育儿假,几经周折终于获批。他不仅从中收获了育儿的乐趣,也切实感受到育儿的辛苦,“职场上如果有越来越多的长辈能对此予以理解的话,优秀的年轻女员工便会更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从长远来看,受益的也是整个单位或公司”。小林美希在《不让生育的社会》一书中指出,男性改变自身意识,是解决许多固有问题的切入点,才有可能将“不让生育的社会”转变为“能够生育的社会”。
好员工还是好妈妈
职场妈妈是当今职场女性中既普遍又特殊的群体,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孩子,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还需要轮“第二班岗”。她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和其他职场人一样,从事全职工作,直面高强度工作和竞争的压力,但同时还要承担起绝大部分育儿和家务职责。那些花了太长时间照顾家人的职业女性,会被认为亵渎了工作;那些避开家庭责任或者将家庭责任委托给他人的女性,则被认为违背了家庭,从而陷入工作—家庭冲突的困境。
如何兼顾职场工作与家务育儿?近日,美国社会学者凯特琳·柯林斯出版专著《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以职场妈妈的困境为出发点,选取了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非常不同的四个国家——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对其中的135位中产阶级职场女性进行访谈,调研她们想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缓解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从而从国家制度、市场配置、文化氛围等角度,试图勾画一种对职场妈妈更为公平并能够提供更为充分的支持的社会图景。
瑞典推行“双职工/双照顾者模式”,施行16个月性别中立的带薪育儿假,包括不用即作废的“爸爸月”,再加上健全的公立幼托体系,职场妈妈可以从伴侣、雇主、同事和政府那里获得支持,兼顾工作和孩子并不困难。
德国推行“一人挣钱/一人顾家模式”,施行12个月的带薪育儿假。虽然兼职工作在德国较为普遍,但妈妈们想要在事业上更进一步是很困难的。受强烈的母爱主义价值观影响,放下孩子出门工作的妈妈会被指责为“乌鸦妈妈”,有事业心的妈妈则会被蔑称为“事业狗”。
意大利推行“家庭/亲族互助模式”,施行5个月的产假(发放80%的薪资)加6个月的育儿假(发放30%的薪资),移民的涌入则为意大利带来了非正规、低收费的照顾服务。然而,理论上有用的家庭政策在实际中并未见效,甚至给妈妈们带来极大的压力。职场妈妈既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妈宝男”般的老公。她们往往无法超越职场上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成为一名“理想员工”。
相比之下,美国的职场妈妈能获得的福利待遇最少,常因为自己的孤立无援与内忧外患而焦头烂额。联邦政府并不提供带薪产假,她们需要自己去解决问题。职场环境更欢迎能够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的员工,女性在那些高收入的职位面前相较男性竞争力更低,职场妈妈也很容易被边缘化,或调岗到所谓的“妈妈岗”,即更不重要的岗位或兼职。
柯林斯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中指出,单靠政策无法解决女性的问题,缓解她们的外在冲突与内在矛盾需要对各国社会有关性别平等、就业和母职的文化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她调查所涉的四个国家中,女性都处于不切实际的“好妈妈”标准之下,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要求社会文化重新定义母亲、工作和家庭,如:育儿的责任不应由女性独自背负、理想员工的形象不应由男性代表等等。工作—家庭冲突看起来是属于个体的、私密的困境,背后其实暗藏着一种性别不平等的权利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