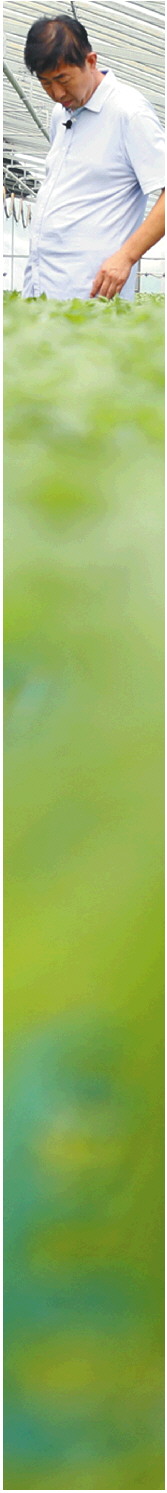鲁西平原“长出”耿店奇迹
在乡村振兴路上,产业兴旺、人才聚集的耿店走在了前列
齐鲁晚报 2021年09月06日
耿遵珠的办公室是村里声量最大的地方,有时连屋后挖掘机的声音都盖不过从这间办公室里传出的热闹。
20年来,聊城市茌平区耿店村的“热闹”让周围村庄的人们眼馋,一座座高标准大棚、一栋栋高楼拔起而起,一百多名“棚二代”返乡创业,还有很多外乡人来村里的大棚打工。虽然村里富了、荣誉多了,但耿店村的“领头雁”耿遵珠比以前更忙了。
耿遵珠说:“在耿店,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实实在在挣钱,二是高高兴兴上楼。当村干部难,乡村振兴不是敲锣打鼓,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许建立 李岩松 李怀磊
偏远村镇的“无奈”
2021年5月,耿遵珠有了新头衔——耿店新村党委书记,从之前一个村的书记,变成了十一个村的书记。“新村”的成立,让“耿店”的范围更大了,同时,耿遵珠的担子也更重了。
2018年,耿遵珠当选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见过“大世面”的他,对“耿店模式”又有了新感悟。今年7月,2021年至2035年的耿店规划书摆在了他的案头,由于经常拿来翻阅,两个月的时间硬是给翻旧了。
对于村庄未来的发展,耿遵珠说,村里的富民产业是大棚,关键在于提高了土地效益,今后发展的诀窍,还是在土地上。
土地之于耿店,多少是有点无奈的。20年前,像耿店这样的自然村在鲁西大平原上比比皆是,无水可依,无山可傍,何况耿店村距茌平城区30多公里,在整个茌平区都属于“偏远村镇”。
“除了土地,几乎没有其他优势资源。”耿遵珠说,这是平原地区最大的现实,“我1966年生,如今在村里生活了55年,依然天天围着土地转。”
2002年,36岁的耿遵珠当选村支部书记。之前他在村里干过代销点、卖过粮食、当过电工和会计,养过蛋鸡,靠着一股实诚劲儿,获得了乡亲们的大力支持。
耿遵珠至今记得,刚上任那会儿,老支书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耿店村是好村,别弄乱了,得把事干好了。”简单的几句话,对耿遵珠触动很大。多年来在村里干活、经商的经验,也使耿遵珠更加关注思路、眼光等问题。
“常说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耿店没有区位优势,走工业的路子对耿店不现实,分析透村里的实际后,我们决定走无农不稳、无商不活的路子。”这是耿遵珠上任伊始的思路。
一年八次去寿光“取经”
从20世纪90年代起,鲁西平原上建起了很多蔬菜大棚,耿店和周围村庄也尝到了设施农业的甜头。但到了2000年左右,情况变了。
“早晨拉,晚上盖,一天赔上几十块。”早晚手工拉帘子、粗放式的劳作,高强度体力劳动还不如出门打工挣得多,很多村民对大棚渐渐失去信心。
2002年,耿店村的大棚产业也走到了十字路口。当时耿店的大棚只种芸豆,有“芸豆之乡”的美誉,但随着一年年重茬,品质下降、效益低下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个50米的老大棚,种菜一年只卖七八千元,出去打工一年能挣上万块。很多人觉得,在村里种大棚真不如外出打工。
还要不要继续种大棚?这是耿遵珠上任后第一个要解决的难题。
“我就想让大家看看,不是大棚产业不行了,而是我们没有技术,不敢改茬,不敢跟进,造成耿店的产业越来越萎缩。你看人家寿光,一个大棚能挣好几万块钱,这就是差距。”为了让大家解放思想,耿遵珠带着村民去寿光“取经”,一年去了8次。学习回来后,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耿店还从寿光聘来了技术员,指导改茬工作,改种黄瓜、辣椒、西红柿。
这一改茬,效益直接翻了一番。还是50米长的老棚,一年种菜的收益达到一万五千多元。大棚产业对村民的吸引力立刻回来了。从2002年开始,耿店彻底迈上了产业振兴的快车道,直到现在依然高歌猛进。2021年上半年,耿店村新建大棚30座。
当时同样都是种大棚,为什么耿店发展起来了?很多来耿店参观学习的人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用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武装了头脑,在大棚产业发展的十字路口没有迷路,坚持了下来。”耿遵珠说。
耿庆祥是耿店村党支部委员,1992年至2002年当过村里的生产队长,他说:“论起种大棚,我们耿店在周边最有发言权,2002年是个分水岭,改茬之后又上了自动卷帘机、水肥一体化等设备,规模越来越大,蔬菜产业真是腾飞了。”
经过20年发展,如今的耿店蔬菜大棚已经形成“一条龙”产业模式:育苗基地、合作社、蔬菜批发市场等配套设施和服务齐全,全链条式产业模式让大家在村里就能赚到钱。
9亩地干了20亩地的事
走进聊城市茌平区贾寨镇耿店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村里的楼多,仅住宅楼就达到了11栋。夏末的鲁西平原,已经有些凉爽了。晚上9点,耿店村的主街上依然人来人往。经过十多年发展,耿店村民上楼了,而且是“高高兴兴”上楼。耿店新村党委书记耿遵珠也上楼了。
为什么要盖楼?村民为什么要上楼?村民们的回答很简单:人多地少。2020年,耿店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4.5万元。这让村民感到了乡村振兴的力量。
耿遵珠表示,耿店的新农村建设与大棚产业是同步推进的,甚至可以说是水到渠成。2006年,大棚引进自动卷帘机、水肥一体化等新装备后,耿店村民的增收速度更快了,产业兴旺也为耿店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
“2007年、2008年,耿店村民真是发财了,到了2009年,全村一下子上了100个高标准大棚。”耿遵珠说,搞新农村建设时,我们村的大棚产业同样蒸蒸日上,每年上新的,改老的,2009年最热闹时,七套挖掘机同时作业,全县很多人来观摩。
村民的钱包确实鼓了,村集体的家底也厚实了,但耿遵珠从村民的反映中,看到了发展新问题,当时很多家庭面临着孩子结婚要新房而村里没法安排。
“要盖房,得有地,这地从何而来?因为村里都是平房,国家也不提倡再占用耕地,无法再扩展了,在这种情况下,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多次去外地取经,最后村里决定不再安排新宅基地,而是准备盖楼。而且那时国家的好政策也来了,恰逢其时。”耿遵珠说。
回头看,2009年是耿店村民上楼的“元年”。村里决定,将集体的大棚拆掉,盖成“3+1”式的楼房,三层居住,底层车库,每平方米700元,想买的先交2万,盖一层交一层的钱。
当村支书20年来,耿遵珠心里最明白的就是“土地账”。他说,如果盖平房,按照一处宅子四分地计算,得用20多亩地,而盖楼的话,只需要用9亩地就能安排60户,而且人居环境大大改善。
耿书记“吃亏”搬家
8月27日下午4点半到6点半,耿遵珠从大棚回到办公室后,就被来来往往的村民“堵”住了,有人找他领新房钥匙,有人为电费的事而来,有人找他商量工地开工的事,还有人是讨价还价。
“我就是觉得冤,买楼的钱交得比别人多,想想就难受。”一位村民说。“每平方米1420元是2018年定下来的价格,这两栋的价格之所以比以前高,是因为有电梯,质量好,没有其他的。”耿遵珠反复向一位前几天已来过一趟的村民解释。“少拿点钱就行。”村民有些犟。“你放心,上楼带电梯,慢慢就知道好处了。听我说,你把剩下的几万块钱补上,一点都不冤。”
在耿遵珠的办公室,从来不缺嗓门高的人,但嗓门再高,也高不过耿遵珠讲的道理。对于耿店村的事情,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了,“有苦你就说,有冤你就诉”,村务村情、乡里乡亲,他总能把理儿拉得透彻、明白,特别是关于上楼的事。而且他的两次“吃亏式”搬家,成了十里八村的谈资。
如果说重拾大棚产业,是耿店村第一次飞跃,那村民上楼便是耿店村的第二次飞跃。
2012年,一期住宅楼建成,但清完账等待抓号分房时,村民中间有了议论,因为都不愿抓到位置最“孬”的那户。
哪个位置最“孬”?四号楼一楼东户。在很多人眼里,这个位置遮阴,挨着临街饭店的婚宴大厅,降了三万元都没人要,村里喊了几次抓号都没人来。
在和村民聊天时,耿遵珠了解到,由于这次给孩子要婚房娶媳妇的比较多,当父母的怕在人前落下话把,说“你看他家要的是最孬的房子”,所以,这套“孬房”成了大家不肯抓号的原因。
看到这种情况,耿遵珠决定:既然大家都说位置最“孬”,那我就要这户。“我把最‘孬’的认下来,不参加抓号了,大家一看最孬的没了,抓号时很积极,楼房一下子抢光了。”就这样,“分房危机”解除了。
接下来的事情,让耿遵珠有些“不好意思”。这次上楼的其他住户一家拿出50元来,到县电视台点了一星期的歌,对他表示感谢。
这次上楼,是耿遵珠第一次搬家,不过他没想到,2014年底,他又搬了一次家。
“棚二代”元年
2010年是耿店村“棚二代”回村的“元年”,一拨拨之前在外打工的人选择回到村里。
耿付建是耿店村最早一批返乡的“棚二代”,2010年春节回家,他发现在外打工的收入,跟在村里种大棚相比,顶多算个零头。春节过后,耿付建决定回家乡发展。
耿付建回村后,一下子投资几十万搞了5个大棚。村两委也帮着他做好修路、架电、排水等工作,连大棚用地也是村里帮忙整合的。2020年,经过多年积累,经营11个大棚的他,年收入达到了40多万元。
2018年春节,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的曹有忠也发现,家乡发展早已脱胎换骨。过完年,曹有忠看着越发年迈的父母,回想起从小玩到大的同伴回乡种大棚的事,他心动了。现在,曹有忠在村里经营着葡萄大棚,也是小有成就。
回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一期盖的楼都分完了,怎么办?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下,耿店村选择拆老宅子,继续向北盖新楼。
拆老宅子,在农村谈何容易。这次,耿遵珠也是“拼了”,决定先拆跟自己一个家族的20多户,他自己的老宅子也在里面。
2011年秋天,在耿遵珠的带领下,耿店村拆了30多户,在腾出的土地上盖了3栋住宅楼,可安排100户。2014年底,楼盖好了,该分房了,可是问题又来了。
这次选房,65岁以上享受一二层。不过,顶层五楼成了最“孬”的楼层,即使价格从每平方米930元优惠到730元,村民们还是不愿意来抓号,尤其是年龄偏大一点的。
对于村民的顾虑,耿遵珠也理解。“既然大家都不愿意要顶楼,那我就带头认一套五楼的房子。”很快,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把五楼“包圆了”。从大家不要到干部带头把五楼认完,这个过程着实感动了村民。
既然认下了五楼,那就得去住,耿遵珠又一次搬了家,从四号楼的一楼搬到了六号楼的五楼。原来的楼房怎么办呢?其实,在那套所谓位置“孬”的房子里,耿遵珠家完成一件大事——儿子娶媳妇。至于之前所说的“环境差”,耿遵珠说,那都是“别人以为”,“我在里面住得挺好的。等我往外让的时候,好几家争着要,最后,我让给了一家有90岁老太太的家庭。”耿遵珠说。
拆迁之前先盖敬老院
8月28日,耿店村里响起了鞭炮声,来村里赶集的人们在一片新规划的“棚二代”住宅楼工地前驻足,满是期待的眼神。
今年上半年,新建造的两栋带电梯楼房完工。9月的耿店村,伴着鲁西平原秋天的凉爽,不少村民已经开始往里搬。
“我们的富裕,是靠解决了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是真正靠农业富裕起来的,不是靠补贴。”说这话时,耿遵珠底气十足。
村民选房最怕什么?怕过程不公平,怕抓到“孬”房。而耿遵珠的“两次搬家”,主动吃亏,在耿店村树立了干部担当的典范。
耿遵珠说,让村民高高兴兴上楼,关键在于村干部要内心坦荡荡,要清正廉洁,要能提供好的公共服务,这些年耿店村的冬季供暖,做得比城市里还要好。
在耿店村,绝大多数村民搬进楼房,但村里的弱势群体,特别是鳏寡孤独群体,也没有被落下。在村庄改造过程中,要有一家高标准的村级敬老院或周转房,成为耿店村的成功经验。住在耿店村幸福院的郑玉环老人,今年74岁,2014年由于身体原因,从老宅子搬出后便住进了免费的幸福院,一家一户的院子,让她很满意,而且拆老房子时,村里还补偿了四万多元。虽然她没住上楼,但她的两个儿子、两个孙子,在村里各有一套楼。
“小孙子今年考上了大学,村里想得很周到,还给发了一个旅行箱。”郑玉环说。
“虽说新楼房可以用老宅子置换,但毕竟是要拿一部分钱的,有些户真拿不出来,还有各种原因上不了楼的。这些困难户的问题解决不了,干哪一项工作,也不能完美收官。所以拆迁之前,先盖敬老院,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耿遵珠说,宅基地换养老房,再加上兜底措施,这才能让全体村民享受到新农村建设的红利。
村两委为了诚信拼了
在耿遵珠心中,村干部的诚信,就是发展的信心。这些年,无论是建蔬菜市场、种苗厂,还是搞合作社,讲诚信已成为耿店村两委班子给人的“第一印象”。
“为解决改茬后出现的卖菜难,村里建了蔬菜批发市场;为降低市场风险,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抱团发展;随着规模扩大,出现了育苗难,村里牵头建起了育苗基地。这些都是股份制搞起来的,真正让老百姓相信我们这个班子是干事创业的,知道我们是讲诚信的。做人讲诚信,做事讲双赢。”耿遵珠说。
2013年冬天,由于天气寒冷,一连下了好几场雪,耿店种苗厂的50多万株订单苗全冻毁了。这批苗是为来年开春准备的,如果不能及时育好苗,全村大棚将遭受巨大损失。
那段时间,耿遵珠和其他村两委班子成员真是愁坏了。耿遵珠决定,哪怕赔钱四处买苗,也不能让村民蒙受损失。一般来说,种苗厂接到10万株订单的话,会培育11万株,以防万一。于是,耿遵珠带领村干部跑到寿光、青州以及河北等地的苗厂,全力收购人家多出来的种苗。“我们的一呼百应是怎么来的?就是讲诚信获得的。大棚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直接关系到村民收入,既然接了村民的订单,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完成,不能失信于民。”耿遵珠说。
8月26日,耿店新村党委举行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主要议题是“三资”(资产、资源、资金)清理专项行动。
“我感觉‘三资’清理专项行动,是换届以来打基础的活儿,耿店村集体经济体量大,但由于之前做得好,在这项工作中反而工作量小。”耿遵珠说,想要治理有效,农村干部必须担当作为,把以前的不正之风纠正过来,该是集体的,必须是集体的。
可以说,厚实的集体经济是耿店村的发展命脉。目前该村集体资产达1000多万元,年收益在50万元以上。
在耿店大棚发展路上,耿遵珠做了一件“化囧为喜”的事。2017年,村里利用腾出来的土地,用扶贫资金建了15座大棚,计划以每个大棚1.3万元的费用承包给村民,但是村委会的大喇叭响了几天,一个来找的都没有。
不少村民说,这是老宅子拆迁后的地,碱性大,种的东西长不好,里面砖头瓦块也不平整。资金引进来了,但没承包出去,大棚闲着就是浪费。“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就比困难多。”耿遵珠心想。
于是,耿遵珠想了一个法子。他先找了一位村民承包了3个棚。剩下的12个棚,他想了“合伙承包”的招儿,找了一位合作伙伴跟他一起承包下来,每人6个棚,当年种辣椒。
由于大棚管理得好,当年辣椒价格又非常好,每斤7元,一年下来,6个棚的纯收入达到了30万元。
“承包大棚的做法,也是从我这儿开始的,通过这件事,就是想告诉村民要靠大脑挣钱,当农场主,这样才能挣到大钱。”耿遵珠说。
20年来,聊城市茌平区耿店村的“热闹”让周围村庄的人们眼馋,一座座高标准大棚、一栋栋高楼拔起而起,一百多名“棚二代”返乡创业,还有很多外乡人来村里的大棚打工。虽然村里富了、荣誉多了,但耿店村的“领头雁”耿遵珠比以前更忙了。
耿遵珠说:“在耿店,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实实在在挣钱,二是高高兴兴上楼。当村干部难,乡村振兴不是敲锣打鼓,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许建立 李岩松 李怀磊
偏远村镇的“无奈”
2021年5月,耿遵珠有了新头衔——耿店新村党委书记,从之前一个村的书记,变成了十一个村的书记。“新村”的成立,让“耿店”的范围更大了,同时,耿遵珠的担子也更重了。
2018年,耿遵珠当选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见过“大世面”的他,对“耿店模式”又有了新感悟。今年7月,2021年至2035年的耿店规划书摆在了他的案头,由于经常拿来翻阅,两个月的时间硬是给翻旧了。
对于村庄未来的发展,耿遵珠说,村里的富民产业是大棚,关键在于提高了土地效益,今后发展的诀窍,还是在土地上。
土地之于耿店,多少是有点无奈的。20年前,像耿店这样的自然村在鲁西大平原上比比皆是,无水可依,无山可傍,何况耿店村距茌平城区30多公里,在整个茌平区都属于“偏远村镇”。
“除了土地,几乎没有其他优势资源。”耿遵珠说,这是平原地区最大的现实,“我1966年生,如今在村里生活了55年,依然天天围着土地转。”
2002年,36岁的耿遵珠当选村支部书记。之前他在村里干过代销点、卖过粮食、当过电工和会计,养过蛋鸡,靠着一股实诚劲儿,获得了乡亲们的大力支持。
耿遵珠至今记得,刚上任那会儿,老支书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耿店村是好村,别弄乱了,得把事干好了。”简单的几句话,对耿遵珠触动很大。多年来在村里干活、经商的经验,也使耿遵珠更加关注思路、眼光等问题。
“常说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耿店没有区位优势,走工业的路子对耿店不现实,分析透村里的实际后,我们决定走无农不稳、无商不活的路子。”这是耿遵珠上任伊始的思路。
一年八次去寿光“取经”
从20世纪90年代起,鲁西平原上建起了很多蔬菜大棚,耿店和周围村庄也尝到了设施农业的甜头。但到了2000年左右,情况变了。
“早晨拉,晚上盖,一天赔上几十块。”早晚手工拉帘子、粗放式的劳作,高强度体力劳动还不如出门打工挣得多,很多村民对大棚渐渐失去信心。
2002年,耿店村的大棚产业也走到了十字路口。当时耿店的大棚只种芸豆,有“芸豆之乡”的美誉,但随着一年年重茬,品质下降、效益低下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个50米的老大棚,种菜一年只卖七八千元,出去打工一年能挣上万块。很多人觉得,在村里种大棚真不如外出打工。
还要不要继续种大棚?这是耿遵珠上任后第一个要解决的难题。
“我就想让大家看看,不是大棚产业不行了,而是我们没有技术,不敢改茬,不敢跟进,造成耿店的产业越来越萎缩。你看人家寿光,一个大棚能挣好几万块钱,这就是差距。”为了让大家解放思想,耿遵珠带着村民去寿光“取经”,一年去了8次。学习回来后,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耿店还从寿光聘来了技术员,指导改茬工作,改种黄瓜、辣椒、西红柿。
这一改茬,效益直接翻了一番。还是50米长的老棚,一年种菜的收益达到一万五千多元。大棚产业对村民的吸引力立刻回来了。从2002年开始,耿店彻底迈上了产业振兴的快车道,直到现在依然高歌猛进。2021年上半年,耿店村新建大棚30座。
当时同样都是种大棚,为什么耿店发展起来了?很多来耿店参观学习的人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用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武装了头脑,在大棚产业发展的十字路口没有迷路,坚持了下来。”耿遵珠说。
耿庆祥是耿店村党支部委员,1992年至2002年当过村里的生产队长,他说:“论起种大棚,我们耿店在周边最有发言权,2002年是个分水岭,改茬之后又上了自动卷帘机、水肥一体化等设备,规模越来越大,蔬菜产业真是腾飞了。”
经过20年发展,如今的耿店蔬菜大棚已经形成“一条龙”产业模式:育苗基地、合作社、蔬菜批发市场等配套设施和服务齐全,全链条式产业模式让大家在村里就能赚到钱。
9亩地干了20亩地的事
走进聊城市茌平区贾寨镇耿店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村里的楼多,仅住宅楼就达到了11栋。夏末的鲁西平原,已经有些凉爽了。晚上9点,耿店村的主街上依然人来人往。经过十多年发展,耿店村民上楼了,而且是“高高兴兴”上楼。耿店新村党委书记耿遵珠也上楼了。
为什么要盖楼?村民为什么要上楼?村民们的回答很简单:人多地少。2020年,耿店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4.5万元。这让村民感到了乡村振兴的力量。
耿遵珠表示,耿店的新农村建设与大棚产业是同步推进的,甚至可以说是水到渠成。2006年,大棚引进自动卷帘机、水肥一体化等新装备后,耿店村民的增收速度更快了,产业兴旺也为耿店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
“2007年、2008年,耿店村民真是发财了,到了2009年,全村一下子上了100个高标准大棚。”耿遵珠说,搞新农村建设时,我们村的大棚产业同样蒸蒸日上,每年上新的,改老的,2009年最热闹时,七套挖掘机同时作业,全县很多人来观摩。
村民的钱包确实鼓了,村集体的家底也厚实了,但耿遵珠从村民的反映中,看到了发展新问题,当时很多家庭面临着孩子结婚要新房而村里没法安排。
“要盖房,得有地,这地从何而来?因为村里都是平房,国家也不提倡再占用耕地,无法再扩展了,在这种情况下,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多次去外地取经,最后村里决定不再安排新宅基地,而是准备盖楼。而且那时国家的好政策也来了,恰逢其时。”耿遵珠说。
回头看,2009年是耿店村民上楼的“元年”。村里决定,将集体的大棚拆掉,盖成“3+1”式的楼房,三层居住,底层车库,每平方米700元,想买的先交2万,盖一层交一层的钱。
当村支书20年来,耿遵珠心里最明白的就是“土地账”。他说,如果盖平房,按照一处宅子四分地计算,得用20多亩地,而盖楼的话,只需要用9亩地就能安排60户,而且人居环境大大改善。
耿书记“吃亏”搬家
8月27日下午4点半到6点半,耿遵珠从大棚回到办公室后,就被来来往往的村民“堵”住了,有人找他领新房钥匙,有人为电费的事而来,有人找他商量工地开工的事,还有人是讨价还价。
“我就是觉得冤,买楼的钱交得比别人多,想想就难受。”一位村民说。“每平方米1420元是2018年定下来的价格,这两栋的价格之所以比以前高,是因为有电梯,质量好,没有其他的。”耿遵珠反复向一位前几天已来过一趟的村民解释。“少拿点钱就行。”村民有些犟。“你放心,上楼带电梯,慢慢就知道好处了。听我说,你把剩下的几万块钱补上,一点都不冤。”
在耿遵珠的办公室,从来不缺嗓门高的人,但嗓门再高,也高不过耿遵珠讲的道理。对于耿店村的事情,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了,“有苦你就说,有冤你就诉”,村务村情、乡里乡亲,他总能把理儿拉得透彻、明白,特别是关于上楼的事。而且他的两次“吃亏式”搬家,成了十里八村的谈资。
如果说重拾大棚产业,是耿店村第一次飞跃,那村民上楼便是耿店村的第二次飞跃。
2012年,一期住宅楼建成,但清完账等待抓号分房时,村民中间有了议论,因为都不愿抓到位置最“孬”的那户。
哪个位置最“孬”?四号楼一楼东户。在很多人眼里,这个位置遮阴,挨着临街饭店的婚宴大厅,降了三万元都没人要,村里喊了几次抓号都没人来。
在和村民聊天时,耿遵珠了解到,由于这次给孩子要婚房娶媳妇的比较多,当父母的怕在人前落下话把,说“你看他家要的是最孬的房子”,所以,这套“孬房”成了大家不肯抓号的原因。
看到这种情况,耿遵珠决定:既然大家都说位置最“孬”,那我就要这户。“我把最‘孬’的认下来,不参加抓号了,大家一看最孬的没了,抓号时很积极,楼房一下子抢光了。”就这样,“分房危机”解除了。
接下来的事情,让耿遵珠有些“不好意思”。这次上楼的其他住户一家拿出50元来,到县电视台点了一星期的歌,对他表示感谢。
这次上楼,是耿遵珠第一次搬家,不过他没想到,2014年底,他又搬了一次家。
“棚二代”元年
2010年是耿店村“棚二代”回村的“元年”,一拨拨之前在外打工的人选择回到村里。
耿付建是耿店村最早一批返乡的“棚二代”,2010年春节回家,他发现在外打工的收入,跟在村里种大棚相比,顶多算个零头。春节过后,耿付建决定回家乡发展。
耿付建回村后,一下子投资几十万搞了5个大棚。村两委也帮着他做好修路、架电、排水等工作,连大棚用地也是村里帮忙整合的。2020年,经过多年积累,经营11个大棚的他,年收入达到了40多万元。
2018年春节,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的曹有忠也发现,家乡发展早已脱胎换骨。过完年,曹有忠看着越发年迈的父母,回想起从小玩到大的同伴回乡种大棚的事,他心动了。现在,曹有忠在村里经营着葡萄大棚,也是小有成就。
回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一期盖的楼都分完了,怎么办?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下,耿店村选择拆老宅子,继续向北盖新楼。
拆老宅子,在农村谈何容易。这次,耿遵珠也是“拼了”,决定先拆跟自己一个家族的20多户,他自己的老宅子也在里面。
2011年秋天,在耿遵珠的带领下,耿店村拆了30多户,在腾出的土地上盖了3栋住宅楼,可安排100户。2014年底,楼盖好了,该分房了,可是问题又来了。
这次选房,65岁以上享受一二层。不过,顶层五楼成了最“孬”的楼层,即使价格从每平方米930元优惠到730元,村民们还是不愿意来抓号,尤其是年龄偏大一点的。
对于村民的顾虑,耿遵珠也理解。“既然大家都不愿意要顶楼,那我就带头认一套五楼的房子。”很快,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把五楼“包圆了”。从大家不要到干部带头把五楼认完,这个过程着实感动了村民。
既然认下了五楼,那就得去住,耿遵珠又一次搬了家,从四号楼的一楼搬到了六号楼的五楼。原来的楼房怎么办呢?其实,在那套所谓位置“孬”的房子里,耿遵珠家完成一件大事——儿子娶媳妇。至于之前所说的“环境差”,耿遵珠说,那都是“别人以为”,“我在里面住得挺好的。等我往外让的时候,好几家争着要,最后,我让给了一家有90岁老太太的家庭。”耿遵珠说。
拆迁之前先盖敬老院
8月28日,耿店村里响起了鞭炮声,来村里赶集的人们在一片新规划的“棚二代”住宅楼工地前驻足,满是期待的眼神。
今年上半年,新建造的两栋带电梯楼房完工。9月的耿店村,伴着鲁西平原秋天的凉爽,不少村民已经开始往里搬。
“我们的富裕,是靠解决了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是真正靠农业富裕起来的,不是靠补贴。”说这话时,耿遵珠底气十足。
村民选房最怕什么?怕过程不公平,怕抓到“孬”房。而耿遵珠的“两次搬家”,主动吃亏,在耿店村树立了干部担当的典范。
耿遵珠说,让村民高高兴兴上楼,关键在于村干部要内心坦荡荡,要清正廉洁,要能提供好的公共服务,这些年耿店村的冬季供暖,做得比城市里还要好。
在耿店村,绝大多数村民搬进楼房,但村里的弱势群体,特别是鳏寡孤独群体,也没有被落下。在村庄改造过程中,要有一家高标准的村级敬老院或周转房,成为耿店村的成功经验。住在耿店村幸福院的郑玉环老人,今年74岁,2014年由于身体原因,从老宅子搬出后便住进了免费的幸福院,一家一户的院子,让她很满意,而且拆老房子时,村里还补偿了四万多元。虽然她没住上楼,但她的两个儿子、两个孙子,在村里各有一套楼。
“小孙子今年考上了大学,村里想得很周到,还给发了一个旅行箱。”郑玉环说。
“虽说新楼房可以用老宅子置换,但毕竟是要拿一部分钱的,有些户真拿不出来,还有各种原因上不了楼的。这些困难户的问题解决不了,干哪一项工作,也不能完美收官。所以拆迁之前,先盖敬老院,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耿遵珠说,宅基地换养老房,再加上兜底措施,这才能让全体村民享受到新农村建设的红利。
村两委为了诚信拼了
在耿遵珠心中,村干部的诚信,就是发展的信心。这些年,无论是建蔬菜市场、种苗厂,还是搞合作社,讲诚信已成为耿店村两委班子给人的“第一印象”。
“为解决改茬后出现的卖菜难,村里建了蔬菜批发市场;为降低市场风险,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抱团发展;随着规模扩大,出现了育苗难,村里牵头建起了育苗基地。这些都是股份制搞起来的,真正让老百姓相信我们这个班子是干事创业的,知道我们是讲诚信的。做人讲诚信,做事讲双赢。”耿遵珠说。
2013年冬天,由于天气寒冷,一连下了好几场雪,耿店种苗厂的50多万株订单苗全冻毁了。这批苗是为来年开春准备的,如果不能及时育好苗,全村大棚将遭受巨大损失。
那段时间,耿遵珠和其他村两委班子成员真是愁坏了。耿遵珠决定,哪怕赔钱四处买苗,也不能让村民蒙受损失。一般来说,种苗厂接到10万株订单的话,会培育11万株,以防万一。于是,耿遵珠带领村干部跑到寿光、青州以及河北等地的苗厂,全力收购人家多出来的种苗。“我们的一呼百应是怎么来的?就是讲诚信获得的。大棚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直接关系到村民收入,既然接了村民的订单,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完成,不能失信于民。”耿遵珠说。
8月26日,耿店新村党委举行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主要议题是“三资”(资产、资源、资金)清理专项行动。
“我感觉‘三资’清理专项行动,是换届以来打基础的活儿,耿店村集体经济体量大,但由于之前做得好,在这项工作中反而工作量小。”耿遵珠说,想要治理有效,农村干部必须担当作为,把以前的不正之风纠正过来,该是集体的,必须是集体的。
可以说,厚实的集体经济是耿店村的发展命脉。目前该村集体资产达1000多万元,年收益在50万元以上。
在耿店大棚发展路上,耿遵珠做了一件“化囧为喜”的事。2017年,村里利用腾出来的土地,用扶贫资金建了15座大棚,计划以每个大棚1.3万元的费用承包给村民,但是村委会的大喇叭响了几天,一个来找的都没有。
不少村民说,这是老宅子拆迁后的地,碱性大,种的东西长不好,里面砖头瓦块也不平整。资金引进来了,但没承包出去,大棚闲着就是浪费。“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就比困难多。”耿遵珠心想。
于是,耿遵珠想了一个法子。他先找了一位村民承包了3个棚。剩下的12个棚,他想了“合伙承包”的招儿,找了一位合作伙伴跟他一起承包下来,每人6个棚,当年种辣椒。
由于大棚管理得好,当年辣椒价格又非常好,每斤7元,一年下来,6个棚的纯收入达到了30万元。
“承包大棚的做法,也是从我这儿开始的,通过这件事,就是想告诉村民要靠大脑挣钱,当农场主,这样才能挣到大钱。”耿遵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