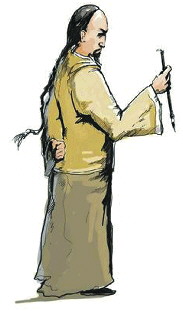师爷:流传天下无官衔
齐鲁晚报 2022年01月21日
□李学朴
师爷,是旧时对幕友的尊称。幕友,又称幕宾、幕客、西宾、宾师等,指受各级官吏聘请帮助处理政务的人。清代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仆人称官员为老爷,称幕友为师爷。”师爷一词的称呼始于清代,从事此业者多为浙江绍兴人。
师爷,按其源流,源出周王之官——“幕人”。《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记载:“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凡朝觐、会同、军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帟、绶。”《周礼注疏》中则说:“王出宫,则幕人以帷与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则张之。”据此看来,“幕人”的职责就是掌管帷幕等物,并在周王朝觐、会同、军旅、田役、祭祀时张幕、设案。
汉代,幕僚制度已基本成型,公卿、郡守都有权聘用僚属。东汉光武中兴之后,辟召之风尤其兴盛。光武帝刘秀曾征召过故人严子陵,但严子陵却宁愿在富春江钓鱼。东汉末年,各派豪族军阀拥兵割据,为确保各自发展,争将天下名士罗致幕下,以壮势力,这导致了幕僚制度进一步发展。
东晋时期,权臣桓温图谋篡夺天下,参军郗超为他谋划。谢安与王坦之曾经去拜访桓温,谈论国家大事,桓温就让郗超藏在幕帐之后偷听。没想到一阵风吹来,吹开了帘帐,郗超露了出来,谢安笑道:“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幕宾”一说。南北朝时期,名士庾杲之受聘到王俭的幕府去做长史,有朋友表示祝贺,说有这样的名士入幕,好比芙蓉依傍着莲花池的绿水。后人因为这个典故,往往将幕府雅称为“莲幕”。
古时师爷的职责,主要在于协助判案、管理钱粮、起草文书、整理档案等。与此相呼应,师爷也分为五大类:刑名、钱谷、挂号、征比、书记。在州县以刑名、钱谷二者责任最为重大,地位也较其他师爷为尊。
明清地方官府是行政和司法合一,地方官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司法长官。他们所管的事主要有两件:一是审理刑事、民事案件,二是征收钱粮,上交藩库。清代有人说,州县衙门里总是响着“三声”——板子声、算盘声、戥子声。说的就是地方官府所处理的事主要是办案和征收钱粮这两类,这两类事中,又以办案最为重要。清代有一种说法,叫“亲民首在理讼”,即是说办案是亲民之官(州县官)的首要大事。案子办得好坏,是朝廷衡量地方官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志。所以,地方官都很重视案件的审理。
但是,清代地方官多是科举出身的“读书不读律”的士人,必须仰仗精通理讼的师爷来协助办理。清人陆向荣《瘦石山房笔记》云:“近日官途多依靠幕友,而于读律毫不讲解。”(《引自牧令书辑要·刑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由于师爷在案子审判中掌握重权,所以很多人的祸福生死就操在他们手里。清代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三》中记述一位时人所说的话:“幕府宾佐,非官而操官之权,笔墨之间,动关生死,为善易,为恶亦易。”清代绍兴山阴人金植因为亲戚和同乡中有很多当刑名师爷,所以对此感触尤深,他说:“一切入幕主文之法家”,执笔时一定要“切切警醒”“倘稍有冤抑,一著点墨,则人命立休于笔下”(《不下带编》卷七)。另一个绍兴人俞蛟也说:刑名师爷“按律引例,以判罪人,生死所争,在毫厘间。”(《梦厂杂著·纪西粤幕》)
师爷一行多与文书案牍打交道,因此只有读书人才能胜任,读书做官是学子毕业所孜孜以求的目标。许多人为此皓首穷经、老死牖下。但是,对于大多数师爷来说,这种梦想不再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科考失意后,及时退出改习此业的,有的从事这一行长达几十年,不再以科举为念。
入幕得势的师爷,往往成为盈利之徒,甚至声色犬马无所不为。万维翰就感叹过:“幕中之流品,最为错杂,有宦辙覆车,借人酒杯,自浇块垒;有贵胄飘零,摒挡纨绔,入幕效颦;又有以铁砚难磨,青毡冷淡,变业谋生……”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既然师爷群体的成分这么复杂,品行不端者就在所难免,上下勾结、朋比为奸的大有人在,欺上瞒下、涂改公文、把持官府、胡解案例者也不乏其人。
清代徐珂所辑的《清稗类钞》中,便对师爷的此种伎俩有着生动的描述。在师爷中,最能作弊的是刑名师爷,因为清代颁布的法令多不甚确切,对一个具体的案件,多半是根据以往的成例来判定,这样就给了师爷上下其手的机会,许多冤狱,都由他们操持。如同治年间轰动京城的杨乃武冤狱,便有一绍兴师爷不光彩的表演,他私通案犯,逼取伪供,致成大狱。丁宝桢为福建巡抚时,某县有开棺剥取尸身衣饰一案,该县刑名师爷为替县令掩饰,在文书上故意用模糊含混字样,以图蒙混过关,终被查出。这样的事例,在晚清文献上并不少见。无怪乎当时的人对师爷以“搞来搞去,终是小人”嗤之以鼻了。
民国初年,有的师爷摇身一变成为民国幕僚,但师爷体制余习未尽,职业思想还没有变过来。民国幕僚人数之多不亚于清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军政长官普遍重视幕僚,这些幕僚被称为顾问、参议、参谋、秘书、副官等,实际上就是清代师爷称谓的花样翻新。
历史上文人历来有重视文史的传统,许多师爷因长期游幕,笔记作品多载当地风土人情、社会百态,如邬斯道《游梁草》《抚豫宣化录记载河南之事》《全庶熙日记》载滇黔两省事,宣鼎《秋雨夜灯录》详述清末社会大量丑恶现象。另一个师爷吴炽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写成《客窗闲话》及《续客窗闲话》,书中描述的活脱是一幅社会百态图。这些著作不仅文字可读,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那些运筹于历史帷幄之中,周旋于帝王将相之间,盘桓于州县衙门之内的师爷们,“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如今只留下一段传奇的历史,一桩桩辛酸的往事,一个个缥缈的背影。
师爷,是旧时对幕友的尊称。幕友,又称幕宾、幕客、西宾、宾师等,指受各级官吏聘请帮助处理政务的人。清代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仆人称官员为老爷,称幕友为师爷。”师爷一词的称呼始于清代,从事此业者多为浙江绍兴人。
师爷,按其源流,源出周王之官——“幕人”。《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记载:“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凡朝觐、会同、军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帟、绶。”《周礼注疏》中则说:“王出宫,则幕人以帷与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则张之。”据此看来,“幕人”的职责就是掌管帷幕等物,并在周王朝觐、会同、军旅、田役、祭祀时张幕、设案。
汉代,幕僚制度已基本成型,公卿、郡守都有权聘用僚属。东汉光武中兴之后,辟召之风尤其兴盛。光武帝刘秀曾征召过故人严子陵,但严子陵却宁愿在富春江钓鱼。东汉末年,各派豪族军阀拥兵割据,为确保各自发展,争将天下名士罗致幕下,以壮势力,这导致了幕僚制度进一步发展。
东晋时期,权臣桓温图谋篡夺天下,参军郗超为他谋划。谢安与王坦之曾经去拜访桓温,谈论国家大事,桓温就让郗超藏在幕帐之后偷听。没想到一阵风吹来,吹开了帘帐,郗超露了出来,谢安笑道:“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幕宾”一说。南北朝时期,名士庾杲之受聘到王俭的幕府去做长史,有朋友表示祝贺,说有这样的名士入幕,好比芙蓉依傍着莲花池的绿水。后人因为这个典故,往往将幕府雅称为“莲幕”。
古时师爷的职责,主要在于协助判案、管理钱粮、起草文书、整理档案等。与此相呼应,师爷也分为五大类:刑名、钱谷、挂号、征比、书记。在州县以刑名、钱谷二者责任最为重大,地位也较其他师爷为尊。
明清地方官府是行政和司法合一,地方官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司法长官。他们所管的事主要有两件:一是审理刑事、民事案件,二是征收钱粮,上交藩库。清代有人说,州县衙门里总是响着“三声”——板子声、算盘声、戥子声。说的就是地方官府所处理的事主要是办案和征收钱粮这两类,这两类事中,又以办案最为重要。清代有一种说法,叫“亲民首在理讼”,即是说办案是亲民之官(州县官)的首要大事。案子办得好坏,是朝廷衡量地方官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志。所以,地方官都很重视案件的审理。
但是,清代地方官多是科举出身的“读书不读律”的士人,必须仰仗精通理讼的师爷来协助办理。清人陆向荣《瘦石山房笔记》云:“近日官途多依靠幕友,而于读律毫不讲解。”(《引自牧令书辑要·刑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由于师爷在案子审判中掌握重权,所以很多人的祸福生死就操在他们手里。清代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三》中记述一位时人所说的话:“幕府宾佐,非官而操官之权,笔墨之间,动关生死,为善易,为恶亦易。”清代绍兴山阴人金植因为亲戚和同乡中有很多当刑名师爷,所以对此感触尤深,他说:“一切入幕主文之法家”,执笔时一定要“切切警醒”“倘稍有冤抑,一著点墨,则人命立休于笔下”(《不下带编》卷七)。另一个绍兴人俞蛟也说:刑名师爷“按律引例,以判罪人,生死所争,在毫厘间。”(《梦厂杂著·纪西粤幕》)
师爷一行多与文书案牍打交道,因此只有读书人才能胜任,读书做官是学子毕业所孜孜以求的目标。许多人为此皓首穷经、老死牖下。但是,对于大多数师爷来说,这种梦想不再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科考失意后,及时退出改习此业的,有的从事这一行长达几十年,不再以科举为念。
入幕得势的师爷,往往成为盈利之徒,甚至声色犬马无所不为。万维翰就感叹过:“幕中之流品,最为错杂,有宦辙覆车,借人酒杯,自浇块垒;有贵胄飘零,摒挡纨绔,入幕效颦;又有以铁砚难磨,青毡冷淡,变业谋生……”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既然师爷群体的成分这么复杂,品行不端者就在所难免,上下勾结、朋比为奸的大有人在,欺上瞒下、涂改公文、把持官府、胡解案例者也不乏其人。
清代徐珂所辑的《清稗类钞》中,便对师爷的此种伎俩有着生动的描述。在师爷中,最能作弊的是刑名师爷,因为清代颁布的法令多不甚确切,对一个具体的案件,多半是根据以往的成例来判定,这样就给了师爷上下其手的机会,许多冤狱,都由他们操持。如同治年间轰动京城的杨乃武冤狱,便有一绍兴师爷不光彩的表演,他私通案犯,逼取伪供,致成大狱。丁宝桢为福建巡抚时,某县有开棺剥取尸身衣饰一案,该县刑名师爷为替县令掩饰,在文书上故意用模糊含混字样,以图蒙混过关,终被查出。这样的事例,在晚清文献上并不少见。无怪乎当时的人对师爷以“搞来搞去,终是小人”嗤之以鼻了。
民国初年,有的师爷摇身一变成为民国幕僚,但师爷体制余习未尽,职业思想还没有变过来。民国幕僚人数之多不亚于清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军政长官普遍重视幕僚,这些幕僚被称为顾问、参议、参谋、秘书、副官等,实际上就是清代师爷称谓的花样翻新。
历史上文人历来有重视文史的传统,许多师爷因长期游幕,笔记作品多载当地风土人情、社会百态,如邬斯道《游梁草》《抚豫宣化录记载河南之事》《全庶熙日记》载滇黔两省事,宣鼎《秋雨夜灯录》详述清末社会大量丑恶现象。另一个师爷吴炽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写成《客窗闲话》及《续客窗闲话》,书中描述的活脱是一幅社会百态图。这些著作不仅文字可读,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那些运筹于历史帷幄之中,周旋于帝王将相之间,盘桓于州县衙门之内的师爷们,“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如今只留下一段传奇的历史,一桩桩辛酸的往事,一个个缥缈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