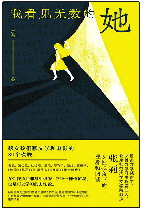成为“不驯服”的读者
齐鲁晚报 2022年12月10日
□张莉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领域执牛耳者张莉的最新力作《我看见无数的她》,首次系统讲述“如何用女性视角重新观看文学和电影”。《黄金时代》《山河故人》《BJ单身日记》《秋园》,三毛、杜拉斯、伍尔夫、波伏娃、娄烨……20个大众熟悉的故事,在女性视角下演绎出新的故事。这本书引导我们去“看见”被遮蔽、被隐身、被扭曲的女性,理解女性的切身之痛和困境,呈现男女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它亲切而细腻,让女性成为了可见的叙述主体,也成为了经验、思维、审美和言说的主体。
跳出受害者思维
同情地理解,但并不是代入角色。很多人看小说,喜欢代入角色。有人喜欢代入主角,而有人会代入配角或者剧中不知名的小角色。以女性视角同情地理解人物处境,并不意味着完全代入女主角。读这些作品时,固然要看到女主角的处境,但也要认识到她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也要看到她的身边人,以及那些弱势的人。一如那篇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文章《阁楼上的疯女人》。大家看《简·爱》,总会代入简·爱的视角,而在这篇文章里,批评家看到的是那位“疯女人”,是站在“疯女人”立场作的解读,由此,这部作品打开了我们理解女性处境、理解《简·爱》的新角度。这是我深为认同的立场。
本书强调的女性视角,其实是要站在低微处言说,这是一种价值观的表达。也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推拿》不是女主人公电影,但我依然将它放进此书里去解读,娄烨导演是我深为喜欢的导演,他的影片深具社会性别意识。《推拿》里,他以弱势和残缺者视角看世界,我以为,那正是一种“女性视角”的传达。
认出受害者身份,站在弱势立场理解,并不意味着用受害者思维看问题。《中年妇女恋爱史》讲述了一个女人在恋爱中不断受伤和不断被辜负的经历,但小说家并没有将女主角茉莉视作受害者。在此书中,我分析了这位女性的爱情观——在这位中年女性眼里,爱情只是一种人际关系,爱情的失去,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完结。站在女性视角,而不是将她当作爱情中的受害者看,会感受到这位中年女性的冷静和清醒,即使被年轻男人欺骗后,她也不是哭嚎和咒骂,而是认识到自己的轻信。这样的人生态度,正是她作为女性的主体性的发现,是一种对自我的确认。
“无论如何也不要把自己放到受害者的位置上去。”这是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中的话,我深以为然。在本书中你会看到,《立春》里王彩玲如何在一个对女人不友好的环境里逐渐变得强大。在我看来,王彩玲跳出了受害者思维去看自己的际遇,从而摆脱了自己的处境。当我们跳出了单向度思维,才能更好地获得成长和力量。
另外,对我而言,这本书里所讨论的女性形象,都不是生来如此,而是诸多因素促使而成。包括那些历史上的著名女性,无论杜拉斯,还是波伏瓦,她们都经历了少女期,经历了青年、中年和晚年,都经历了岁月的历练,而直到晚年,她们还依然在打开自己,在努力获得力量,向这个世界学习。她们和女性主义的关系,和女性写作的关系,经历了漫长的纠缠,最终她们确认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女性主义者的身份,也就是说,她们是在生活中完成自我的。
确认作为读者的主体性
成为不驯服的读者,确认作为读者的主体性。好故事或者好电影,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入口和路径,也可能卷起我们的情感,控制我们的理解方式和视角。尤其是面对经典作品时,前人已经积累许多固定理解方式和认知,我们是否敢于打破那些固化的想象?
想到几年前在研究生课上和同学们一起读沈从文《萧萧》的经历。在乡村的语境里,城里的女学生是被妖魔化的。在老祖父那里,女学生“事事都稀奇古怪,和庄稼人不同,有的简直还可说岂有此理”。祖父的讲述让村人们哄笑,可听故事的少女却不这么认为,甚至听到祖父笑谈后,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的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
这一场景让我念念不忘。《萧萧》中,是谁在讲女学生的故事?一位是老祖父,一位是“花狗”。老祖父把女学生作为笑谈,“花狗”则以此博得萧萧的好感,引诱她。在两位乡间男人的讲述里,女学生形象被扭曲、变形、妖魔化,但作为听众的萧萧,却没有被迷惑,她没有汲取到他们希冀她汲取的,相反,她幻想的却是自己有一天像女学生一样坐在汽车里,像女学生一样剪头发,像女学生一样去“自由”……即使懵懂无知,萧萧也试图从那个怪谈中挣脱出来,从那个千疮百孔的故事里获得启悟和滋养。所以,在被诱惑怀孕后,她想到的是要逃跑,去做女学生,过另一种生活。没有能离开村庄是萧萧的运气不好,而想离开却是她主体性的表达。我想说的是,萧萧的可爱在于,在一个扭曲的故事里,她选择的是不服从故事的逻辑,也不认同。
当故事塑造我们、社会规则塑造我们时,女性其实也有反塑造的能力,一如八十年前的乡村少女萧萧,每次遇到困难时,她都会想到女学生,因为那意味着命运的另一种可能。换言之,祖父们一直想塑造萧萧,但萧萧摆脱了这种塑造,对自我进行了反塑造,萧萧从故事中获得了她想获得的东西。
重识女性天地的辽阔
萨义德曾经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分析《曼斯菲尔德庄园》时说,尽管奥斯汀写的只是家内的故事,但是,她的故事里,有着隐秘的对远方帝国的想象和理解,那些“形式上的丰富、历史的真实和预见性”,都包裹在范妮的故事里,因此,“我们不应该误解她对外部世界的有限的提及,她对工作、事件的过程和阶级的些微的强调,和她的把日常不可调和的道德抽象化的能力。”说得多么好。女性的故事里固然有儿女情,有家务事,但是,话语的另一端,还连接着天地、湖海、江河,连接着勇气、智慧、力量。
如何从女性视角汲取故事的营养,如何从女性故事中获得启悟,是我在这本书里试图完成的。女性视角,是一种立场,但也是价值观和方法论。它使我们更丰富,更有独立性,它使我们远离狭隘和盲目。女性视角的解读,最终目的是助读者成为有同情心、理解力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有质疑能力和批判能力的独立思考者。
故事是倾诉。故事是历险。故事一直在风中传扬,而讲故事的人早已走远。那么,今天的我们如何读、怎样读,如何听、怎样听?钥匙在小说家笔尖里,也在我们读者手中。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定会从这些故事中成长的——不一定成为故事希望我们成长的样子,相反,我们要成为我们想成为的样子。
女性故事是女性命运的讲述。女性的故事里有女性,也一定还有男人和世界,有山高水长,也有儿女情深。对女人与女性身份的关注、对女性视角的强调从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这个世界多么丰富、芜杂、辽远,它从来都不是黑白分明、男女对峙。
(节选自《我看见无数的她》序言)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领域执牛耳者张莉的最新力作《我看见无数的她》,首次系统讲述“如何用女性视角重新观看文学和电影”。《黄金时代》《山河故人》《BJ单身日记》《秋园》,三毛、杜拉斯、伍尔夫、波伏娃、娄烨……20个大众熟悉的故事,在女性视角下演绎出新的故事。这本书引导我们去“看见”被遮蔽、被隐身、被扭曲的女性,理解女性的切身之痛和困境,呈现男女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它亲切而细腻,让女性成为了可见的叙述主体,也成为了经验、思维、审美和言说的主体。
跳出受害者思维
同情地理解,但并不是代入角色。很多人看小说,喜欢代入角色。有人喜欢代入主角,而有人会代入配角或者剧中不知名的小角色。以女性视角同情地理解人物处境,并不意味着完全代入女主角。读这些作品时,固然要看到女主角的处境,但也要认识到她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也要看到她的身边人,以及那些弱势的人。一如那篇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文章《阁楼上的疯女人》。大家看《简·爱》,总会代入简·爱的视角,而在这篇文章里,批评家看到的是那位“疯女人”,是站在“疯女人”立场作的解读,由此,这部作品打开了我们理解女性处境、理解《简·爱》的新角度。这是我深为认同的立场。
本书强调的女性视角,其实是要站在低微处言说,这是一种价值观的表达。也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推拿》不是女主人公电影,但我依然将它放进此书里去解读,娄烨导演是我深为喜欢的导演,他的影片深具社会性别意识。《推拿》里,他以弱势和残缺者视角看世界,我以为,那正是一种“女性视角”的传达。
认出受害者身份,站在弱势立场理解,并不意味着用受害者思维看问题。《中年妇女恋爱史》讲述了一个女人在恋爱中不断受伤和不断被辜负的经历,但小说家并没有将女主角茉莉视作受害者。在此书中,我分析了这位女性的爱情观——在这位中年女性眼里,爱情只是一种人际关系,爱情的失去,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完结。站在女性视角,而不是将她当作爱情中的受害者看,会感受到这位中年女性的冷静和清醒,即使被年轻男人欺骗后,她也不是哭嚎和咒骂,而是认识到自己的轻信。这样的人生态度,正是她作为女性的主体性的发现,是一种对自我的确认。
“无论如何也不要把自己放到受害者的位置上去。”这是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中的话,我深以为然。在本书中你会看到,《立春》里王彩玲如何在一个对女人不友好的环境里逐渐变得强大。在我看来,王彩玲跳出了受害者思维去看自己的际遇,从而摆脱了自己的处境。当我们跳出了单向度思维,才能更好地获得成长和力量。
另外,对我而言,这本书里所讨论的女性形象,都不是生来如此,而是诸多因素促使而成。包括那些历史上的著名女性,无论杜拉斯,还是波伏瓦,她们都经历了少女期,经历了青年、中年和晚年,都经历了岁月的历练,而直到晚年,她们还依然在打开自己,在努力获得力量,向这个世界学习。她们和女性主义的关系,和女性写作的关系,经历了漫长的纠缠,最终她们确认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女性主义者的身份,也就是说,她们是在生活中完成自我的。
确认作为读者的主体性
成为不驯服的读者,确认作为读者的主体性。好故事或者好电影,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入口和路径,也可能卷起我们的情感,控制我们的理解方式和视角。尤其是面对经典作品时,前人已经积累许多固定理解方式和认知,我们是否敢于打破那些固化的想象?
想到几年前在研究生课上和同学们一起读沈从文《萧萧》的经历。在乡村的语境里,城里的女学生是被妖魔化的。在老祖父那里,女学生“事事都稀奇古怪,和庄稼人不同,有的简直还可说岂有此理”。祖父的讲述让村人们哄笑,可听故事的少女却不这么认为,甚至听到祖父笑谈后,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的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
这一场景让我念念不忘。《萧萧》中,是谁在讲女学生的故事?一位是老祖父,一位是“花狗”。老祖父把女学生作为笑谈,“花狗”则以此博得萧萧的好感,引诱她。在两位乡间男人的讲述里,女学生形象被扭曲、变形、妖魔化,但作为听众的萧萧,却没有被迷惑,她没有汲取到他们希冀她汲取的,相反,她幻想的却是自己有一天像女学生一样坐在汽车里,像女学生一样剪头发,像女学生一样去“自由”……即使懵懂无知,萧萧也试图从那个怪谈中挣脱出来,从那个千疮百孔的故事里获得启悟和滋养。所以,在被诱惑怀孕后,她想到的是要逃跑,去做女学生,过另一种生活。没有能离开村庄是萧萧的运气不好,而想离开却是她主体性的表达。我想说的是,萧萧的可爱在于,在一个扭曲的故事里,她选择的是不服从故事的逻辑,也不认同。
当故事塑造我们、社会规则塑造我们时,女性其实也有反塑造的能力,一如八十年前的乡村少女萧萧,每次遇到困难时,她都会想到女学生,因为那意味着命运的另一种可能。换言之,祖父们一直想塑造萧萧,但萧萧摆脱了这种塑造,对自我进行了反塑造,萧萧从故事中获得了她想获得的东西。
重识女性天地的辽阔
萨义德曾经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分析《曼斯菲尔德庄园》时说,尽管奥斯汀写的只是家内的故事,但是,她的故事里,有着隐秘的对远方帝国的想象和理解,那些“形式上的丰富、历史的真实和预见性”,都包裹在范妮的故事里,因此,“我们不应该误解她对外部世界的有限的提及,她对工作、事件的过程和阶级的些微的强调,和她的把日常不可调和的道德抽象化的能力。”说得多么好。女性的故事里固然有儿女情,有家务事,但是,话语的另一端,还连接着天地、湖海、江河,连接着勇气、智慧、力量。
如何从女性视角汲取故事的营养,如何从女性故事中获得启悟,是我在这本书里试图完成的。女性视角,是一种立场,但也是价值观和方法论。它使我们更丰富,更有独立性,它使我们远离狭隘和盲目。女性视角的解读,最终目的是助读者成为有同情心、理解力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有质疑能力和批判能力的独立思考者。
故事是倾诉。故事是历险。故事一直在风中传扬,而讲故事的人早已走远。那么,今天的我们如何读、怎样读,如何听、怎样听?钥匙在小说家笔尖里,也在我们读者手中。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定会从这些故事中成长的——不一定成为故事希望我们成长的样子,相反,我们要成为我们想成为的样子。
女性故事是女性命运的讲述。女性的故事里有女性,也一定还有男人和世界,有山高水长,也有儿女情深。对女人与女性身份的关注、对女性视角的强调从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这个世界多么丰富、芜杂、辽远,它从来都不是黑白分明、男女对峙。
(节选自《我看见无数的她》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