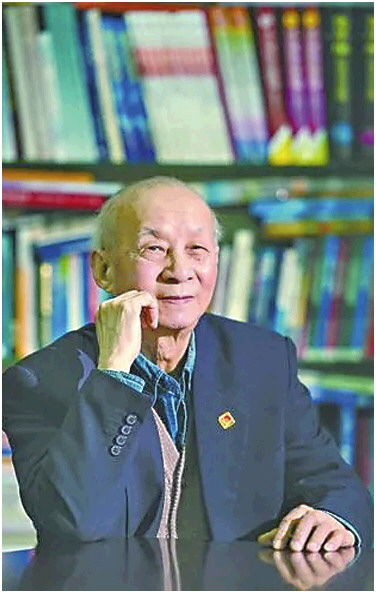“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院士逝世
他一生都在追光路上奔跑
齐鲁晚报 2022年12月19日
12月16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官网发布了《中国宽带发展白皮书(2022年)》,其中写道:截至2022年9月底,中国光纤用户达5.5亿户,数量居全球首位。这5.5亿用户能使用高质量的光纤通信,都要感谢一个人——“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就在上述白皮书发布前一日,赵梓森在武汉逝世,享年90岁。
赵梓森是我国光纤通信技术的主要奠基人和公认的开拓者。和今天动辄百万千万元投入采购科研设备相比,他在单位厕所旁的清洗室里,搭建起简易实验室,利用一台破旧机床、几盘电炉、几只烧瓶,靠“土法创新”拉出我国第一根实用型石英光纤。
赵梓森一生都在跟“光”打交道,四十余载低调筑梦、追光前行,他见证了中国的光纤事业从无到有,从蹒跚起步到世界先进水平,也见证了中国光谷从“一束光”到“一座城”的传奇。
记者 于海霞 整理
从小喜欢搞发明创造
1932年2月,赵梓森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母亲靠做缝纫活、销售小商品贴补家用。儿时,兄妹八人,家中负担沉重。年少爱玩的日子里,买不起玩具,赵梓森就想方设法自己制作。比如看到别人有玩具飞机,而自己的零花钱不够,他就动手自制。胶水贵,他就买丙酮和废弃的乒乓球壳融合来制作胶水;买不起螺旋桨,就找来木块自己削;把竹子劈开削细成竹丝,弯起来再糊上纸,做成机体。
看似“小打小闹”的发明创造,让赵梓森的数理化成绩非常优秀,“制取氢气,就涉及化学问题;做模型飞机,不懂几何就不行;做小马达,更离不开物理。”
十多岁时,赵梓森带着弟弟尝试组装矿石收音机,买不起半导体,就把矿石敲碎后用火加温使铜氧化,自制检波氧化铜,然后钉上弹簧指针,装上耳机,然而当他们兴高采烈地爬到屋顶去检测时,却没有收到任何信号——原来,能检波的是氧化亚铜半导体。彼时青春少年无法想象,半个世纪后,自己凭借创新让千家万户用手机就可以实现千万里的通话,成为“中国光纤之父”。
在学校,赵梓森喜欢理科,尤其是数学,经常因为善于思考受到老师的表扬。他的动手能力也很强,喜欢制作航模。由于对理工科过于热衷,他偏科了,英语、历史、地理等学科常常不能及格,中考时勉强考上了一所普通高中。进入高中后,赵梓森明白了,学习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不喜欢的课也得认真学。
初中化学老师龚叔云的激励,也影响着这位“中国光纤之父”终身。因为欣赏他勤动手、爱钻研的好品质,龚老师曾专门写信鼓励已经读高中的赵梓森。信中那句“你以后一定会成为科学家”的话语,无数次萦绕在追梦少年的心头。
1949年考大学时,他不敢报考学费便宜但难度较高的公立大学理工科,也没有报考学费高的私立大学,最终考上了浙江大学农学院。然而,植物学、细胞学等科目他提不起兴趣,干脆退学重新参加高考。这次,他考入了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没承想,课程相似,他再次退学。在母亲的支持下,1950年,赵梓森入读以理工著称的上海大同大学,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电子学、电机学、通信学,为他日后接触和研制光纤打下了基础。
1954年9月,大学毕业的赵梓森被分配到武汉电信学校(武汉市邮电科学研究院的前身)做了一名中专教师。当时一起分到学校的年轻教师,很多人觉得在中专教书很容易,平时常常打牌下象棋,而赵梓森在工作之余仍每天坚持学习。他觉得自己在大学时学的知识太浅,已跟不上时代。为弥补差距,他重新自学苏联教材的微积分、电工原理、无线电原理等,还补习了英语、俄语、日语等外语,仅用3个月就背下一本简明英语字典。1958年,武汉电信学校升格为武汉邮电学院,开始本科招生,赵梓森也从一名中专老师变成了大学老师。
在厕所旁拉出第一根光纤
1969年,北京邮电科学研究院将国家科研项目“激光大气传输通信”以及项目执行人员转移到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到了1971年,院领导认为项目进展太慢,要求“技术好”的赵梓森加入进来,并牵头负责。项目紧急,而实验所需的重要设备平行光管要一年以后才能到货。赵梓森从小练就的“土法上马”大显身手,他采用太阳光做平行光源来代替平行光管进行校正,仅用两天就突破了。
一年多工夫,项目组的大气传输光通信距离从8米飞跃到10千米。当大家欣喜万分时,赵梓森却很淡定,大气传输光通信技术受天气影响大,一旦碰上雨、雪、雾等天气,就无法完成通信,“总不可能下雨下雪时,老百姓不打电话吧”。他意识到,搞大气传输光通信就是走死胡同,必须寻求新的方法。
1973年,赵梓森偶然在图书馆的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消息,美国在搞光纤通信。玻璃丝还能通信?痴迷科研的赵梓森很快意识到光通信有希望。
“我提出要发展’光纤通信’的科研项目,大多数人反对,包括邮电部、武汉院和北京院的领导。有领导在几十人的会上说:’玻璃丝怎么能通信!赵梓森你不要胡搞,要花几千万,你负得了责吗?’”赵梓森在《中国光纤通信发展的回顾》一文中回忆。然而,赵梓森和其他同事还是毅然决然开始了研究光纤之路。
没有正规的实验室,就在实验楼厕所旁的清洗室内做化学实验。没有现成设备,就用旧机床加工。没有精密调准器,就用螺丝钉加橡皮泥拼接。在一次试验中,四氯化硅从管道中溢出,生成的氯气和盐酸冲进赵梓森的眼睛和口腔,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口腔也发炎,直淌黄水。同事将已经昏迷的赵梓森送进医院急救,“医生都愣住了,他们没见过这样的情况,不会治”。赵梓森刚好苏醒,他说:“蒸馏水冲眼睛,打吊针。”两小时后,身体恢复正常,赵梓森又回到了实验室。
1976年3月,武汉邮科院一个厕所旁的简陋实验室里,一根长度为17米的“玻璃细丝”——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从科研人员赵梓森手中缓缓流过。中国第一根光纤就这样诞生了。
在当年举办的“邮电部工业学大庆展览会”上,赵梓森通过自行研制的光纤,成功传输黑白电视信号,引起国家的重视。光纤通信因此被破格列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我国的光纤通信技术从此迈入了“快车道”。1979年,赵梓森团队拉制出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每公里衰耗只有4分贝的光纤,就此拉开了中国光纤通信事业的序幕。三年后,中国老百姓真正开始用光纤打电话。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1981年,原国家邮电部和国家科委确定在武汉建立一条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意在通过实际使用完成商用试验以定型推广。由于其限于1982年完成,所以简称“八二工程”。赵梓森在项目建设中负责后台指挥。
按照设计方案,这是一个市内电话局间的中继工程,跨越长江、汉水,贯穿武汉三镇,连接武汉四个市话分局。因为早期缺乏检修经验和检修仪器,每次都是相关人员一齐出动,赵梓森曾和20多个同事挤在院里分配的一辆额定8人的面包车里,到处奔波。有了这股劲头,事还能不成?1982年12月31日,中国光纤通信的第一个实用化系统——“八二工程”终于按期全线开通,正式进入武汉市市话网,也标志着中国进入光纤数字化通信时代。
“八二工程”之后,赵梓森及团队又先后完成了数十项由短及长的光纤通信架设工程。其中,1987年完成的全长244.86公里的“汉荆沙工程”(武汉—荆州—沙市),被作为全国同类行业的示范;1993年完成的全长3046公里的“京汉广工程”(北京—武汉—广州),跨越北京、湖北、湖南、广东等6省市,是当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架空光缆通信线路。就这样,在10年时间,赵梓森的团队就将大容量高传速的光纤通信线路连通到天南海北,完成了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工作。
1983年,赵梓森被任命为武汉邮科院总工程师,2年后升任副院长。他这一辈子都扑在了光通信事业上。光纤在长距离传输时常发生意外断裂情况,他不记得有多少次从睡梦中被叫醒,赶往几十公里外寻找断点、修理光纤。
从“一束光”到“一座城”
2000年5月7日,赵梓森和25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专家联名向国家呈交了关于在武汉建设国家级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国光谷”的建议书;同年5月31日,武汉中国光谷领导小组聘请赵梓森、李德仁院士为“中国光谷”首席科学家;同年6月30日,国家信息产业部正式作出答复:支持以国家级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基地,建设集研究开发、产品生产、企业孵化、人才培养等为一体的光电子产业基地。至此,“武汉·中国光谷”正式诞生。
2001年2月28日,科技部正式批准在武汉建立国家光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命名为武汉·中国光谷。光谷建成后,很快达成了预期目标。从2001年立项批建到2007年,只用了不到六年时间,武汉·中国光谷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光电子产品研产基地。
2018年,武汉邮科院研发的光纤,一根可实现67.5亿对人同时通话。如今,武汉邮科院已发展成中央企业中国信科集团。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光通信技术强国,市场份额占到全世界一半以上。
1995年,赵梓森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后,赵梓森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担任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首席顾问、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生导师。在人生的晚年,赵梓森空闲的时候,大多都在查阅国内外最先进的光纤通信技术,不断地了解掌握新动向。他也告诫年轻人跟上时代、引领时代。
时至今日,大浪淘沙,“光谷”已专指“武汉·中国光谷”。从“一束光”到“一座城”,这块曾经被戏称为“武汉地图外的两厘米”的荒野之地,已经成长为518平方千米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在赵梓森的日常生活中,拉小提琴是一项重要日程——这个爱好,他从年轻一直坚持到年老。他喜欢门德尔松、巴赫、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天鹅》更是每天必拉的曲目,一直到80岁之后手指灵敏度下降,才开始放弃拉琴,改听音乐。“灵感,常常伴随着他的琴声起舞。即使再困难的时候,他仍然是个乐观的舞者。”赵梓森的妻子、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范幼英说。
“40年前,我只是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光纤通信,跟上世界潮流;没想到,4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光纤强国。”2018年,时年86岁的赵梓森感慨万千。
素材来源:长江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网、环球人物等
赵梓森是我国光纤通信技术的主要奠基人和公认的开拓者。和今天动辄百万千万元投入采购科研设备相比,他在单位厕所旁的清洗室里,搭建起简易实验室,利用一台破旧机床、几盘电炉、几只烧瓶,靠“土法创新”拉出我国第一根实用型石英光纤。
赵梓森一生都在跟“光”打交道,四十余载低调筑梦、追光前行,他见证了中国的光纤事业从无到有,从蹒跚起步到世界先进水平,也见证了中国光谷从“一束光”到“一座城”的传奇。
记者 于海霞 整理
从小喜欢搞发明创造
1932年2月,赵梓森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母亲靠做缝纫活、销售小商品贴补家用。儿时,兄妹八人,家中负担沉重。年少爱玩的日子里,买不起玩具,赵梓森就想方设法自己制作。比如看到别人有玩具飞机,而自己的零花钱不够,他就动手自制。胶水贵,他就买丙酮和废弃的乒乓球壳融合来制作胶水;买不起螺旋桨,就找来木块自己削;把竹子劈开削细成竹丝,弯起来再糊上纸,做成机体。
看似“小打小闹”的发明创造,让赵梓森的数理化成绩非常优秀,“制取氢气,就涉及化学问题;做模型飞机,不懂几何就不行;做小马达,更离不开物理。”
十多岁时,赵梓森带着弟弟尝试组装矿石收音机,买不起半导体,就把矿石敲碎后用火加温使铜氧化,自制检波氧化铜,然后钉上弹簧指针,装上耳机,然而当他们兴高采烈地爬到屋顶去检测时,却没有收到任何信号——原来,能检波的是氧化亚铜半导体。彼时青春少年无法想象,半个世纪后,自己凭借创新让千家万户用手机就可以实现千万里的通话,成为“中国光纤之父”。
在学校,赵梓森喜欢理科,尤其是数学,经常因为善于思考受到老师的表扬。他的动手能力也很强,喜欢制作航模。由于对理工科过于热衷,他偏科了,英语、历史、地理等学科常常不能及格,中考时勉强考上了一所普通高中。进入高中后,赵梓森明白了,学习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不喜欢的课也得认真学。
初中化学老师龚叔云的激励,也影响着这位“中国光纤之父”终身。因为欣赏他勤动手、爱钻研的好品质,龚老师曾专门写信鼓励已经读高中的赵梓森。信中那句“你以后一定会成为科学家”的话语,无数次萦绕在追梦少年的心头。
1949年考大学时,他不敢报考学费便宜但难度较高的公立大学理工科,也没有报考学费高的私立大学,最终考上了浙江大学农学院。然而,植物学、细胞学等科目他提不起兴趣,干脆退学重新参加高考。这次,他考入了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没承想,课程相似,他再次退学。在母亲的支持下,1950年,赵梓森入读以理工著称的上海大同大学,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电子学、电机学、通信学,为他日后接触和研制光纤打下了基础。
1954年9月,大学毕业的赵梓森被分配到武汉电信学校(武汉市邮电科学研究院的前身)做了一名中专教师。当时一起分到学校的年轻教师,很多人觉得在中专教书很容易,平时常常打牌下象棋,而赵梓森在工作之余仍每天坚持学习。他觉得自己在大学时学的知识太浅,已跟不上时代。为弥补差距,他重新自学苏联教材的微积分、电工原理、无线电原理等,还补习了英语、俄语、日语等外语,仅用3个月就背下一本简明英语字典。1958年,武汉电信学校升格为武汉邮电学院,开始本科招生,赵梓森也从一名中专老师变成了大学老师。
在厕所旁拉出第一根光纤
1969年,北京邮电科学研究院将国家科研项目“激光大气传输通信”以及项目执行人员转移到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到了1971年,院领导认为项目进展太慢,要求“技术好”的赵梓森加入进来,并牵头负责。项目紧急,而实验所需的重要设备平行光管要一年以后才能到货。赵梓森从小练就的“土法上马”大显身手,他采用太阳光做平行光源来代替平行光管进行校正,仅用两天就突破了。
一年多工夫,项目组的大气传输光通信距离从8米飞跃到10千米。当大家欣喜万分时,赵梓森却很淡定,大气传输光通信技术受天气影响大,一旦碰上雨、雪、雾等天气,就无法完成通信,“总不可能下雨下雪时,老百姓不打电话吧”。他意识到,搞大气传输光通信就是走死胡同,必须寻求新的方法。
1973年,赵梓森偶然在图书馆的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消息,美国在搞光纤通信。玻璃丝还能通信?痴迷科研的赵梓森很快意识到光通信有希望。
“我提出要发展’光纤通信’的科研项目,大多数人反对,包括邮电部、武汉院和北京院的领导。有领导在几十人的会上说:’玻璃丝怎么能通信!赵梓森你不要胡搞,要花几千万,你负得了责吗?’”赵梓森在《中国光纤通信发展的回顾》一文中回忆。然而,赵梓森和其他同事还是毅然决然开始了研究光纤之路。
没有正规的实验室,就在实验楼厕所旁的清洗室内做化学实验。没有现成设备,就用旧机床加工。没有精密调准器,就用螺丝钉加橡皮泥拼接。在一次试验中,四氯化硅从管道中溢出,生成的氯气和盐酸冲进赵梓森的眼睛和口腔,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口腔也发炎,直淌黄水。同事将已经昏迷的赵梓森送进医院急救,“医生都愣住了,他们没见过这样的情况,不会治”。赵梓森刚好苏醒,他说:“蒸馏水冲眼睛,打吊针。”两小时后,身体恢复正常,赵梓森又回到了实验室。
1976年3月,武汉邮科院一个厕所旁的简陋实验室里,一根长度为17米的“玻璃细丝”——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从科研人员赵梓森手中缓缓流过。中国第一根光纤就这样诞生了。
在当年举办的“邮电部工业学大庆展览会”上,赵梓森通过自行研制的光纤,成功传输黑白电视信号,引起国家的重视。光纤通信因此被破格列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我国的光纤通信技术从此迈入了“快车道”。1979年,赵梓森团队拉制出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每公里衰耗只有4分贝的光纤,就此拉开了中国光纤通信事业的序幕。三年后,中国老百姓真正开始用光纤打电话。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1981年,原国家邮电部和国家科委确定在武汉建立一条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意在通过实际使用完成商用试验以定型推广。由于其限于1982年完成,所以简称“八二工程”。赵梓森在项目建设中负责后台指挥。
按照设计方案,这是一个市内电话局间的中继工程,跨越长江、汉水,贯穿武汉三镇,连接武汉四个市话分局。因为早期缺乏检修经验和检修仪器,每次都是相关人员一齐出动,赵梓森曾和20多个同事挤在院里分配的一辆额定8人的面包车里,到处奔波。有了这股劲头,事还能不成?1982年12月31日,中国光纤通信的第一个实用化系统——“八二工程”终于按期全线开通,正式进入武汉市市话网,也标志着中国进入光纤数字化通信时代。
“八二工程”之后,赵梓森及团队又先后完成了数十项由短及长的光纤通信架设工程。其中,1987年完成的全长244.86公里的“汉荆沙工程”(武汉—荆州—沙市),被作为全国同类行业的示范;1993年完成的全长3046公里的“京汉广工程”(北京—武汉—广州),跨越北京、湖北、湖南、广东等6省市,是当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架空光缆通信线路。就这样,在10年时间,赵梓森的团队就将大容量高传速的光纤通信线路连通到天南海北,完成了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工作。
1983年,赵梓森被任命为武汉邮科院总工程师,2年后升任副院长。他这一辈子都扑在了光通信事业上。光纤在长距离传输时常发生意外断裂情况,他不记得有多少次从睡梦中被叫醒,赶往几十公里外寻找断点、修理光纤。
从“一束光”到“一座城”
2000年5月7日,赵梓森和25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专家联名向国家呈交了关于在武汉建设国家级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国光谷”的建议书;同年5月31日,武汉中国光谷领导小组聘请赵梓森、李德仁院士为“中国光谷”首席科学家;同年6月30日,国家信息产业部正式作出答复:支持以国家级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基地,建设集研究开发、产品生产、企业孵化、人才培养等为一体的光电子产业基地。至此,“武汉·中国光谷”正式诞生。
2001年2月28日,科技部正式批准在武汉建立国家光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命名为武汉·中国光谷。光谷建成后,很快达成了预期目标。从2001年立项批建到2007年,只用了不到六年时间,武汉·中国光谷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光电子产品研产基地。
2018年,武汉邮科院研发的光纤,一根可实现67.5亿对人同时通话。如今,武汉邮科院已发展成中央企业中国信科集团。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光通信技术强国,市场份额占到全世界一半以上。
1995年,赵梓森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后,赵梓森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担任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首席顾问、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生导师。在人生的晚年,赵梓森空闲的时候,大多都在查阅国内外最先进的光纤通信技术,不断地了解掌握新动向。他也告诫年轻人跟上时代、引领时代。
时至今日,大浪淘沙,“光谷”已专指“武汉·中国光谷”。从“一束光”到“一座城”,这块曾经被戏称为“武汉地图外的两厘米”的荒野之地,已经成长为518平方千米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在赵梓森的日常生活中,拉小提琴是一项重要日程——这个爱好,他从年轻一直坚持到年老。他喜欢门德尔松、巴赫、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天鹅》更是每天必拉的曲目,一直到80岁之后手指灵敏度下降,才开始放弃拉琴,改听音乐。“灵感,常常伴随着他的琴声起舞。即使再困难的时候,他仍然是个乐观的舞者。”赵梓森的妻子、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范幼英说。
“40年前,我只是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光纤通信,跟上世界潮流;没想到,4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光纤强国。”2018年,时年86岁的赵梓森感慨万千。
素材来源:长江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网、环球人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