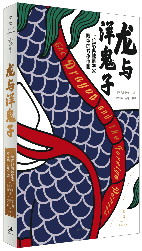西方学者眼中百年前的中国故事
齐鲁晚报 2023年01月07日
□季东
《龙与洋鬼子》一书是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亲历记。安特生亲身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完成北伐的巨变,也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凯等重要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对于袁世凯的统治,张勋复辟,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争斗,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都有细密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与思考。除此之外,作为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安特生在书中留下的考察经历,也具有重要价值。这本亲历记像一幅风俗画,用生动的文字和珍贵的图像,透过西方学者的独特视角,讲述了百年前活生生的中国故事。
“仰韶文化之父”
安特生,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1910年第11届世界地质学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安特生被任命为大会秘书长。
由于瑞典没有参加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各种帝国主义活动,1900年八国联军中也没有瑞典的军队,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方保持着与瑞典王国的友好关系。因此,北洋政府于1914年邀请瑞典人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
安特生组织了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并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者。由于成功勘探到了北京北边丘陵地带的铁矿,1915年春天,在农商部总长周自齐的安排下,安特生有机会见到了时任大总统袁世凯。
安特生在考古领域的奇遇更多。他于1918年首次到访周口店,后来在龙骨山发现了该地区不该存在的石英。他意识到这可能表明有史前人类存在,因此他安排助手进行发掘工作。最终,在1926年,瑞典国王访问北京之际,安特生宣布发现了两颗人类牙齿,这些后来被确定为北京猿人的最早发现。在与袁富力等中国考古人员的合作下,安特生随后又在河南省黄河沿岸发现了史前新石器时代遗址。1921年,这些遗迹被命名为仰韶文化,他也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1924年初,安特生在甘肃兰州的集市上收购彩陶,机缘巧合,他发现了一名烟贩的货摊上,摆着一只精美但是破旧的彩陶罐。经询问得知,彩陶罐来源于洮河河谷。他与随从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洮河流域,同时与当时的甘肃政府取得联系,获得考古许可证书。在那里,他成功发现了马家窑文化。
安特生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是空前的。他将近代考古的知识、科学原则、理念和方法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并且运用这些方法在与他的众多中国助手的合作中,取得了不凡成就。在此之前,中国只有金石学,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安特生将田野调查的方法介绍给他的中国助手们,他为中国的考古学带来了一套近现代的发掘方法,同时他在实地考古的测量、绘图、辑录到标本采集方面,也都做出了典范。
由于安特生首先是地质学家,因此他在史前考古发掘中,特别重视地貌学、地层学的方法,分层学的科学原则,也为后来中国史前考古发掘打下了基础。他在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方面,做了具有预见性的工作,特别是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等多学科的运用,真正拉开了周口店遗址挖掘的序幕。而仰韶文化的发现,结束了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的历史。因为之前国际学术界公认,中国没有发现明确的石器时代的遗迹。
“洋鬼子”的幽默
安特生一生写了多本专著,其中《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国史前史研究》比较著名,《龙与洋鬼子》并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这本书的瑞典语版出版于1926年,一年后出版了德文版,两年后的1928年出版了英文版。原书出版45年后的1971年,又出版了日文版。
“洋鬼子”这个词汇似乎不那么友好。好友丁文江曾向安特生解释:“‘洋鬼子’不应理解为辱骂,而是动物学里的定义。人类有黑眼睛和黑头发;魔鬼有红头发和绿眼睛。因此,外国人属于后者。这简单明了、无可争议,就像卡尔·冯·林奈依据植物的生殖器官将植物加以分类一样。”
尽管从中国人的世界观出发,洋人被“科学地”归在了具有红头发和绿眼睛的魔鬼类,但安特生依然认为:“在拥挤的大街上,当孩子们或者愤怒的暴民围追堵截一位外国人,怒斥其为‘洋鬼子’时,这就是骂人的话了。”
所以,安特生将这本书命名为“龙与洋鬼子”,是希望运用反讽的手段产生幽默的效果。在西方的文化中,“龙”所代表的是一种邪恶的力量,而中国的“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洋鬼子”既是安特生,也指一般的西方人。因此,书名的含义就是“中国与西方”。
在安特生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很少有那些所谓异国情调的猎奇式描述,或将中国人归为人种学意义上几种类型化的样式。尽管他在中国以“洋人”自称,但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人的一种友善。他在《龙与洋鬼子》中写道:“一般来说,中国男人瘦而结实,女人的肩膀强壮而宽大,孩子们长得胖乎乎的,他们的眼睛清澈、明亮。”
《龙与洋鬼子》除了学术考察外,记载了很多路上他遇到的有趣见闻。比如在北京发生的沙尘暴,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当代的现象,其实不然。在某年二月的一天,安特生乘车从北京到天津,便遭遇了一场不寻常的“沙尘暴”。他写道:“其中有来自戈壁沙漠的美丽而干净的黄白色沙尘,这些沙尘落在城市上空,人们可以用小院里的桶把它搜集起来,这些堆成小山的灰尘又被风刮到了田野中去。”
由于当时的植被状况不好,在北京附近,安特生所到之处,几乎没有树木。“这个国家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树木,但某些受保护的森林,例如北京东北偏东的东陵,似乎表明早期有一片相连的森林,已经被当地人砍伐,其中大部分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更糟糕的是,山里的人用可怜的树枝生火,而自从原始森林被砍伐以来,山里就没有树木了,每一棵树的枝条都被小小的砍柴人无情地砍掉。”由此可知,北京城市四周的植树造林,植被覆盖率的提高,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作为一个外来者,安特生常常会有些别样的观察。比如关于沙眼,他这样记录:“在中国,沙眼或许是最严重的眼科疾病。它的传播方式非常奇特。在一切公共场所,不管是旅馆、剧院还是列车上,服务人员通常会为客人分发热气腾腾的毛巾供其洁面,毛巾上还常会有淡香。用这些毛巾擦脸虽然清爽舒适,但极不健康。因为毛巾经不同顾客反复使用,虽会被投进一个大壶里消毒,但壶中的水多半是温水而不是开水,达不到消毒的效果。通过这些毛巾,沙眼寄生虫便输送到了健康的眼睛里。根据中国人对卫生和清洁的观念,饭后或晚间在剧院观影时,用毛巾擦脸洁面这种方法并无不妥。在剧院里,把用过的毛巾卷起来,直接扔给大厅对面的热水壶旁的人,对服务员来说是种广受青睐的小聪明手段。”今天读来,这样的描述也是颇具年代感了。
挑战时间的力量
由于安特生的考古发掘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加之他当时所接触的都是中国学界最优秀的学者,因此他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识是深刻的。
他懂得从农耕文明角度评价中国人。“对庄稼生长执着地关注,使得中国农民几乎一天到晚都得不到空闲,这无疑培养了中国人特有的防御性以及对和平本能的热爱。长城,从山海关的海边一直延伸到甘肃的沙漠深处,在精神上与中国人惊人的消极抵抗力相对应,这种品质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最强大的力量。”此外,他认为“对学习和艺术的热爱以及崇尚”,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另一个特点。
那么,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安特生认为“那就是敢于挑战时间的力量”。“人们怕时间,时间却怕金字塔”是埃及人的一句古老谚语。其含义是:拥有肉身的人们,害怕时间,是因为时间会带来死亡;时间害怕金字塔,是因为不论过去多少年,金字塔仍然矗立着。
在金字塔面前,时间似乎失去了它的力量;而中国文化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安特生称:“所有早期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克里特宫殿的统治者、埃及金字塔的建造者、楔形文字的先民——都早已逝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伟大的孤独之中坚持了下来,作为他们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作品、哲学和艺术的直接继承人。”
进而,他指出:“许多在东方的外国人说,中国人缺乏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使我们成为爆炸式的引擎,并以更加疯狂的速度加快了我们的文化在这里的发展。但是很少有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在精神上蕴藏着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宝藏:他们会种植牡丹、养金鱼,或者在树荫下打坐,而西方人在努力追求装饰,或者为了发现一个微小的‘科学真理’而奋斗不已。”
安特生相信中国的未来是不可估量的,他指出:“也许有一天,开启世界新征程的重任又落在了东方人身上。今天,我们应该从中国身上学习的东西就是,历经千年,中国仍保持着民族文化的活力。在青铜器时代,古代埃及、克里特岛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的文明就因遭到野蛮人的破坏而中断,但是,中国人,从开天辟地之日起,连续四千余年,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繁荣。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安特生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并且他认为,中国的未来一定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而是东西文明的融合。今天读来,作为中国人,更应该有这样一种文化自信。
《龙与洋鬼子》一书是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亲历记。安特生亲身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完成北伐的巨变,也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凯等重要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对于袁世凯的统治,张勋复辟,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争斗,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都有细密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与思考。除此之外,作为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安特生在书中留下的考察经历,也具有重要价值。这本亲历记像一幅风俗画,用生动的文字和珍贵的图像,透过西方学者的独特视角,讲述了百年前活生生的中国故事。
“仰韶文化之父”
安特生,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1910年第11届世界地质学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安特生被任命为大会秘书长。
由于瑞典没有参加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各种帝国主义活动,1900年八国联军中也没有瑞典的军队,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方保持着与瑞典王国的友好关系。因此,北洋政府于1914年邀请瑞典人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
安特生组织了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并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者。由于成功勘探到了北京北边丘陵地带的铁矿,1915年春天,在农商部总长周自齐的安排下,安特生有机会见到了时任大总统袁世凯。
安特生在考古领域的奇遇更多。他于1918年首次到访周口店,后来在龙骨山发现了该地区不该存在的石英。他意识到这可能表明有史前人类存在,因此他安排助手进行发掘工作。最终,在1926年,瑞典国王访问北京之际,安特生宣布发现了两颗人类牙齿,这些后来被确定为北京猿人的最早发现。在与袁富力等中国考古人员的合作下,安特生随后又在河南省黄河沿岸发现了史前新石器时代遗址。1921年,这些遗迹被命名为仰韶文化,他也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1924年初,安特生在甘肃兰州的集市上收购彩陶,机缘巧合,他发现了一名烟贩的货摊上,摆着一只精美但是破旧的彩陶罐。经询问得知,彩陶罐来源于洮河河谷。他与随从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洮河流域,同时与当时的甘肃政府取得联系,获得考古许可证书。在那里,他成功发现了马家窑文化。
安特生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是空前的。他将近代考古的知识、科学原则、理念和方法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并且运用这些方法在与他的众多中国助手的合作中,取得了不凡成就。在此之前,中国只有金石学,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安特生将田野调查的方法介绍给他的中国助手们,他为中国的考古学带来了一套近现代的发掘方法,同时他在实地考古的测量、绘图、辑录到标本采集方面,也都做出了典范。
由于安特生首先是地质学家,因此他在史前考古发掘中,特别重视地貌学、地层学的方法,分层学的科学原则,也为后来中国史前考古发掘打下了基础。他在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方面,做了具有预见性的工作,特别是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等多学科的运用,真正拉开了周口店遗址挖掘的序幕。而仰韶文化的发现,结束了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的历史。因为之前国际学术界公认,中国没有发现明确的石器时代的遗迹。
“洋鬼子”的幽默
安特生一生写了多本专著,其中《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国史前史研究》比较著名,《龙与洋鬼子》并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这本书的瑞典语版出版于1926年,一年后出版了德文版,两年后的1928年出版了英文版。原书出版45年后的1971年,又出版了日文版。
“洋鬼子”这个词汇似乎不那么友好。好友丁文江曾向安特生解释:“‘洋鬼子’不应理解为辱骂,而是动物学里的定义。人类有黑眼睛和黑头发;魔鬼有红头发和绿眼睛。因此,外国人属于后者。这简单明了、无可争议,就像卡尔·冯·林奈依据植物的生殖器官将植物加以分类一样。”
尽管从中国人的世界观出发,洋人被“科学地”归在了具有红头发和绿眼睛的魔鬼类,但安特生依然认为:“在拥挤的大街上,当孩子们或者愤怒的暴民围追堵截一位外国人,怒斥其为‘洋鬼子’时,这就是骂人的话了。”
所以,安特生将这本书命名为“龙与洋鬼子”,是希望运用反讽的手段产生幽默的效果。在西方的文化中,“龙”所代表的是一种邪恶的力量,而中国的“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洋鬼子”既是安特生,也指一般的西方人。因此,书名的含义就是“中国与西方”。
在安特生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很少有那些所谓异国情调的猎奇式描述,或将中国人归为人种学意义上几种类型化的样式。尽管他在中国以“洋人”自称,但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人的一种友善。他在《龙与洋鬼子》中写道:“一般来说,中国男人瘦而结实,女人的肩膀强壮而宽大,孩子们长得胖乎乎的,他们的眼睛清澈、明亮。”
《龙与洋鬼子》除了学术考察外,记载了很多路上他遇到的有趣见闻。比如在北京发生的沙尘暴,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当代的现象,其实不然。在某年二月的一天,安特生乘车从北京到天津,便遭遇了一场不寻常的“沙尘暴”。他写道:“其中有来自戈壁沙漠的美丽而干净的黄白色沙尘,这些沙尘落在城市上空,人们可以用小院里的桶把它搜集起来,这些堆成小山的灰尘又被风刮到了田野中去。”
由于当时的植被状况不好,在北京附近,安特生所到之处,几乎没有树木。“这个国家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树木,但某些受保护的森林,例如北京东北偏东的东陵,似乎表明早期有一片相连的森林,已经被当地人砍伐,其中大部分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更糟糕的是,山里的人用可怜的树枝生火,而自从原始森林被砍伐以来,山里就没有树木了,每一棵树的枝条都被小小的砍柴人无情地砍掉。”由此可知,北京城市四周的植树造林,植被覆盖率的提高,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作为一个外来者,安特生常常会有些别样的观察。比如关于沙眼,他这样记录:“在中国,沙眼或许是最严重的眼科疾病。它的传播方式非常奇特。在一切公共场所,不管是旅馆、剧院还是列车上,服务人员通常会为客人分发热气腾腾的毛巾供其洁面,毛巾上还常会有淡香。用这些毛巾擦脸虽然清爽舒适,但极不健康。因为毛巾经不同顾客反复使用,虽会被投进一个大壶里消毒,但壶中的水多半是温水而不是开水,达不到消毒的效果。通过这些毛巾,沙眼寄生虫便输送到了健康的眼睛里。根据中国人对卫生和清洁的观念,饭后或晚间在剧院观影时,用毛巾擦脸洁面这种方法并无不妥。在剧院里,把用过的毛巾卷起来,直接扔给大厅对面的热水壶旁的人,对服务员来说是种广受青睐的小聪明手段。”今天读来,这样的描述也是颇具年代感了。
挑战时间的力量
由于安特生的考古发掘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加之他当时所接触的都是中国学界最优秀的学者,因此他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识是深刻的。
他懂得从农耕文明角度评价中国人。“对庄稼生长执着地关注,使得中国农民几乎一天到晚都得不到空闲,这无疑培养了中国人特有的防御性以及对和平本能的热爱。长城,从山海关的海边一直延伸到甘肃的沙漠深处,在精神上与中国人惊人的消极抵抗力相对应,这种品质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最强大的力量。”此外,他认为“对学习和艺术的热爱以及崇尚”,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另一个特点。
那么,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安特生认为“那就是敢于挑战时间的力量”。“人们怕时间,时间却怕金字塔”是埃及人的一句古老谚语。其含义是:拥有肉身的人们,害怕时间,是因为时间会带来死亡;时间害怕金字塔,是因为不论过去多少年,金字塔仍然矗立着。
在金字塔面前,时间似乎失去了它的力量;而中国文化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安特生称:“所有早期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克里特宫殿的统治者、埃及金字塔的建造者、楔形文字的先民——都早已逝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伟大的孤独之中坚持了下来,作为他们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作品、哲学和艺术的直接继承人。”
进而,他指出:“许多在东方的外国人说,中国人缺乏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使我们成为爆炸式的引擎,并以更加疯狂的速度加快了我们的文化在这里的发展。但是很少有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在精神上蕴藏着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宝藏:他们会种植牡丹、养金鱼,或者在树荫下打坐,而西方人在努力追求装饰,或者为了发现一个微小的‘科学真理’而奋斗不已。”
安特生相信中国的未来是不可估量的,他指出:“也许有一天,开启世界新征程的重任又落在了东方人身上。今天,我们应该从中国身上学习的东西就是,历经千年,中国仍保持着民族文化的活力。在青铜器时代,古代埃及、克里特岛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的文明就因遭到野蛮人的破坏而中断,但是,中国人,从开天辟地之日起,连续四千余年,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繁荣。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安特生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并且他认为,中国的未来一定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而是东西文明的融合。今天读来,作为中国人,更应该有这样一种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