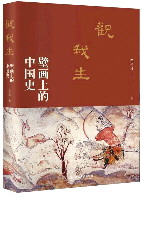古墓里的图像“元宇宙”
齐鲁晚报 2023年02月25日
□伯镇
“图像史”是史学界的研究热门领域。苗子兮的《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一书,以从汉代至宋朝有代表性的十四个墓葬美术个案为切入点,来解读图像背后的生动历史。这是一部由线条和色彩绘就的历史,皇亲国戚、豪门贵妇、边地小吏、异域来客、农夫牧人,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这部历史的主人公。从昆仑仙境到人间乐国,从春播秋收到南来北往,从觥筹交错的盛宴到车马喧闹的出行,墓室主人的日常生活、生平功业、希冀情感被表现在画壁上,时代的风尚、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风云被折射在画面上。每幅画,是一扇小小的窗口,透过它,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生命故事,还有大时代的起承转合。
看见“清平乐”
1999年,在河南登封黑山沟,一座古墓被发掘出来。根据从墓中出土的买地契可知,墓主人名叫李守贵,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葬。墓室壁画里的墓主人画像显示,他是一位面多皱纹的老者,当过耳顺之年。据此可以推断,李守贵应当生于仁宗朝,并经历了神宗朝的跌宕起伏,在哲宗朝寿终正寝。
李守贵墓室中绘有三层壁画,下层壁画位于柱间,共有六幅。西侧的三幅壁画仿佛呈现的是主人家中的一场欢宴。西北壁上绘出了幔帐和组绶,帐下,立有两座屏风,标示出厅堂的主要位置,李守贵及其夫人就分坐在屏风之前的高足椅上,共对一张方桌。李守贵头戴无脚幞头,着圆领袍,腰系黑带,面上的皱纹显示他已颇有年纪。夫人则头梳高髻,裹额帕,身着褙子,两襟间露出红色抹胸,下束百褶裙。
夫妇面前的方桌上,置放着两只带托茶盏,而屏风之间有一女子,手托一带温碗的注壶,似乎要为夫妇的茶盏注水。西南侧壁画里亦绘有一屏风和方桌,二女子正在备茶。方桌上有盘,盘中置两只托盏,另有果盘若干,叠放的盏托若干。一女子手持茶末罐,此罐与北宋磁州窑瓷器特征相似。
这些画面具有浓重的写实风格,刻画了李守贵生前的富贵安逸生活。夫妇共坐,饮茶品酒,女伎作乐,这是宋代墓葬壁画最常见的主题。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认为,此类场景是表示夫妻恩爱的“开芳宴”。
苗子兮结合历史背景推测,在李守贵的回忆里,仁宗朝可能是一段久远的美好时光。此时,皇帝垂拱而治,天下太平。西夏的战事遥远得仿佛传说,且不久边境就恢复了平静。庆历三年(1043年)的新政也很快偃旗息鼓,并未带来太大变故。总之,平安无事。那时李守贵还年轻,但已经在父亲的指点下,打理自家的田地和资产,并小有所成。当然,烦恼也是有的,比如作为上户,李家也得轮流承担衙前的差役,如果遇上运输官物这样的差事,且不幸官物失窃的话,就不得不赔偿,有时候,甚至会倾家荡产。不过,李家运气不错,这样的倒霉事应该没碰上过。
李守贵经历了整个神宗朝,当时的王安石变法利刃主要就是砍向李家这样的富户,而其所在的河南府又是新法严苛之地,李守贵那段时光想必不太好过。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一度废除新法,但哲宗亲政,又恢复了新法。合理的想象是,李守贵从继承下田庄和家产起,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都需要与新法周旋。但从李守贵墓的规格来看,老李家守住了自己的财富。
是偶然还是必然?还真不好说。“在新法的惊涛骇浪中,一些精明的富民还是能驾驭自己的财富之舟冲出暴风雨,不管他们使用了什么卑劣的手段。至于那些舟覆人亡者,他们没有姓名,甚至也组不成数字,只是大时代中搅动风云者掸下的尘埃。”《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可惜花无百日红。在李守贵下葬28年后,从白山黑水间崛起的女真人灭掉了辽国,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兵南下。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两京陷落,金兵铁蹄肆虐于中原。史载:“初,敌纵兵四掠,东至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陕、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荼毒之后,大批民众被掳,郡县为之一空。时代洪流下,李守贵的子孙们,再也没有了先辈享受过的太平日子。
如梦幻泡影
“观我生”之名源自《周易·观》,北朝颜之推也有《观我生赋》,不过,书中苗子兮用的是其字面意思:“观看我的一生。”她用纪传体的方式,还原了包括李守贵在内的14种人生。这些墓主人身份各异,有皇亲国戚、豪门贵妇、边地小吏、异域来客、农夫牧人,通过他们的生平故事,可以读到上千年历史背后的沉浮:士族高门被打压后走向没落,科举为寒门士子打开上升通道,安史之乱后唐朝在西域失势,中国开始转为内向……
有时候,一图胜千言。图像,是比文字更古老的记录形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六七万年前的莽荒时代。从被绘制的那一刻起,图像就被赋予了象天法地、状物拟人的作用,是它,最早叙述了先民们眼中的大千世界。
在古人的脑海里,世界并不限于当下,或此生。当灵魂抛下形骸,离开此岸后,将奔向一个更辽阔且更恒久的世界,这是先民们的广泛共识。于是,安放形骸的墓葬既是此岸生命的终点,也成为了新的航程的起点。所以,先民们在墓葬中绘制的图像,也往往具有双重的意义。它是对此生的回顾,亦是对来世的展望,现实与幻想、凡间与仙境于其间交融在一起。
先秦时期,墓葬多为竖穴式,空间狭窄,所以图像大多直接绘于棺椁上,篇幅有限。自汉代开始,砖石室墓流行,宽阔平整的壁面为图像提供了良好载体,壁上之画或彩绘、或雕刻、或模印,皆可统称为“壁画”。
汉代人有厚葬之风,所以绘图于壁、画像于石蔚然成风,墓葬壁画迎来第一个高峰。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盗墓猖獗,所以丧事崇尚简薄,墓葬壁画少了许多。北朝直至唐五代时期,厚葬之风再起,墓葬壁画特受重视,甚至丹青名家也经常为冥宅绘画,墓葬壁画迎来第二个高峰。到了宋代,士大夫提倡薄葬,然而民间富户很多,他们为了装饰冥宅不惜豪掷千金,墓葬壁画持续流行。到了金、元时期,墓葬壁画绘制粗鄙,不复前朝风流,进入明清时期则彻底衰败。由此算来,墓葬壁画的繁盛期,自汉至宋辽长达一千余年。
在跟随《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一书阅读墓主人的过往中,读者很容易感受到个体在历史沉浮中的无力。正如苗子兮所感慨的那样,“乱世中,一切荣华富贵都是梦幻泡影”,“培植一棵大树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摧毁它只在顷刻之间”。
七贤成“七仙”
当然,以图叙史并非简单地相信图像告诉我们的一切。
1960年,在江苏南京西善桥宫山,一座南朝大墓被开启,在砖砌墓壁上,人们惊讶地发现,风流千载的竹林七贤赫然在目。
而宫山墓并非特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考古学家陆续在江苏丹阳胡桥仙塘湾南朝墓、丹阳建山金家村南朝墓、丹阳胡桥吴家村南朝墓、南京雨花台石子岗南朝墓、南京雨花台铁心桥小村1号南朝墓、南京栖霞狮子冲1号南朝墓中也见到了类似的竹林七贤砖印图像。这几座墓葬等级甚高,甚至其中不乏帝陵,如仙塘湾墓被认为是齐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吴家村墓可能是齐和帝萧宝融的恭安陵。
至于为何墓葬中会出现竹林七贤像,学者们大致有两派观点:一派以此竹林七贤像为名士图,绘之乃是因墓主人崇尚玄学,或出于帝王笼络士族之需;另一派以此竹林七贤像为神仙图,绘之乃是对升仙的渴望。
《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更认同后者。“从车马出行到仙人戏龙虎,这似乎已经构建了一条从地面到虚空的升仙路径,这让人不得不思考竹林七贤在此场景中对主人升仙的意义。首先,竹林七贤图像和仙人戏龙虎同处上栏,这意味着在创作者心目中,七贤已经超拔于尘俗之上,但七贤与树相伴,而非飞云,似乎又暗示着他们所处并非天境,也许是林木蓊郁的山中。那么,七贤的居处很可能是升仙路上的一个中间环节,即主人的魂灵从尘世出发,经七贤等高士所居处,再由仙人引导,乘龙虎飞入仙界。”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高士们是道术极为高深的人,他们是通往仙界的媒介,甚至本身就是神仙。然而,这显然只是人们的朴素愿望而已。
可见,墓葬壁画作为一种形式化的记录体裁,它同时具有写实和虚构的特质,而这种虚构,不仅是溢美夸大,它还受到当时已形成的图像程式的巨大影响。“因此,在行文中,我不得不谨慎控制着壁画可以扮演的角色,有时候,它们作为主角登场,直接告诉我们过去发生的种种,有时候,它们不过是配角,提示着墓主人跌宕生命历程背后的时代风貌。当然,对一部宏大戏剧而言,这两种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苗子兮指出。
墓葬图像也好,美术考古也罢,其本质都是一种可供阅读的历史与图像素材,其关键在于深入发掘墓葬艺术背后的逻辑和观念。苗子兮受过历史学的学术训练,文献功底扎实,学术观点保持了相当的前沿性。可贵的是,她以一种细腻的女性视角,采用散文化的叙事和优美的语言,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图像志描述化作涓涓细流,并最终汇入中国历史的大海。
此外,由《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可以看出,艺术史、历史与文学并非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可以被一个有趣的灵魂融会贯通,进而构建一个知识与经验、理性与感性、真实与想象相结合的墓葬图像“元宇宙”。这无疑是一份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却又迷人的文化财富。
“图像史”是史学界的研究热门领域。苗子兮的《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一书,以从汉代至宋朝有代表性的十四个墓葬美术个案为切入点,来解读图像背后的生动历史。这是一部由线条和色彩绘就的历史,皇亲国戚、豪门贵妇、边地小吏、异域来客、农夫牧人,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这部历史的主人公。从昆仑仙境到人间乐国,从春播秋收到南来北往,从觥筹交错的盛宴到车马喧闹的出行,墓室主人的日常生活、生平功业、希冀情感被表现在画壁上,时代的风尚、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风云被折射在画面上。每幅画,是一扇小小的窗口,透过它,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生命故事,还有大时代的起承转合。
看见“清平乐”
1999年,在河南登封黑山沟,一座古墓被发掘出来。根据从墓中出土的买地契可知,墓主人名叫李守贵,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葬。墓室壁画里的墓主人画像显示,他是一位面多皱纹的老者,当过耳顺之年。据此可以推断,李守贵应当生于仁宗朝,并经历了神宗朝的跌宕起伏,在哲宗朝寿终正寝。
李守贵墓室中绘有三层壁画,下层壁画位于柱间,共有六幅。西侧的三幅壁画仿佛呈现的是主人家中的一场欢宴。西北壁上绘出了幔帐和组绶,帐下,立有两座屏风,标示出厅堂的主要位置,李守贵及其夫人就分坐在屏风之前的高足椅上,共对一张方桌。李守贵头戴无脚幞头,着圆领袍,腰系黑带,面上的皱纹显示他已颇有年纪。夫人则头梳高髻,裹额帕,身着褙子,两襟间露出红色抹胸,下束百褶裙。
夫妇面前的方桌上,置放着两只带托茶盏,而屏风之间有一女子,手托一带温碗的注壶,似乎要为夫妇的茶盏注水。西南侧壁画里亦绘有一屏风和方桌,二女子正在备茶。方桌上有盘,盘中置两只托盏,另有果盘若干,叠放的盏托若干。一女子手持茶末罐,此罐与北宋磁州窑瓷器特征相似。
这些画面具有浓重的写实风格,刻画了李守贵生前的富贵安逸生活。夫妇共坐,饮茶品酒,女伎作乐,这是宋代墓葬壁画最常见的主题。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认为,此类场景是表示夫妻恩爱的“开芳宴”。
苗子兮结合历史背景推测,在李守贵的回忆里,仁宗朝可能是一段久远的美好时光。此时,皇帝垂拱而治,天下太平。西夏的战事遥远得仿佛传说,且不久边境就恢复了平静。庆历三年(1043年)的新政也很快偃旗息鼓,并未带来太大变故。总之,平安无事。那时李守贵还年轻,但已经在父亲的指点下,打理自家的田地和资产,并小有所成。当然,烦恼也是有的,比如作为上户,李家也得轮流承担衙前的差役,如果遇上运输官物这样的差事,且不幸官物失窃的话,就不得不赔偿,有时候,甚至会倾家荡产。不过,李家运气不错,这样的倒霉事应该没碰上过。
李守贵经历了整个神宗朝,当时的王安石变法利刃主要就是砍向李家这样的富户,而其所在的河南府又是新法严苛之地,李守贵那段时光想必不太好过。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一度废除新法,但哲宗亲政,又恢复了新法。合理的想象是,李守贵从继承下田庄和家产起,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都需要与新法周旋。但从李守贵墓的规格来看,老李家守住了自己的财富。
是偶然还是必然?还真不好说。“在新法的惊涛骇浪中,一些精明的富民还是能驾驭自己的财富之舟冲出暴风雨,不管他们使用了什么卑劣的手段。至于那些舟覆人亡者,他们没有姓名,甚至也组不成数字,只是大时代中搅动风云者掸下的尘埃。”《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可惜花无百日红。在李守贵下葬28年后,从白山黑水间崛起的女真人灭掉了辽国,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兵南下。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两京陷落,金兵铁蹄肆虐于中原。史载:“初,敌纵兵四掠,东至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陕、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荼毒之后,大批民众被掳,郡县为之一空。时代洪流下,李守贵的子孙们,再也没有了先辈享受过的太平日子。
如梦幻泡影
“观我生”之名源自《周易·观》,北朝颜之推也有《观我生赋》,不过,书中苗子兮用的是其字面意思:“观看我的一生。”她用纪传体的方式,还原了包括李守贵在内的14种人生。这些墓主人身份各异,有皇亲国戚、豪门贵妇、边地小吏、异域来客、农夫牧人,通过他们的生平故事,可以读到上千年历史背后的沉浮:士族高门被打压后走向没落,科举为寒门士子打开上升通道,安史之乱后唐朝在西域失势,中国开始转为内向……
有时候,一图胜千言。图像,是比文字更古老的记录形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六七万年前的莽荒时代。从被绘制的那一刻起,图像就被赋予了象天法地、状物拟人的作用,是它,最早叙述了先民们眼中的大千世界。
在古人的脑海里,世界并不限于当下,或此生。当灵魂抛下形骸,离开此岸后,将奔向一个更辽阔且更恒久的世界,这是先民们的广泛共识。于是,安放形骸的墓葬既是此岸生命的终点,也成为了新的航程的起点。所以,先民们在墓葬中绘制的图像,也往往具有双重的意义。它是对此生的回顾,亦是对来世的展望,现实与幻想、凡间与仙境于其间交融在一起。
先秦时期,墓葬多为竖穴式,空间狭窄,所以图像大多直接绘于棺椁上,篇幅有限。自汉代开始,砖石室墓流行,宽阔平整的壁面为图像提供了良好载体,壁上之画或彩绘、或雕刻、或模印,皆可统称为“壁画”。
汉代人有厚葬之风,所以绘图于壁、画像于石蔚然成风,墓葬壁画迎来第一个高峰。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盗墓猖獗,所以丧事崇尚简薄,墓葬壁画少了许多。北朝直至唐五代时期,厚葬之风再起,墓葬壁画特受重视,甚至丹青名家也经常为冥宅绘画,墓葬壁画迎来第二个高峰。到了宋代,士大夫提倡薄葬,然而民间富户很多,他们为了装饰冥宅不惜豪掷千金,墓葬壁画持续流行。到了金、元时期,墓葬壁画绘制粗鄙,不复前朝风流,进入明清时期则彻底衰败。由此算来,墓葬壁画的繁盛期,自汉至宋辽长达一千余年。
在跟随《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一书阅读墓主人的过往中,读者很容易感受到个体在历史沉浮中的无力。正如苗子兮所感慨的那样,“乱世中,一切荣华富贵都是梦幻泡影”,“培植一棵大树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摧毁它只在顷刻之间”。
七贤成“七仙”
当然,以图叙史并非简单地相信图像告诉我们的一切。
1960年,在江苏南京西善桥宫山,一座南朝大墓被开启,在砖砌墓壁上,人们惊讶地发现,风流千载的竹林七贤赫然在目。
而宫山墓并非特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考古学家陆续在江苏丹阳胡桥仙塘湾南朝墓、丹阳建山金家村南朝墓、丹阳胡桥吴家村南朝墓、南京雨花台石子岗南朝墓、南京雨花台铁心桥小村1号南朝墓、南京栖霞狮子冲1号南朝墓中也见到了类似的竹林七贤砖印图像。这几座墓葬等级甚高,甚至其中不乏帝陵,如仙塘湾墓被认为是齐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吴家村墓可能是齐和帝萧宝融的恭安陵。
至于为何墓葬中会出现竹林七贤像,学者们大致有两派观点:一派以此竹林七贤像为名士图,绘之乃是因墓主人崇尚玄学,或出于帝王笼络士族之需;另一派以此竹林七贤像为神仙图,绘之乃是对升仙的渴望。
《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更认同后者。“从车马出行到仙人戏龙虎,这似乎已经构建了一条从地面到虚空的升仙路径,这让人不得不思考竹林七贤在此场景中对主人升仙的意义。首先,竹林七贤图像和仙人戏龙虎同处上栏,这意味着在创作者心目中,七贤已经超拔于尘俗之上,但七贤与树相伴,而非飞云,似乎又暗示着他们所处并非天境,也许是林木蓊郁的山中。那么,七贤的居处很可能是升仙路上的一个中间环节,即主人的魂灵从尘世出发,经七贤等高士所居处,再由仙人引导,乘龙虎飞入仙界。”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高士们是道术极为高深的人,他们是通往仙界的媒介,甚至本身就是神仙。然而,这显然只是人们的朴素愿望而已。
可见,墓葬壁画作为一种形式化的记录体裁,它同时具有写实和虚构的特质,而这种虚构,不仅是溢美夸大,它还受到当时已形成的图像程式的巨大影响。“因此,在行文中,我不得不谨慎控制着壁画可以扮演的角色,有时候,它们作为主角登场,直接告诉我们过去发生的种种,有时候,它们不过是配角,提示着墓主人跌宕生命历程背后的时代风貌。当然,对一部宏大戏剧而言,这两种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苗子兮指出。
墓葬图像也好,美术考古也罢,其本质都是一种可供阅读的历史与图像素材,其关键在于深入发掘墓葬艺术背后的逻辑和观念。苗子兮受过历史学的学术训练,文献功底扎实,学术观点保持了相当的前沿性。可贵的是,她以一种细腻的女性视角,采用散文化的叙事和优美的语言,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图像志描述化作涓涓细流,并最终汇入中国历史的大海。
此外,由《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可以看出,艺术史、历史与文学并非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可以被一个有趣的灵魂融会贯通,进而构建一个知识与经验、理性与感性、真实与想象相结合的墓葬图像“元宇宙”。这无疑是一份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却又迷人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