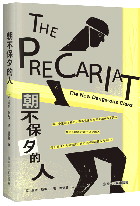被吞噬的休闲时间
□盖伊·斯坦丁
齐鲁晚报 2023年05月06日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推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一些国家的政府强调通过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将风险转嫁给劳动者,让企业得以提高效率、适应国际竞争。在这股浪潮中,传统工人阶级在20世纪60年代争取而来的稳定就业和社会福利被不断侵蚀,劳动者的工时、薪资、工作地点甚至工作内容都可以被轻易变更。英国著名劳动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在著作《朝不保夕的人》中指出,作为福利的休闲时间一步步被挤压,人们不再敬畏休闲,也不再尊重具有再生产能力和创造性的“无所事事”。
不平等的时间支配能力
劳动、“为获得工资的劳动”、“为社会再生产而做的工作”日渐繁重,也吞噬了我们的“休闲”时间。商品化市场社会最糟糕的结果之一是,人们不再敬畏休闲,不再尊重具有再生产能力和创造性的“无所事事”。
承担高强度工作和劳动的人发现自己的大脑和身体都被透支,下班后几乎没有精力再做其他事情,连思考都变得费劲,只能沉浸在被动的“玩乐”中。人们只是呆呆地看着屏幕,或是隔着屏幕和人聊天,这就是他们的放松方式。
当然,我们都需要某些形式的“玩乐”,但如果劳动和工作过于繁重,我们可能就会丧失精力和想法,无法参加更加积极的休闲活动。
2009年,据马克·阿吉亚尔和埃里克·赫斯特估计,尽管当代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但她们每周的休闲时间比1965年还是增加了4小时,男性则增加了6小时。
然而休闲时间不等同于有偿劳动之外的所有时间。尽管其他社会群体也面临压力,但朝不保夕者哪怕只是为了最起码的生存,都要从事大量“为获得工资的劳动”和其他工作,才能安身立命。
过去,人们想放松自己,会参加高品质的文化和艺术活动。比如,欣赏优美的音乐、戏剧、美术作品和伟大的文学名著,了解我们自身或所在社群的历史,这些活动都需要用“黄金时间”来实现,意思是不被打扰,不会感到心神不宁或紧张,也没有劳动或工作的羁绊而因此失眠的时间。如果失去了休闲时间,人们就更不会有黄金时间。
休闲时间被挤压的另一个方面是不同的人支配时间的能力极为不平等。朝不保夕者必须听候调遣,随时准备被潜在雇主征用他们的劳动力。那些泡网吧的人,在家中、酒吧或是街角游荡的人,看似“有的是可以随意支配的时间”。然而,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无法制订或维持如何以其他方式分配时间的策略。他们看不清一个明确的未来,因此,他们一旦离开工作岗位,时间就被虚掷了。
这种时间使用方式,实则是弹性劳动力市场的特质之一。只要市场希望朝不保夕者一直处于“待命”状态,他们就被剥夺了规划时间的权利。
不稳定劳动陷阱
贬低休闲活动,尤其是工人阶级休闲活动的价值,是劳工主义最糟糕的遗产。传承价值的教育活动越来越少,导致年轻人逐渐脱离他们身边的文化,丧失对他们所在社群的社会记忆。
“街角社会”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遍布都市的意象。人们不知该如何运用时间,“闲逛”成了大家主要的时间使用方式。有人称这种困局为“休闲的匮乏”。物质上的匮乏限制了年轻朝不保夕者的休闲活动,他们囊中羞涩,也没有职业社群,更无法在稳定性的庇护下好好地支配自己的时间。
这就助长了他们对包括工作和劳动在内的所有活动的厌恶态度。这是一个“不稳定劳动陷阱”。仅仅为了基本生存,人类就需要足够的公共空间,但紧缩政策却连这类公共空间也要侵蚀。毕竟,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些东西就是“奢侈品”,因为它们对增加产出或促进经济增长没有直接贡献。只有当朝不保夕者威胁到了社会稳定,这种评估事物价值的做法才会引发人们的反思。
在英国,包括工人俱乐部和公共场所在内的休闲事业都成了撒切尔治下激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牺牲品。法国的小酒馆也一样,它们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人民的议会”,如今却大都关张。
“惯习”能反映出某人的阶级属性,某人的活动区域、生活方式决定了他“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朝不保夕者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匹配,同样短暂、弹性、投机,很少有人能够构建出稳定的道路。
人们可能会因为恐惧和焦虑营造出的不安全感,而缩进一个更逼仄的空间,这一缩,生活就很难再走上正轨了。在一个充满弹性和不安全感的社会中,人们更容易虚掷光阴,而不是利用时间自我精进,为今后的发展做好准备。
所有时间都是工作时间
再回头思考工作场所这一概念的瓦解所造成的影响,它中断了朝不保夕者的生活机会,让生活中的任何角落都成为他们的工作场所;任何时间,甚至几乎所有时间,都变成工作时间。就算不在工作场所工作或劳动,他们也无法拥有自主权,到头来可能还是提线木偶。而且,统计数据也会骗人,“工作时间”并不等同于“实际的工作时间”。
模糊两者间的区别会让人认为自己正在进行“自由劳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像雇主有办法让劳动者从事无偿的“为获得工资的劳动”,他们也可以将工作和劳动任务挪到正式工作场所之外。这是权力关系造成的。
某些劳动无法让人获得工资,人们却不能自主决定是否要做。这种劳动是免费的,却是不自由的。哈特和奈格里在一项影响深远的分析中指出:服务性劳动是免费的、“非物质的”、“无法测量的”。
但事实上,这类劳动可以被量化,而且量化的标准还会被那些参与劳动关系协商人士的议价能力影响。因为生活缺乏安全感,弹性劳动文化盛行,朝不保夕者目前处于弱势地位,让雇主拿走“为获得工资的劳动”带来的大部分收益。
多线程工作、无法系统而富有意义地控制时间,也无法沟通过去和未来,只能苟活于当下。当一个人陷入朝不保夕化的生活状态中,他就和工作绑定,无法思考职业发展。
我们面对眼前的各种信号,注意力四处移动,无法集中。多线程工作降低了每件任务的生产率,碎片化的思考方式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让我们更难以从事创造性工作,更难以全身心投入需要专心致志、深思熟虑和持之以恒的休闲活动。
休闲被排挤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靠被动玩乐放松心神。下班后不停地在网络上连线互动,是朝不保夕者的“精神鸦片”,正如啤酒和杜松子酒是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的饮品一样。
如今的工作场所无处不在,它们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个角落,却又让人无法辨识,无法提供安全感。即便朝不保夕者确有一技之长,这些技能也有可能消失,不再能帮助他们获得一种稳定的身份,也无法帮助他们维持有尊严的生活。
这种不健康的环境,很容易让人变得机会主义和玩世不恭,让社会变成彩票中心,由运气决定一切,而朝不保夕者承担了极高比例的失败风险。
(本文摘选自《朝不保夕的人》,原文有删节,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不平等的时间支配能力
劳动、“为获得工资的劳动”、“为社会再生产而做的工作”日渐繁重,也吞噬了我们的“休闲”时间。商品化市场社会最糟糕的结果之一是,人们不再敬畏休闲,不再尊重具有再生产能力和创造性的“无所事事”。
承担高强度工作和劳动的人发现自己的大脑和身体都被透支,下班后几乎没有精力再做其他事情,连思考都变得费劲,只能沉浸在被动的“玩乐”中。人们只是呆呆地看着屏幕,或是隔着屏幕和人聊天,这就是他们的放松方式。
当然,我们都需要某些形式的“玩乐”,但如果劳动和工作过于繁重,我们可能就会丧失精力和想法,无法参加更加积极的休闲活动。
2009年,据马克·阿吉亚尔和埃里克·赫斯特估计,尽管当代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但她们每周的休闲时间比1965年还是增加了4小时,男性则增加了6小时。
然而休闲时间不等同于有偿劳动之外的所有时间。尽管其他社会群体也面临压力,但朝不保夕者哪怕只是为了最起码的生存,都要从事大量“为获得工资的劳动”和其他工作,才能安身立命。
过去,人们想放松自己,会参加高品质的文化和艺术活动。比如,欣赏优美的音乐、戏剧、美术作品和伟大的文学名著,了解我们自身或所在社群的历史,这些活动都需要用“黄金时间”来实现,意思是不被打扰,不会感到心神不宁或紧张,也没有劳动或工作的羁绊而因此失眠的时间。如果失去了休闲时间,人们就更不会有黄金时间。
休闲时间被挤压的另一个方面是不同的人支配时间的能力极为不平等。朝不保夕者必须听候调遣,随时准备被潜在雇主征用他们的劳动力。那些泡网吧的人,在家中、酒吧或是街角游荡的人,看似“有的是可以随意支配的时间”。然而,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无法制订或维持如何以其他方式分配时间的策略。他们看不清一个明确的未来,因此,他们一旦离开工作岗位,时间就被虚掷了。
这种时间使用方式,实则是弹性劳动力市场的特质之一。只要市场希望朝不保夕者一直处于“待命”状态,他们就被剥夺了规划时间的权利。
不稳定劳动陷阱
贬低休闲活动,尤其是工人阶级休闲活动的价值,是劳工主义最糟糕的遗产。传承价值的教育活动越来越少,导致年轻人逐渐脱离他们身边的文化,丧失对他们所在社群的社会记忆。
“街角社会”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遍布都市的意象。人们不知该如何运用时间,“闲逛”成了大家主要的时间使用方式。有人称这种困局为“休闲的匮乏”。物质上的匮乏限制了年轻朝不保夕者的休闲活动,他们囊中羞涩,也没有职业社群,更无法在稳定性的庇护下好好地支配自己的时间。
这就助长了他们对包括工作和劳动在内的所有活动的厌恶态度。这是一个“不稳定劳动陷阱”。仅仅为了基本生存,人类就需要足够的公共空间,但紧缩政策却连这类公共空间也要侵蚀。毕竟,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些东西就是“奢侈品”,因为它们对增加产出或促进经济增长没有直接贡献。只有当朝不保夕者威胁到了社会稳定,这种评估事物价值的做法才会引发人们的反思。
在英国,包括工人俱乐部和公共场所在内的休闲事业都成了撒切尔治下激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牺牲品。法国的小酒馆也一样,它们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人民的议会”,如今却大都关张。
“惯习”能反映出某人的阶级属性,某人的活动区域、生活方式决定了他“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朝不保夕者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匹配,同样短暂、弹性、投机,很少有人能够构建出稳定的道路。
人们可能会因为恐惧和焦虑营造出的不安全感,而缩进一个更逼仄的空间,这一缩,生活就很难再走上正轨了。在一个充满弹性和不安全感的社会中,人们更容易虚掷光阴,而不是利用时间自我精进,为今后的发展做好准备。
所有时间都是工作时间
再回头思考工作场所这一概念的瓦解所造成的影响,它中断了朝不保夕者的生活机会,让生活中的任何角落都成为他们的工作场所;任何时间,甚至几乎所有时间,都变成工作时间。就算不在工作场所工作或劳动,他们也无法拥有自主权,到头来可能还是提线木偶。而且,统计数据也会骗人,“工作时间”并不等同于“实际的工作时间”。
模糊两者间的区别会让人认为自己正在进行“自由劳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像雇主有办法让劳动者从事无偿的“为获得工资的劳动”,他们也可以将工作和劳动任务挪到正式工作场所之外。这是权力关系造成的。
某些劳动无法让人获得工资,人们却不能自主决定是否要做。这种劳动是免费的,却是不自由的。哈特和奈格里在一项影响深远的分析中指出:服务性劳动是免费的、“非物质的”、“无法测量的”。
但事实上,这类劳动可以被量化,而且量化的标准还会被那些参与劳动关系协商人士的议价能力影响。因为生活缺乏安全感,弹性劳动文化盛行,朝不保夕者目前处于弱势地位,让雇主拿走“为获得工资的劳动”带来的大部分收益。
多线程工作、无法系统而富有意义地控制时间,也无法沟通过去和未来,只能苟活于当下。当一个人陷入朝不保夕化的生活状态中,他就和工作绑定,无法思考职业发展。
我们面对眼前的各种信号,注意力四处移动,无法集中。多线程工作降低了每件任务的生产率,碎片化的思考方式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让我们更难以从事创造性工作,更难以全身心投入需要专心致志、深思熟虑和持之以恒的休闲活动。
休闲被排挤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靠被动玩乐放松心神。下班后不停地在网络上连线互动,是朝不保夕者的“精神鸦片”,正如啤酒和杜松子酒是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的饮品一样。
如今的工作场所无处不在,它们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个角落,却又让人无法辨识,无法提供安全感。即便朝不保夕者确有一技之长,这些技能也有可能消失,不再能帮助他们获得一种稳定的身份,也无法帮助他们维持有尊严的生活。
这种不健康的环境,很容易让人变得机会主义和玩世不恭,让社会变成彩票中心,由运气决定一切,而朝不保夕者承担了极高比例的失败风险。
(本文摘选自《朝不保夕的人》,原文有删节,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