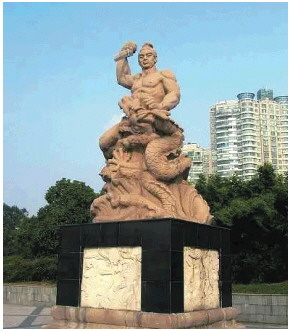生前除三害 死后留谜团
周处墓中的铝片究竟是哪来的
齐鲁晚报 2024年03月16日
电影《周处除三害》的热映让周处这个西晋时期的历史人物进入公众视野。周处,因“除三害”的传说而在中国家喻户晓,成为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范。但一般人恐怕还不知道他的墓在70多年前即被发现。而更为离奇的,是这墓中出土的小小铝片有“穿越”之嫌。从轰动到探询质疑,从讨论一度归于沉寂到近年的旧事重提,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悬案,至今仍扑朔迷离。
□许宏
周处墓的发现与发掘
1952年12月,江苏宜兴精一中学师生在挑土平整操场上的一处小土丘时,掘破了一座砖室墓的墓顶。公安人员进入墓室取出若干遗物后,将墓室封好,之后文物管理部门进行初步调查。1953年春,华东文物工作队派员对发现的两座墓葬做了发掘。
当地人称这处小土丘为周墓墩,相传为周处的墓地。土丘一角有“周王庙”,奉祀周处。经发掘,被掘开的墓葬(编为1号墓)中发现刻有文字的青砖,上书“元康七年九月廿日前周将军”等字样。清代《宜兴县志》记载周处葬于此,而周处正是西晋元康七年(297年)战死的,所以此墓为周处墓无疑。此前一些古代名人葬地位置,相关的记载和民间传说多以讹传讹,考古发现证实记载的例子并不多见,周处墓的发现算是考古界的一个佳话。
周处家族墓地是一处南北向隆起的坟丘,占地5.7万平方米。1953年和1976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其中的6座墓,6座墓南北排成一列,根据诸墓位置、结构形制及墓砖文字,可确定1号墓为周处墓,2号墓为周处子周札墓,3号墓亦为周处子周靖墓,4号墓为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周处父周鲂墓,5号墓为周处子周玘墓,6号墓为周鲂父周宾墓。周氏是三国东吴至西晋时期江南著名的大门阀士族,自周处的祖父周宾始著,经周鲂、周处至周玘、周札,“一门五侯”,“四世显著”。
周处墓虽早年被盗掘,还是出土了不少遗物,其中十余件带有镂孔花纹的金属带饰尤引人注目。更令人称奇的是,与其同出的某些金属残片经检测竟是铝质的,这大大超出了当时的认知。
检测生出的疑问
当时负责周处墓清理发掘和报告编写工作的是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先生。
1955年,罗宗真在考古报告整理的过程中,把从该墓出土的一件金属残片交南京大学化学系做了成分分析,得知内层为含铝约85%的铝铜合金。罗宗真在考古报告中写道:“像这样含有大量铝的合金,在我们工作中还是初次发现,为我们研究晋代冶金术提出了新的资料。”当这一考古报告的原稿投寄到中国考古学的权威杂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学报》时,时任该所所长、《考古学报》主编的夏鼐先生感觉兹事体大。作为民国时代的“海归”、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夏鼐知道,铝是一种难于冶炼的金属,到了19世纪才被冶炼出来,他在审核原稿校样时,怀疑这个“铝”字是否为“铅”字之误。他意识到问题的重大:“实际上,这不仅是我们考古工作中初次发现,也是全世界初次听说有这样古老的以铝为主要成分的合金。”慎重起见,夏鼐专门去函询问,索取样品,遂委托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陆学善先生做了光谱分析,确认残片内层的主要成分为铝。这一分析成果被夏鼐安排附在周处墓发掘报告的最后,连同他自己的“跋语”一同刊发于1957年第4期《考古学报》上。夏鼐在跋语的第一条即提及这一鉴定结果,指出“这是化学史和冶金史中的新发现”,接着提出他的疑问:“我们要问在当时是用什么方法提炼出这不易炼冶的金属达到85%的纯度?”
的确,铝在地球上虽含量丰富、分布甚广,但很难熔炼。即便对缺乏专业知识的公众而言,不少人也知道铝是最年轻的金属,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不敢想象金属铝的出现能够早到一千多年前的西晋时期。学术界对这一发现更是重视有加。
随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杨根先生又从夏鼐手中取得一小块残片,经光谱定性分析知其含大量的铝及其他微量元素,金相鉴定为多种合金组织。1959年春,南京博物院又送了几件残片给杨根。经检测,其中一片的主要成分为铝,另两片的主要成分为银。杨根结合汉晋时期鼓风技术的改进和炼丹术、制钢术的兴盛,认为在晋代出现这一杰出成就是有可能的:“这是世界化学史和冶金史上的一次创获,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成就。”
几次检测证明,这批金属器包含两种合金,一种为银基,一种为铝基。夏鼐后来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所分析的样品都是小块碎片,但全部17件较为完整的金属带饰都没有经过分析以确定其质料。由于出土文物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一般不做有损分析,不得已的情况下也是给些细小的碎片等。罗宗真提及“当时我们希望尽量可能地保存原物的完整,总是捡最小、最残的块片送去分析,并没有损坏原件”。显然,标本的局限性也增大了问题的复杂性。
铝从哪里来?
上述出土品的检测结果和论述还仅限于国内的学术刊物,对外展出后,引起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关注。1959年10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公开预展,由古代冶金陈列小组推荐,展出了周处墓所出全部带饰。南京博物院也曾展出过该墓出土的带饰,展品标签上都明确标示这些带饰系铝制品。这一定性,迅速在国际学术界和公众中引起了轰动。
截至1963年,国内发表的相关科普文章至少6篇,这些文章大多依从杨根的论断,肯定西晋时期已掌握了炼铝技术。
1962年,沈时英发表《关于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带饰成分问题》一文,在公布其对银质和铝质残片检测结果的基础上,做了较细致的讨论。他指出,在我国晋代产生银基合金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我国早在公元前就已经能够炼出金属银了。但其中测过多次的一片是含杂质较多的纯铝,“还难以证明它确为古代金属”。鉴于国内外火法炼铝的各种试验都未能获得高铝合金,更难以得到纯铝,用钠来还原氧化铝或其他铝盐的设想也很难成立。他强调指出:“关于晋代是否有铝带饰(纯铝的)问题,还应该作深入研究,下肯定性结论,似嫌为时过早”。
重新鉴定与夏鼐的再发言
如前所述,周处墓中出土的17件较完整而成形的金属带饰并未经过科学检测。显然,这些金属带饰究竟是否如先前所判定和展示的为铝质器件,必须予以鉴定。为此,夏鼐于1964年协调将南京博物院留存的2件和1959年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的14件带饰提交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做了无损或极小分量取样检测,经密度测定、光谱和X射线物相分析,确认全部带饰为含有杂质的同一种金属,是银而不是铝。
1972年,夏鼐发表《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一文,公布了上述鉴定结果。可知这16件较完整的带饰都是银的,另有少数小块金属片,有银的也有铝的;前者是银带饰的残片,后者细小而不成形,无法知其原形。根据文献考证及与广州、洛阳所出东晋、西晋同类实物相比对,确认银带饰为公元3世纪的遗物,无疑属晋元康七年(297年)埋葬周处时的随葬品。
至于小块铝质残片的年代,夏鼐认为“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夏鼐素来以严谨著称,他的分析也丝丝入扣:“在小块铝片不能确认为晋墓随葬物的情况下,如果它只不过是不辨器形的小块,而且只是两三小片(甚至于可能原来只是一片)的时候,它是后世混入物的可能性便更大了。”他指出,该墓曾有发生于元代和清代的至少两次盗掘。依发掘报告,1952年考古工作者正式发掘一号墓之前,“曾有些人进去过,还取出一部分文物,所以在墓内有明显的扰乱痕迹”;又引述罗宗真后来的文章中所称清理时“取出一些小块残片,是从淤土中尽可能拣出来的”一语,指出“这样一来,便不能保证小块铝片一定不是后世的混入物了”。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总之,据说是晋墓中发现的小块铝片,它是有后世混入物的重大嫌疑,决不能作为晋代已有金属铝的物证。今后我们最好不要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
对质疑意见的存疑
周处墓铝质残片的材质虽被确认,但对其来历在学理上却并无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学者断言西晋不可能有金属铝;夏鼐则谨慎地认为:“西晋炼出铝这件事,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可以说是不大可能的。”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
按说,严谨的考古学权威夏鼐一言既出,此事基本就算有个无法确证的定论了,但关于铝质残片的来历及其年代,又有不同的声音。
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先生对夏鼐的文章提出存疑。他引述罗宗真1963年的文章,认为残片系作者亲手发掘,且明确说明地层并未扰乱,残片并非盗掘时带入,因而不能视为混入的重大嫌疑。他还认为,周处墓先前两次被盗掘和1952年打开时曾有人进去,均不足以成为残片系混入物的凭据,所出残片锈迹斑斑,也不像是新混入的,而块小、量少、不成形,恰恰符合铝易被侵蚀的特性。
现在看来,这位多产作家的质疑并无太大新意和深度,但夏鼐以中国考古学领军人物的身份,仍耐心作答,认真讨论。叶永烈后来回忆道:“考古学家夏鼐与我之间,关于‘西晋有铝’问题的讨论信件,竟然有9封。”他还提及这样一个细节,与作家的信大多落款无时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给我的每一封信,都在信纸右上角端端正正写明‘19××年×月×日’,这无疑是他多年考古工作中养成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
自夏鼐于1972年发表长文后,多数学者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西晋炼铝之说归于沉寂。而铝片的发掘者罗宗真,则始终坚持铝片为晋代遗物。
新的思路与破解办法
诸位专家学者争议的实质在于晋代究竟是否有金属铝。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还不知道地球上有天然铝的存在。因此,所有争议便都限于晋代能否炼制金属铝这一点。既然在学理和实践的层面未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论据,西晋不可能有金属铝、铝片只能是后世混入物的这种非此即彼的论断为一些人所接受,也就可以理解,尽管这种论断也同样缺乏充分的判据。
鉴于上述,冶金史专家华觉明提出了两个探索周处墓铝质残片来历的新思路和破解办法。
第一,自然界确有天然铝,中国也有天然铝,周处墓铝质残片会不会与天然铝有某种关联?
铝的化学性质很活泼,长期以来没有人想到有天然铝的存在。然而自然界确有天然铝。1978年,苏联科学家奥列尼可夫等首次宣布,在西伯利亚台地的暗色岩中发现了天然铝。1983年,国际新矿物委员会确认了这一新发现,认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中国也有天然铝。1983年4月11日,新华社报道在广西贺县的花岗岩中发现了天然铝。此外,贵州安龙、湖南麻阳、广东莲花山等地也分别在1974年和1990年发现天然铝。
由于人们不知道有天然铝的存在,对周处墓铝质残片的来历局限于非此即彼(不是人工炼铝便是后世混入物)的两难选择之中。如今确证地球有天然铝,中国也有天然铝,且不仅出自一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美国、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还在做火法炼铝的工业试验,并且确实炼出了纯铝,这对我们探讨铝质残片来历有无启示作用?
华觉明进而指出,以上事例,在两个方面对我们或许有所启示:
首先,和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相反,电解法并非制铝的唯一方法,火法冶炼也可以得到纯铝。
其次,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周处墓铝质残片的议论已趋沉寂,许多人以为火法炼铝绝无可能之时,美国和日本却仍在做这样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火法炼铝的方法未被发现,或者古人已曾用过这类方法呢?
就我们已有的化学知识来说,确实很难想象早在晋代能炼出高纯度的金属铝来。而在古代技术条件下是否绝对没有可能以火法制取金属铝,仍须在学理上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反之亦然。
就周处墓铝质残片来历这一世纪悬案来说,最终结果究竟如何,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坚守科学精神,提倡思想自由,保有实事求是和包容的学术态度,才是推进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本文摘自《发现与推理:考古记事本末(一)》,许宏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许宏
周处墓的发现与发掘
1952年12月,江苏宜兴精一中学师生在挑土平整操场上的一处小土丘时,掘破了一座砖室墓的墓顶。公安人员进入墓室取出若干遗物后,将墓室封好,之后文物管理部门进行初步调查。1953年春,华东文物工作队派员对发现的两座墓葬做了发掘。
当地人称这处小土丘为周墓墩,相传为周处的墓地。土丘一角有“周王庙”,奉祀周处。经发掘,被掘开的墓葬(编为1号墓)中发现刻有文字的青砖,上书“元康七年九月廿日前周将军”等字样。清代《宜兴县志》记载周处葬于此,而周处正是西晋元康七年(297年)战死的,所以此墓为周处墓无疑。此前一些古代名人葬地位置,相关的记载和民间传说多以讹传讹,考古发现证实记载的例子并不多见,周处墓的发现算是考古界的一个佳话。
周处家族墓地是一处南北向隆起的坟丘,占地5.7万平方米。1953年和1976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其中的6座墓,6座墓南北排成一列,根据诸墓位置、结构形制及墓砖文字,可确定1号墓为周处墓,2号墓为周处子周札墓,3号墓亦为周处子周靖墓,4号墓为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周处父周鲂墓,5号墓为周处子周玘墓,6号墓为周鲂父周宾墓。周氏是三国东吴至西晋时期江南著名的大门阀士族,自周处的祖父周宾始著,经周鲂、周处至周玘、周札,“一门五侯”,“四世显著”。
周处墓虽早年被盗掘,还是出土了不少遗物,其中十余件带有镂孔花纹的金属带饰尤引人注目。更令人称奇的是,与其同出的某些金属残片经检测竟是铝质的,这大大超出了当时的认知。
检测生出的疑问
当时负责周处墓清理发掘和报告编写工作的是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先生。
1955年,罗宗真在考古报告整理的过程中,把从该墓出土的一件金属残片交南京大学化学系做了成分分析,得知内层为含铝约85%的铝铜合金。罗宗真在考古报告中写道:“像这样含有大量铝的合金,在我们工作中还是初次发现,为我们研究晋代冶金术提出了新的资料。”当这一考古报告的原稿投寄到中国考古学的权威杂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学报》时,时任该所所长、《考古学报》主编的夏鼐先生感觉兹事体大。作为民国时代的“海归”、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夏鼐知道,铝是一种难于冶炼的金属,到了19世纪才被冶炼出来,他在审核原稿校样时,怀疑这个“铝”字是否为“铅”字之误。他意识到问题的重大:“实际上,这不仅是我们考古工作中初次发现,也是全世界初次听说有这样古老的以铝为主要成分的合金。”慎重起见,夏鼐专门去函询问,索取样品,遂委托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陆学善先生做了光谱分析,确认残片内层的主要成分为铝。这一分析成果被夏鼐安排附在周处墓发掘报告的最后,连同他自己的“跋语”一同刊发于1957年第4期《考古学报》上。夏鼐在跋语的第一条即提及这一鉴定结果,指出“这是化学史和冶金史中的新发现”,接着提出他的疑问:“我们要问在当时是用什么方法提炼出这不易炼冶的金属达到85%的纯度?”
的确,铝在地球上虽含量丰富、分布甚广,但很难熔炼。即便对缺乏专业知识的公众而言,不少人也知道铝是最年轻的金属,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不敢想象金属铝的出现能够早到一千多年前的西晋时期。学术界对这一发现更是重视有加。
随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杨根先生又从夏鼐手中取得一小块残片,经光谱定性分析知其含大量的铝及其他微量元素,金相鉴定为多种合金组织。1959年春,南京博物院又送了几件残片给杨根。经检测,其中一片的主要成分为铝,另两片的主要成分为银。杨根结合汉晋时期鼓风技术的改进和炼丹术、制钢术的兴盛,认为在晋代出现这一杰出成就是有可能的:“这是世界化学史和冶金史上的一次创获,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成就。”
几次检测证明,这批金属器包含两种合金,一种为银基,一种为铝基。夏鼐后来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所分析的样品都是小块碎片,但全部17件较为完整的金属带饰都没有经过分析以确定其质料。由于出土文物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一般不做有损分析,不得已的情况下也是给些细小的碎片等。罗宗真提及“当时我们希望尽量可能地保存原物的完整,总是捡最小、最残的块片送去分析,并没有损坏原件”。显然,标本的局限性也增大了问题的复杂性。
铝从哪里来?
上述出土品的检测结果和论述还仅限于国内的学术刊物,对外展出后,引起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关注。1959年10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公开预展,由古代冶金陈列小组推荐,展出了周处墓所出全部带饰。南京博物院也曾展出过该墓出土的带饰,展品标签上都明确标示这些带饰系铝制品。这一定性,迅速在国际学术界和公众中引起了轰动。
截至1963年,国内发表的相关科普文章至少6篇,这些文章大多依从杨根的论断,肯定西晋时期已掌握了炼铝技术。
1962年,沈时英发表《关于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带饰成分问题》一文,在公布其对银质和铝质残片检测结果的基础上,做了较细致的讨论。他指出,在我国晋代产生银基合金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我国早在公元前就已经能够炼出金属银了。但其中测过多次的一片是含杂质较多的纯铝,“还难以证明它确为古代金属”。鉴于国内外火法炼铝的各种试验都未能获得高铝合金,更难以得到纯铝,用钠来还原氧化铝或其他铝盐的设想也很难成立。他强调指出:“关于晋代是否有铝带饰(纯铝的)问题,还应该作深入研究,下肯定性结论,似嫌为时过早”。
重新鉴定与夏鼐的再发言
如前所述,周处墓中出土的17件较完整而成形的金属带饰并未经过科学检测。显然,这些金属带饰究竟是否如先前所判定和展示的为铝质器件,必须予以鉴定。为此,夏鼐于1964年协调将南京博物院留存的2件和1959年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的14件带饰提交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做了无损或极小分量取样检测,经密度测定、光谱和X射线物相分析,确认全部带饰为含有杂质的同一种金属,是银而不是铝。
1972年,夏鼐发表《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一文,公布了上述鉴定结果。可知这16件较完整的带饰都是银的,另有少数小块金属片,有银的也有铝的;前者是银带饰的残片,后者细小而不成形,无法知其原形。根据文献考证及与广州、洛阳所出东晋、西晋同类实物相比对,确认银带饰为公元3世纪的遗物,无疑属晋元康七年(297年)埋葬周处时的随葬品。
至于小块铝质残片的年代,夏鼐认为“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夏鼐素来以严谨著称,他的分析也丝丝入扣:“在小块铝片不能确认为晋墓随葬物的情况下,如果它只不过是不辨器形的小块,而且只是两三小片(甚至于可能原来只是一片)的时候,它是后世混入物的可能性便更大了。”他指出,该墓曾有发生于元代和清代的至少两次盗掘。依发掘报告,1952年考古工作者正式发掘一号墓之前,“曾有些人进去过,还取出一部分文物,所以在墓内有明显的扰乱痕迹”;又引述罗宗真后来的文章中所称清理时“取出一些小块残片,是从淤土中尽可能拣出来的”一语,指出“这样一来,便不能保证小块铝片一定不是后世的混入物了”。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总之,据说是晋墓中发现的小块铝片,它是有后世混入物的重大嫌疑,决不能作为晋代已有金属铝的物证。今后我们最好不要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
对质疑意见的存疑
周处墓铝质残片的材质虽被确认,但对其来历在学理上却并无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学者断言西晋不可能有金属铝;夏鼐则谨慎地认为:“西晋炼出铝这件事,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可以说是不大可能的。”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
按说,严谨的考古学权威夏鼐一言既出,此事基本就算有个无法确证的定论了,但关于铝质残片的来历及其年代,又有不同的声音。
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先生对夏鼐的文章提出存疑。他引述罗宗真1963年的文章,认为残片系作者亲手发掘,且明确说明地层并未扰乱,残片并非盗掘时带入,因而不能视为混入的重大嫌疑。他还认为,周处墓先前两次被盗掘和1952年打开时曾有人进去,均不足以成为残片系混入物的凭据,所出残片锈迹斑斑,也不像是新混入的,而块小、量少、不成形,恰恰符合铝易被侵蚀的特性。
现在看来,这位多产作家的质疑并无太大新意和深度,但夏鼐以中国考古学领军人物的身份,仍耐心作答,认真讨论。叶永烈后来回忆道:“考古学家夏鼐与我之间,关于‘西晋有铝’问题的讨论信件,竟然有9封。”他还提及这样一个细节,与作家的信大多落款无时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给我的每一封信,都在信纸右上角端端正正写明‘19××年×月×日’,这无疑是他多年考古工作中养成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
自夏鼐于1972年发表长文后,多数学者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西晋炼铝之说归于沉寂。而铝片的发掘者罗宗真,则始终坚持铝片为晋代遗物。
新的思路与破解办法
诸位专家学者争议的实质在于晋代究竟是否有金属铝。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还不知道地球上有天然铝的存在。因此,所有争议便都限于晋代能否炼制金属铝这一点。既然在学理和实践的层面未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论据,西晋不可能有金属铝、铝片只能是后世混入物的这种非此即彼的论断为一些人所接受,也就可以理解,尽管这种论断也同样缺乏充分的判据。
鉴于上述,冶金史专家华觉明提出了两个探索周处墓铝质残片来历的新思路和破解办法。
第一,自然界确有天然铝,中国也有天然铝,周处墓铝质残片会不会与天然铝有某种关联?
铝的化学性质很活泼,长期以来没有人想到有天然铝的存在。然而自然界确有天然铝。1978年,苏联科学家奥列尼可夫等首次宣布,在西伯利亚台地的暗色岩中发现了天然铝。1983年,国际新矿物委员会确认了这一新发现,认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中国也有天然铝。1983年4月11日,新华社报道在广西贺县的花岗岩中发现了天然铝。此外,贵州安龙、湖南麻阳、广东莲花山等地也分别在1974年和1990年发现天然铝。
由于人们不知道有天然铝的存在,对周处墓铝质残片的来历局限于非此即彼(不是人工炼铝便是后世混入物)的两难选择之中。如今确证地球有天然铝,中国也有天然铝,且不仅出自一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美国、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还在做火法炼铝的工业试验,并且确实炼出了纯铝,这对我们探讨铝质残片来历有无启示作用?
华觉明进而指出,以上事例,在两个方面对我们或许有所启示:
首先,和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相反,电解法并非制铝的唯一方法,火法冶炼也可以得到纯铝。
其次,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周处墓铝质残片的议论已趋沉寂,许多人以为火法炼铝绝无可能之时,美国和日本却仍在做这样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火法炼铝的方法未被发现,或者古人已曾用过这类方法呢?
就我们已有的化学知识来说,确实很难想象早在晋代能炼出高纯度的金属铝来。而在古代技术条件下是否绝对没有可能以火法制取金属铝,仍须在学理上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反之亦然。
就周处墓铝质残片来历这一世纪悬案来说,最终结果究竟如何,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坚守科学精神,提倡思想自由,保有实事求是和包容的学术态度,才是推进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本文摘自《发现与推理:考古记事本末(一)》,许宏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