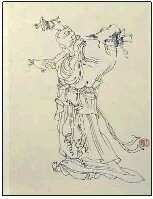有趣的灵魂,岂肯将人生书写权拱手让人
他们生前给自己写下墓志铭
齐鲁晚报 2024年04月06日
古代,当一个人走完自己的一生,亲朋好友会寻请一位有文采的名士,为他撰写一篇追述生平事迹的文字(序),再加上一段抒情的韵文(铭),合称墓志铭。接下来,经过书丹(用毛笔蘸取朱砂,将文字书写在平整的石板上)、凿刻等工序,将文字刻入石板,制成墓志。讲究的还要在墓志上覆盖一个尺寸相同的石质盖子,刻上“某某墓志”的字样,一起埋入主人的墓中。
唐宋以后,请名家撰写墓志铭已成为风尚,很多文学大家都留下了大量的墓志铭。如唐代的韩愈,他40卷的文集中,“碑志”就占了12卷。但总有些有趣的灵魂,不甘于将人生的书写权拱手让给他人。他们要用自己的笔,写下自己的墓志铭。恰逢清明时节,我们就来讲两个自撰墓志铭的人物故事。
□纪习尚
王绩,若顽若愚
王绩(585年-644年),字无功,号东皋子,“性简傲,好饮酒”,是隋末唐初著名的山水诗人。他出身于著名的太原王氏家族,有家学渊源,兄长王通是隋代著名的大儒,长期在河汾一带(今山西西南部)讲学,学生中不少成了政坛风云人物,如魏征、薛收、温彦博、杜淹、杜如晦等。644年,60岁的王绩染病。躺在病榻上,他自觉时日无多,不禁感叹这一生过得虽然自在潇洒,却无法被世人理解。为了展示一个真实的自己,他决定自撰墓志铭。
这篇著名的《自撰墓志铭》,第一句就是:“王绩者,有父母,无朋友。”为什么无朋友?这要从他的处世之道说起。
王绩的一生可以用“两起两落”概括。隋朝末年,王绩举孝悌廉洁科,先是在京城担任校勘典籍的“秘书省正字”,但是枯燥的文字工作与他放纵不羁的个性格格不入。于是他申请外放,担任扬州六合县丞,品级依然不高,但总算拥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王绩在这里完全放飞自我,他把工作推在一边,整日与酒为伴,按《新唐书》的说法就是:“嗜酒不任事。”而当时正值群雄并起的多事之秋,隋炀帝就待在咫尺之外的扬州,躺平的王绩因此被弹劾,退隐故乡。
回到故乡的王绩,种田、酿酒、养鹅、采药、占卜,过着逍遥的田园生活。他在河边有土地16顷,与河中心的沙洲相望。沙洲上住着一位不会说话的隐士,王绩敬佩他的为人,也搬到了沙洲上。两个志气相投的灵魂,不需要语言就可交流,王绩经常邀他饮酒,相对无语,但每饮必醉。
李渊建唐后,起用隋代的旧臣,王绩也以县丞的身份,担任门下省待诏,享受每天配给三升酒的待遇。已近不惑之年,而且经过了一轮官场起落的王绩,依然嗜酒如命。虽然只是个待诏的小官,却每天乐呵呵的,有人不解地问他:“待诏这么好吗?”王绩笑着说:“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我留恋这美酒啊!”这话传到了侍中陈叔达耳中,特意把他的配额提高到每天一斗,王绩因此被称为“斗酒学士”。
为了能喝到美酒,他甚至愿意自降身份。当时的太乐署史(官职名)善酿酒,王绩想担任他的下属官太乐丞,但主管官员调动的吏部不同意:“太乐丞是九品都不到的流外官,以你现在的身份,不宜担任。”但王绩紧追不放,吏部最后只好答应。
“不上进”如此,王绩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身边的人把他视为异类,甚至亲戚朋友家中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都不邀请他参加。事业上的成功也成泡影,自己虽然有才华,但不付出,怎么能建功立业、光耀门庭?他对此是清醒的,正如在《答程道士书》中的无奈自述:“吾自揆审矣,必不能自致台辅,恭宣大道。”于是不再留恋朝堂,决意退隐山林。
世间少了一个蹩脚的文官,却多了一个放达的诗人。两次隐居,他纵情山水间,左手酒樽、右手毛笔,写下了不少山水诗作。其中有《野望》:“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以及《秋夜喜遇王处士》:“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等名篇。
他又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呢?在墓志铭的序中,他说:“王绩者,有父母,无朋友,自为之字曰无功焉。人或问之,箕踞不对。盖以有道於己,无功於时也。不读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起家以禄位,历数职而进一阶,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於是退归,以酒德游於乡里,往往卖卜,时时著书,行若无所之,坐若无所据。乡人未有达其意也。”
短短数行,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个性老人形象。他不懂人情世故,不为达官贵人赏识,也不被邻里乡人理解。“无朋友”,是自嘲,也含着一丝嗔怪,亲人与朋友的疏远,他其实是在意的;至于“无功”,是说这一生没有取得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他不后悔,但内心其实是有遗憾的,如果真的放下了,怎么会将它取为自己的字?
铭中,他写道:“有唐逸人,太原王绩。若顽若愚,似矫似激。……不知节制,焉有亲戚?”那些没有邀请他参加家族大事的亲戚,他始终是记得的。
张岱,半生梦幻
隋唐之际有放诞不羁的王绩,明清之间则有颇具传奇色彩的张岱。两人相似之处不少:都经历过鼎革时期的兵荒马乱,都没有耀眼的仕途,都曾退隐山林、以著述度日。不过相比只留下三卷《王无功集》的王绩,张岱留给后人的作品很多,除诗歌外,还有史学著作《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古今义烈传》《史阙》,回忆录《陶庵梦忆》《快园道古》《西湖梦寻》,18卷的小品文《琅嬛文集》等,他的形象也因此更为立体。
张岱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约故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他漫长的一生中,前47年留在明代,后46年跨进了清朝。王朝更替深刻影响了他的生活,除了经济破产,因为与南明朝廷有过交往,他还被别人视为洪水猛兽。69岁时,张岱担心自己一旦倒下,就将如路边的草木,无人知晓。于是决定像王绩、陶潜、徐渭等前人一样,自撰墓志铭。他构思良久,反复多次,终于写成了这篇千余字的《自为墓志铭》。墓志铭中,张岱将自己的人生分为两段:“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前半段,张岱悠游自在,阅尽人间繁华。他出生在浙江山阴(今绍兴)一个富裕的书香家庭,童年时在外祖父陶允嘉处生活(张岱晚年自号陶庵老人,正是对母家的纪念),外祖父一家对他疼爱有加。在优渥而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张岱在提升学识的同时,也养成了率真的性格,对一切有趣的事物都充满好奇。后半段,明亡清兴,张岱的生活由安逸骤而艰难,心态也由热烈变为落寞。
他在墓志铭中说:“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甲申之后,是指1644年明朝灭亡以后,作为遗老,他精神上非常痛苦。1645年秋,为避兵乱,他隐居剡中(今浙江嵊州),再次回到家中时,已是一片狼藉。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窘境:“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数代的财产被劫掠一空,留下来的只有几件破烂家具,饭也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总结这一生,张岱在墓志铭中极尽戏谑,但字字透着认真。对自己年少时爱慕浮华、没有花全部时间读圣贤书,张岱毫不避讳,他写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这里,张岱一连用了12个“好”,并不是词汇的简单堆砌,而是实实在在都有所指。比如“好梨园”,他是资深票友。曾在南京听柳敬亭说书,在镇江金山观看夜戏,也曾在江苏武进欣赏女子表演昆曲;看戏之余,他还用文人的眼光评戏,留下了明末清初的宝贵戏剧资料。“好鼓吹”,说他爱好器乐,而且很有天赋。20岁和22岁时,他在绍兴跟随两位老师学习弹琴,半年时间就掌握了20多支曲子。张岱觉得老师的指法有些油滑,于是故意用生涩的指法弹奏,声音动听了不少。一个人玩不过瘾,他还组建了一支乐队——丝社,每月至少活动三次。张岱特意写了乐队章程,说明了宗旨和活动内容:“偕我同志,爰立琴盟,约有常期,宁虚芳日。杂丝和竹,用以鼓吹清音;动操鸣弦,自令众山皆响。”
正因为是写给自己,夸赞的、歌颂的词汇尽可略去,调侃的、诙谐的字眼无所顾忌。著作等身的张岱在墓志铭中称自己有“六不成”:“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这是自谦的说法,不必相信,但从中可看出,他毕生孜孜以求的,正是文章、书法、节义的尽善尽美。
后人会如何称呼自己?张岱想到了多种可能,但不管是什么,他都已不在乎了:“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唐宋以后,请名家撰写墓志铭已成为风尚,很多文学大家都留下了大量的墓志铭。如唐代的韩愈,他40卷的文集中,“碑志”就占了12卷。但总有些有趣的灵魂,不甘于将人生的书写权拱手让给他人。他们要用自己的笔,写下自己的墓志铭。恰逢清明时节,我们就来讲两个自撰墓志铭的人物故事。
□纪习尚
王绩,若顽若愚
王绩(585年-644年),字无功,号东皋子,“性简傲,好饮酒”,是隋末唐初著名的山水诗人。他出身于著名的太原王氏家族,有家学渊源,兄长王通是隋代著名的大儒,长期在河汾一带(今山西西南部)讲学,学生中不少成了政坛风云人物,如魏征、薛收、温彦博、杜淹、杜如晦等。644年,60岁的王绩染病。躺在病榻上,他自觉时日无多,不禁感叹这一生过得虽然自在潇洒,却无法被世人理解。为了展示一个真实的自己,他决定自撰墓志铭。
这篇著名的《自撰墓志铭》,第一句就是:“王绩者,有父母,无朋友。”为什么无朋友?这要从他的处世之道说起。
王绩的一生可以用“两起两落”概括。隋朝末年,王绩举孝悌廉洁科,先是在京城担任校勘典籍的“秘书省正字”,但是枯燥的文字工作与他放纵不羁的个性格格不入。于是他申请外放,担任扬州六合县丞,品级依然不高,但总算拥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王绩在这里完全放飞自我,他把工作推在一边,整日与酒为伴,按《新唐书》的说法就是:“嗜酒不任事。”而当时正值群雄并起的多事之秋,隋炀帝就待在咫尺之外的扬州,躺平的王绩因此被弹劾,退隐故乡。
回到故乡的王绩,种田、酿酒、养鹅、采药、占卜,过着逍遥的田园生活。他在河边有土地16顷,与河中心的沙洲相望。沙洲上住着一位不会说话的隐士,王绩敬佩他的为人,也搬到了沙洲上。两个志气相投的灵魂,不需要语言就可交流,王绩经常邀他饮酒,相对无语,但每饮必醉。
李渊建唐后,起用隋代的旧臣,王绩也以县丞的身份,担任门下省待诏,享受每天配给三升酒的待遇。已近不惑之年,而且经过了一轮官场起落的王绩,依然嗜酒如命。虽然只是个待诏的小官,却每天乐呵呵的,有人不解地问他:“待诏这么好吗?”王绩笑着说:“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我留恋这美酒啊!”这话传到了侍中陈叔达耳中,特意把他的配额提高到每天一斗,王绩因此被称为“斗酒学士”。
为了能喝到美酒,他甚至愿意自降身份。当时的太乐署史(官职名)善酿酒,王绩想担任他的下属官太乐丞,但主管官员调动的吏部不同意:“太乐丞是九品都不到的流外官,以你现在的身份,不宜担任。”但王绩紧追不放,吏部最后只好答应。
“不上进”如此,王绩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身边的人把他视为异类,甚至亲戚朋友家中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都不邀请他参加。事业上的成功也成泡影,自己虽然有才华,但不付出,怎么能建功立业、光耀门庭?他对此是清醒的,正如在《答程道士书》中的无奈自述:“吾自揆审矣,必不能自致台辅,恭宣大道。”于是不再留恋朝堂,决意退隐山林。
世间少了一个蹩脚的文官,却多了一个放达的诗人。两次隐居,他纵情山水间,左手酒樽、右手毛笔,写下了不少山水诗作。其中有《野望》:“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以及《秋夜喜遇王处士》:“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等名篇。
他又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呢?在墓志铭的序中,他说:“王绩者,有父母,无朋友,自为之字曰无功焉。人或问之,箕踞不对。盖以有道於己,无功於时也。不读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起家以禄位,历数职而进一阶,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於是退归,以酒德游於乡里,往往卖卜,时时著书,行若无所之,坐若无所据。乡人未有达其意也。”
短短数行,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个性老人形象。他不懂人情世故,不为达官贵人赏识,也不被邻里乡人理解。“无朋友”,是自嘲,也含着一丝嗔怪,亲人与朋友的疏远,他其实是在意的;至于“无功”,是说这一生没有取得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他不后悔,但内心其实是有遗憾的,如果真的放下了,怎么会将它取为自己的字?
铭中,他写道:“有唐逸人,太原王绩。若顽若愚,似矫似激。……不知节制,焉有亲戚?”那些没有邀请他参加家族大事的亲戚,他始终是记得的。
张岱,半生梦幻
隋唐之际有放诞不羁的王绩,明清之间则有颇具传奇色彩的张岱。两人相似之处不少:都经历过鼎革时期的兵荒马乱,都没有耀眼的仕途,都曾退隐山林、以著述度日。不过相比只留下三卷《王无功集》的王绩,张岱留给后人的作品很多,除诗歌外,还有史学著作《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古今义烈传》《史阙》,回忆录《陶庵梦忆》《快园道古》《西湖梦寻》,18卷的小品文《琅嬛文集》等,他的形象也因此更为立体。
张岱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约故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他漫长的一生中,前47年留在明代,后46年跨进了清朝。王朝更替深刻影响了他的生活,除了经济破产,因为与南明朝廷有过交往,他还被别人视为洪水猛兽。69岁时,张岱担心自己一旦倒下,就将如路边的草木,无人知晓。于是决定像王绩、陶潜、徐渭等前人一样,自撰墓志铭。他构思良久,反复多次,终于写成了这篇千余字的《自为墓志铭》。墓志铭中,张岱将自己的人生分为两段:“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前半段,张岱悠游自在,阅尽人间繁华。他出生在浙江山阴(今绍兴)一个富裕的书香家庭,童年时在外祖父陶允嘉处生活(张岱晚年自号陶庵老人,正是对母家的纪念),外祖父一家对他疼爱有加。在优渥而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张岱在提升学识的同时,也养成了率真的性格,对一切有趣的事物都充满好奇。后半段,明亡清兴,张岱的生活由安逸骤而艰难,心态也由热烈变为落寞。
他在墓志铭中说:“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甲申之后,是指1644年明朝灭亡以后,作为遗老,他精神上非常痛苦。1645年秋,为避兵乱,他隐居剡中(今浙江嵊州),再次回到家中时,已是一片狼藉。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窘境:“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数代的财产被劫掠一空,留下来的只有几件破烂家具,饭也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总结这一生,张岱在墓志铭中极尽戏谑,但字字透着认真。对自己年少时爱慕浮华、没有花全部时间读圣贤书,张岱毫不避讳,他写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这里,张岱一连用了12个“好”,并不是词汇的简单堆砌,而是实实在在都有所指。比如“好梨园”,他是资深票友。曾在南京听柳敬亭说书,在镇江金山观看夜戏,也曾在江苏武进欣赏女子表演昆曲;看戏之余,他还用文人的眼光评戏,留下了明末清初的宝贵戏剧资料。“好鼓吹”,说他爱好器乐,而且很有天赋。20岁和22岁时,他在绍兴跟随两位老师学习弹琴,半年时间就掌握了20多支曲子。张岱觉得老师的指法有些油滑,于是故意用生涩的指法弹奏,声音动听了不少。一个人玩不过瘾,他还组建了一支乐队——丝社,每月至少活动三次。张岱特意写了乐队章程,说明了宗旨和活动内容:“偕我同志,爰立琴盟,约有常期,宁虚芳日。杂丝和竹,用以鼓吹清音;动操鸣弦,自令众山皆响。”
正因为是写给自己,夸赞的、歌颂的词汇尽可略去,调侃的、诙谐的字眼无所顾忌。著作等身的张岱在墓志铭中称自己有“六不成”:“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这是自谦的说法,不必相信,但从中可看出,他毕生孜孜以求的,正是文章、书法、节义的尽善尽美。
后人会如何称呼自己?张岱想到了多种可能,但不管是什么,他都已不在乎了:“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