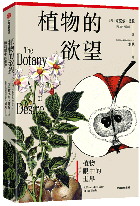苹果的甘甜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齐鲁晚报 2025年08月29日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植物的驯化视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在著作《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一书中,美国作家迈克尔·波伦从植物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史,提出植物通过满足人类的欲望——甘甜、美丽、陶醉和控制,成功地让人类为它们服务,传播它们的基因。
□迈克尔·波伦
苹果籽约翰尼
1806年春的某个下午,如果你正好站在俄亥俄河岸边,比如西弗吉尼亚惠灵以北的某个地方,那么你八成会注意到有一条简易河船正在向下游缓缓驶去。这条船,其实是两根挖空的原木,它们绑在一起便成了一条简陋的双体船,或者说是一条挂着“边车”的独木舟。独木舟中懒散地躺着一名约莫30岁的精瘦男子,他的“边车”,也就是这条双体船的另一个船体里面,许多种子堆成了一座小山,把船体压得吃水更深。其上小心翼翼地盖着一层藓泥,以免种子被阳光烤干。
在独木舟中打盹儿的那个家伙叫约翰·查普曼,俄亥俄人早就熟知他的绰号——“苹果籽约翰尼”。此刻,他正前往玛丽埃塔,在那里,马斯金格姆河把俄亥俄河的北岸凿断,由这巨大的豁口可以直抵西北领地的腹心。马斯金格姆河许多支流的流域尚无欧洲人定居,从北至曼斯菲尔德的地方开始,它们就在俄亥俄州那些土壤肥沃、森林茂密的山丘间流淌。查普曼的计划是在其中一条支流的河畔建立果树苗圃。这个人最有可能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阿勒格尼县,每年他都回到那里采集苹果种子,从每一家苹果酒坊后门旁边堆积如山的苹果渣中把它们拣出来。查普曼那天带走了多少种子,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但可以确信的是,他那条双体船运往荒野的东西,足以建立好几个完整的果园。
亨利·戴维·梭罗曾写道:“值得注意的是,苹果树的历史与人的历史紧密关联。”在这段历史中,美国那一章的大部分都反映在查普曼的故事里。这是拓荒者的故事,作为拓荒者的查普曼,通过种植旧世界的植物,把新世界的边疆改造成了宜居之地。今天,我们往往会轻蔑地说这些物种是带有“异国情调”的玩意儿,然而如果没有它们,美国的荒野恐怕永远也成不了人的家园。那么,苹果又得到了什么回报呢?它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涌现了不计其数的新品种,把另外半个世界变成它的新栖息地。
在与其他物种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过分夸大了自己的功劳。尽管物种驯化似乎代表了征服自然的力量,但就连这种力量也是言过其实的。毕竟,这种特别的舞蹈需要两方参与才跳得下去,而很多动植物都选择不跳。比如人类尽了很大的努力,却从未能驯化栎树——它所结的橡实虽然营养丰富,对人类来说却苦不堪食。很明显,栎树与松鼠合作得很愉快——松鼠每埋下大约4颗橡实,就会不由自主地忘掉其中1颗的埋藏地点——但栎树从来不需要与人类达成任何种类的正式协议。
苹果则不然,它非常渴望与人类做交易。就像之前和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移民一样,苹果也把美国当成了家。在这个过程中,把种子成船运到边疆的苹果籽约翰尼出了很大力,但苹果自己也出了很大力。苹果并不只是乘客或受供养者,它就是它自己故事的主人公。
回归野外才可能重生
用种子并不能种出和原来一模一样的苹果。也就是说,从种子长成的苹果树,是一种野生型苹果树,与其母树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任何人如果想收获可食用的苹果,都得采用嫁接术,因为实生树结出的苹果基本都不堪食用。梭罗就写道,它们“酸得足以让松鼠倒牙,让松鸦尖叫”。梭罗声称他喜欢这种苹果的味道,但是他的大部分同胞都觉得它们除酿造苹果酒以外几乎毫无用处——颁布禁酒令之前,大部分苹果的最终命运都是被酿成苹果酒。
将一个苹果拦腰横向切开,你会看到中央有5个小室,它们排列成完美对称的星芒状,仿佛五角星图案。每一室中都生有一粒种子(偶尔两粒),种子表面是有光泽的深褐色,仿佛由木匠上过油、抛过光。对于苹果种子,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它们含有少量氰化物,很可能是苹果演化出来的防御机制,用于阻止尝试嚼食种子的动物:它们尝起来几乎都苦不堪言。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与这些种子的遗传成分有关,其中同样满是意外。不必提与约翰·查普曼一同沿俄亥俄河而下的那些种子,即便是你切开的苹果里的每粒种子,其所包含的遗传指令都可以打造一棵全新而迥异的苹果树。将其种下之后,长出的树只是乍一看与母树相似。如果不采用嫁接这种古老的无性繁殖技术,那么世界上每个苹果都会自成一个品种,没有一个优良的品种能够在唯一的那棵苹果树寿终正寝之后存续下去。就苹果树而言,它的果实几乎总是与母树相去甚远。
植物学上管这种多变性叫“杂合性”。虽然很多物种都有这种特征,但在苹果那里,杂合性发挥到了极致。比起其他任何单一特征,苹果的遗传多变性,也就是它无可避免的野性,都可以更好地解释它何以能够在各种地方欣欣向荣,无论是在新英格兰还是新西兰,无论是在哈萨克斯坦还是加利福尼亚,它都能安家落户。不管苹果树在哪里落籍,它的后代总能为“苹果”这个概念提供众多不同的变体——单独一个苹果就能提供至少5个变体,而每棵树能提供数千个。其中几乎总会有一些新奇的变异个体,能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品质,在这棵树入籍的新家园让后代得以茁壮成长。
对苹果树真正的驯化,要等到中国人发明嫁接术。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某个时候,中国人发现,可以从一棵合意的树上斫下一段树枝,将它嵌进另一棵树的树干里,一旦嫁接成功,从那个接合点长出的新枝条结出的果实,便能拥有其母株所拥有的优良性状。正是这种技术最终让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能够把最上等的品种拣选出来,加以繁育。这时候,苹果在欧洲似乎已经安居了一段时间。根据记载,罗马人栽培了23个不同的苹果品种,还把其中一些带到了英国。
正如梭罗在一篇赞美野苹果的文章中所说,果树一直跟随着帝国西进的历程,先从古代世界来到欧洲,然后与早期移居者一起来到美洲。最早前往美洲的移民随身携带了嫁接而成的旧世界苹果树,但这些树苗在新的家园通常都长势不良。严酷的寒冬让很多苹果树骤然冻毙;即使冬天能幸免于难,在英国闻所未闻的晚春霜冻又把很多果实扼杀在花期。然而殖民者也用种子种树——在大西洋上漂泊时,他们吃掉苹果,把里面的种子保留下来。最终是用这些种子种出来的“枇苹”,也就是由实生苗长成的果树,得以在新世界茁壮成长。(特别是后来殖民者还进口了蜜蜂,用于改善传粉;在此之前,苹果树的传粉情况时好时坏,很不稳定。)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1年就声称,纽约州弗拉兴一个酿酒用苹果园里有一个本土品种叫“纽敦枇苹”,名声大得已经传到了欧洲。
实际上,苹果就像移居者自己一样,不得不放弃以前的家居生活,回归野外,然后才可能重生,比如“纽敦枇苹”“鲍德温”“金色锈斑”“红玉”。这正是约翰·查普曼那条船上的苹果种子要做的事。苹果当年一路穿越亚洲和欧洲,逐渐积累了庞大的基因储备。通过回归野生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进行有性繁殖,结出种子,苹果便可以在这庞大储备中深入挖掘,发现它在新世界存活所急需的精准性状组合。美洲本土还有北美海棠类植物,它们是这里仅有的苹果类树种。苹果又可能与它们杂交,获得一些所需的性状。多亏了这个种原本就拥有的巨大资源,加上约翰·查普曼等人的努力,新世界只用了相当短的时间就孕育出了自己的苹果品种。它们适应了北美洲的土壤、气候和白昼长度,既与古老的欧洲株系不同,又与美洲本土的野生种有异。
甘甜促进苹果演化
我们需要开展一次历史想象的飞跃,才能意识到苹果对生活在200年前的人们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苹果在我们眼中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虽然它是一种人们广为食用的水果(仅次于香蕉),但生活中就算没有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对我们来说,更难想象的是如果没有甘甜的体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在查普曼的时代,苹果能够提供给美国人的东西正是甘甜,最宽泛、最古老意义上的甘甜,这是它可以满足的欲望。
糖在18世纪的美国是稀缺品。即使在加勒比地区建立了甘蔗种植园之后,糖仍然是大多数美国人无法企及的奢侈品。在英国人到来之前,以及到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北美洲也没有蜜蜂,因此无蜜可吃;北方的印第安人则只能依赖槭糖作为甜味剂。直到19世纪后期,糖才变得量大价廉,得以进入许多美国人的生活(其中大多数人生活在东海岸);在此之前,大多数人生活中的甘甜感主要来自水果的果肉。在美国,这通常就意味着苹果。
甘甜是一种欲望,始于舌头的味觉,但并非就在这里结束。至少在过去,它并非在这里结束。从前,甘甜的体验如此特别,以至于这个词成了某种完美状态的隐喻。人们会说最好的土地是甘甜的;最悦耳的声音、最有说服力的话语、最美丽的景色、最优雅的人,都是甘甜的;任何整体中最精华的部分是甘甜的,所以莎士比亚会说春季是“一年中的甘甜时节”。“甘甜”作为形容词,被舌头借给了其他所有感官,于是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它有了一个多少有些陈旧的定义——“能够提供快乐或满足欲望”。当它作为名词时,它又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等号,用于指称任何符合人类欲望的实在之物:甘甜代表满足。
人类学家发现,不同的文化对苦味、酸味和咸味的喜爱程度差异甚大,但对甜味的喜爱是一样的。很多动物也是如此,这并不奇怪,因为糖分是自然界储存食物能量的方式。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我们对甜味的初次体验来自母亲的乳汁。也许甘甜就是我们在乳房上尝到的味道;也许我们天生就有追求甘甜的本能,因此会对母亲的乳汁满怀渴望。
不管是哪种情况,事实都表明,甘甜是促进演化的一种力量。苹果树之类结水果的植物把它们的种子包裹在富含糖分和营养的果肉中,从而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利用哺乳动物喜好甜食的习性。水果提供了果糖,作为交换,动物要帮助运输种子,让植物能够扩展地盘。在这场伟大的协同演化交易中,动物一方对甜味具有极为强烈的偏好,植物一方则尽己所能地提供又大又甜的果实,双方一道繁衍生息,如此便演化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物种,以及我们人类自身。但是植物也采取了一些方法作为预防措施,保护它们的种子不被合作方的贪婪摧毁。它们会把甜味和果色的发育一直推迟到种子完全成熟之时(在此之前,果实往往呈现不起眼的青绿色,也不堪入口);有些植物会在种子中积累毒素,确保动物只会吃甘甜的果肉,比如苹果就是如此。
人们刺激某些酵母摄食植物制造的糖分,然后它们就制造出酒精。在禁酒令颁布之前,美国种出来的苹果很少有机会被直接食用,最终大都存到了酒桶里。到20世纪,苹果才获得了有益健康的名声——“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是那些担心禁酒会严重影响苹果销量的苹果种植者凭空编造的营销口号。
(本文摘选自《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内容有删节,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迈克尔·波伦
苹果籽约翰尼
1806年春的某个下午,如果你正好站在俄亥俄河岸边,比如西弗吉尼亚惠灵以北的某个地方,那么你八成会注意到有一条简易河船正在向下游缓缓驶去。这条船,其实是两根挖空的原木,它们绑在一起便成了一条简陋的双体船,或者说是一条挂着“边车”的独木舟。独木舟中懒散地躺着一名约莫30岁的精瘦男子,他的“边车”,也就是这条双体船的另一个船体里面,许多种子堆成了一座小山,把船体压得吃水更深。其上小心翼翼地盖着一层藓泥,以免种子被阳光烤干。
在独木舟中打盹儿的那个家伙叫约翰·查普曼,俄亥俄人早就熟知他的绰号——“苹果籽约翰尼”。此刻,他正前往玛丽埃塔,在那里,马斯金格姆河把俄亥俄河的北岸凿断,由这巨大的豁口可以直抵西北领地的腹心。马斯金格姆河许多支流的流域尚无欧洲人定居,从北至曼斯菲尔德的地方开始,它们就在俄亥俄州那些土壤肥沃、森林茂密的山丘间流淌。查普曼的计划是在其中一条支流的河畔建立果树苗圃。这个人最有可能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阿勒格尼县,每年他都回到那里采集苹果种子,从每一家苹果酒坊后门旁边堆积如山的苹果渣中把它们拣出来。查普曼那天带走了多少种子,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但可以确信的是,他那条双体船运往荒野的东西,足以建立好几个完整的果园。
亨利·戴维·梭罗曾写道:“值得注意的是,苹果树的历史与人的历史紧密关联。”在这段历史中,美国那一章的大部分都反映在查普曼的故事里。这是拓荒者的故事,作为拓荒者的查普曼,通过种植旧世界的植物,把新世界的边疆改造成了宜居之地。今天,我们往往会轻蔑地说这些物种是带有“异国情调”的玩意儿,然而如果没有它们,美国的荒野恐怕永远也成不了人的家园。那么,苹果又得到了什么回报呢?它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涌现了不计其数的新品种,把另外半个世界变成它的新栖息地。
在与其他物种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过分夸大了自己的功劳。尽管物种驯化似乎代表了征服自然的力量,但就连这种力量也是言过其实的。毕竟,这种特别的舞蹈需要两方参与才跳得下去,而很多动植物都选择不跳。比如人类尽了很大的努力,却从未能驯化栎树——它所结的橡实虽然营养丰富,对人类来说却苦不堪食。很明显,栎树与松鼠合作得很愉快——松鼠每埋下大约4颗橡实,就会不由自主地忘掉其中1颗的埋藏地点——但栎树从来不需要与人类达成任何种类的正式协议。
苹果则不然,它非常渴望与人类做交易。就像之前和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移民一样,苹果也把美国当成了家。在这个过程中,把种子成船运到边疆的苹果籽约翰尼出了很大力,但苹果自己也出了很大力。苹果并不只是乘客或受供养者,它就是它自己故事的主人公。
回归野外才可能重生
用种子并不能种出和原来一模一样的苹果。也就是说,从种子长成的苹果树,是一种野生型苹果树,与其母树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任何人如果想收获可食用的苹果,都得采用嫁接术,因为实生树结出的苹果基本都不堪食用。梭罗就写道,它们“酸得足以让松鼠倒牙,让松鸦尖叫”。梭罗声称他喜欢这种苹果的味道,但是他的大部分同胞都觉得它们除酿造苹果酒以外几乎毫无用处——颁布禁酒令之前,大部分苹果的最终命运都是被酿成苹果酒。
将一个苹果拦腰横向切开,你会看到中央有5个小室,它们排列成完美对称的星芒状,仿佛五角星图案。每一室中都生有一粒种子(偶尔两粒),种子表面是有光泽的深褐色,仿佛由木匠上过油、抛过光。对于苹果种子,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它们含有少量氰化物,很可能是苹果演化出来的防御机制,用于阻止尝试嚼食种子的动物:它们尝起来几乎都苦不堪言。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与这些种子的遗传成分有关,其中同样满是意外。不必提与约翰·查普曼一同沿俄亥俄河而下的那些种子,即便是你切开的苹果里的每粒种子,其所包含的遗传指令都可以打造一棵全新而迥异的苹果树。将其种下之后,长出的树只是乍一看与母树相似。如果不采用嫁接这种古老的无性繁殖技术,那么世界上每个苹果都会自成一个品种,没有一个优良的品种能够在唯一的那棵苹果树寿终正寝之后存续下去。就苹果树而言,它的果实几乎总是与母树相去甚远。
植物学上管这种多变性叫“杂合性”。虽然很多物种都有这种特征,但在苹果那里,杂合性发挥到了极致。比起其他任何单一特征,苹果的遗传多变性,也就是它无可避免的野性,都可以更好地解释它何以能够在各种地方欣欣向荣,无论是在新英格兰还是新西兰,无论是在哈萨克斯坦还是加利福尼亚,它都能安家落户。不管苹果树在哪里落籍,它的后代总能为“苹果”这个概念提供众多不同的变体——单独一个苹果就能提供至少5个变体,而每棵树能提供数千个。其中几乎总会有一些新奇的变异个体,能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品质,在这棵树入籍的新家园让后代得以茁壮成长。
对苹果树真正的驯化,要等到中国人发明嫁接术。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某个时候,中国人发现,可以从一棵合意的树上斫下一段树枝,将它嵌进另一棵树的树干里,一旦嫁接成功,从那个接合点长出的新枝条结出的果实,便能拥有其母株所拥有的优良性状。正是这种技术最终让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能够把最上等的品种拣选出来,加以繁育。这时候,苹果在欧洲似乎已经安居了一段时间。根据记载,罗马人栽培了23个不同的苹果品种,还把其中一些带到了英国。
正如梭罗在一篇赞美野苹果的文章中所说,果树一直跟随着帝国西进的历程,先从古代世界来到欧洲,然后与早期移居者一起来到美洲。最早前往美洲的移民随身携带了嫁接而成的旧世界苹果树,但这些树苗在新的家园通常都长势不良。严酷的寒冬让很多苹果树骤然冻毙;即使冬天能幸免于难,在英国闻所未闻的晚春霜冻又把很多果实扼杀在花期。然而殖民者也用种子种树——在大西洋上漂泊时,他们吃掉苹果,把里面的种子保留下来。最终是用这些种子种出来的“枇苹”,也就是由实生苗长成的果树,得以在新世界茁壮成长。(特别是后来殖民者还进口了蜜蜂,用于改善传粉;在此之前,苹果树的传粉情况时好时坏,很不稳定。)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1年就声称,纽约州弗拉兴一个酿酒用苹果园里有一个本土品种叫“纽敦枇苹”,名声大得已经传到了欧洲。
实际上,苹果就像移居者自己一样,不得不放弃以前的家居生活,回归野外,然后才可能重生,比如“纽敦枇苹”“鲍德温”“金色锈斑”“红玉”。这正是约翰·查普曼那条船上的苹果种子要做的事。苹果当年一路穿越亚洲和欧洲,逐渐积累了庞大的基因储备。通过回归野生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进行有性繁殖,结出种子,苹果便可以在这庞大储备中深入挖掘,发现它在新世界存活所急需的精准性状组合。美洲本土还有北美海棠类植物,它们是这里仅有的苹果类树种。苹果又可能与它们杂交,获得一些所需的性状。多亏了这个种原本就拥有的巨大资源,加上约翰·查普曼等人的努力,新世界只用了相当短的时间就孕育出了自己的苹果品种。它们适应了北美洲的土壤、气候和白昼长度,既与古老的欧洲株系不同,又与美洲本土的野生种有异。
甘甜促进苹果演化
我们需要开展一次历史想象的飞跃,才能意识到苹果对生活在200年前的人们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苹果在我们眼中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虽然它是一种人们广为食用的水果(仅次于香蕉),但生活中就算没有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对我们来说,更难想象的是如果没有甘甜的体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在查普曼的时代,苹果能够提供给美国人的东西正是甘甜,最宽泛、最古老意义上的甘甜,这是它可以满足的欲望。
糖在18世纪的美国是稀缺品。即使在加勒比地区建立了甘蔗种植园之后,糖仍然是大多数美国人无法企及的奢侈品。在英国人到来之前,以及到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北美洲也没有蜜蜂,因此无蜜可吃;北方的印第安人则只能依赖槭糖作为甜味剂。直到19世纪后期,糖才变得量大价廉,得以进入许多美国人的生活(其中大多数人生活在东海岸);在此之前,大多数人生活中的甘甜感主要来自水果的果肉。在美国,这通常就意味着苹果。
甘甜是一种欲望,始于舌头的味觉,但并非就在这里结束。至少在过去,它并非在这里结束。从前,甘甜的体验如此特别,以至于这个词成了某种完美状态的隐喻。人们会说最好的土地是甘甜的;最悦耳的声音、最有说服力的话语、最美丽的景色、最优雅的人,都是甘甜的;任何整体中最精华的部分是甘甜的,所以莎士比亚会说春季是“一年中的甘甜时节”。“甘甜”作为形容词,被舌头借给了其他所有感官,于是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它有了一个多少有些陈旧的定义——“能够提供快乐或满足欲望”。当它作为名词时,它又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等号,用于指称任何符合人类欲望的实在之物:甘甜代表满足。
人类学家发现,不同的文化对苦味、酸味和咸味的喜爱程度差异甚大,但对甜味的喜爱是一样的。很多动物也是如此,这并不奇怪,因为糖分是自然界储存食物能量的方式。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我们对甜味的初次体验来自母亲的乳汁。也许甘甜就是我们在乳房上尝到的味道;也许我们天生就有追求甘甜的本能,因此会对母亲的乳汁满怀渴望。
不管是哪种情况,事实都表明,甘甜是促进演化的一种力量。苹果树之类结水果的植物把它们的种子包裹在富含糖分和营养的果肉中,从而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利用哺乳动物喜好甜食的习性。水果提供了果糖,作为交换,动物要帮助运输种子,让植物能够扩展地盘。在这场伟大的协同演化交易中,动物一方对甜味具有极为强烈的偏好,植物一方则尽己所能地提供又大又甜的果实,双方一道繁衍生息,如此便演化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物种,以及我们人类自身。但是植物也采取了一些方法作为预防措施,保护它们的种子不被合作方的贪婪摧毁。它们会把甜味和果色的发育一直推迟到种子完全成熟之时(在此之前,果实往往呈现不起眼的青绿色,也不堪入口);有些植物会在种子中积累毒素,确保动物只会吃甘甜的果肉,比如苹果就是如此。
人们刺激某些酵母摄食植物制造的糖分,然后它们就制造出酒精。在禁酒令颁布之前,美国种出来的苹果很少有机会被直接食用,最终大都存到了酒桶里。到20世纪,苹果才获得了有益健康的名声——“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是那些担心禁酒会严重影响苹果销量的苹果种植者凭空编造的营销口号。
(本文摘选自《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内容有删节,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