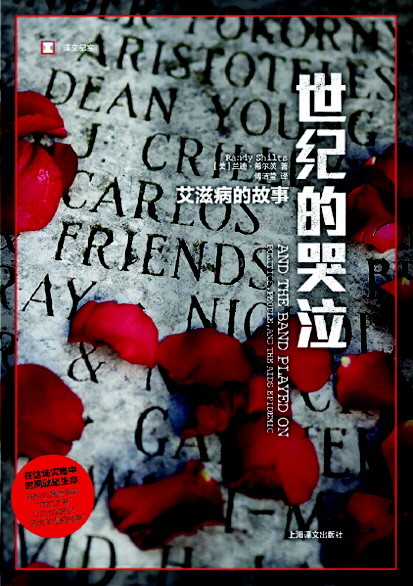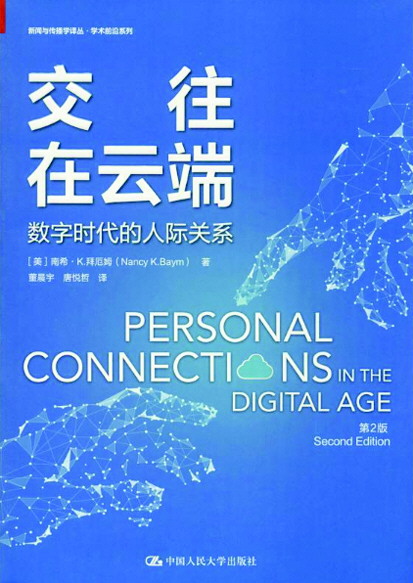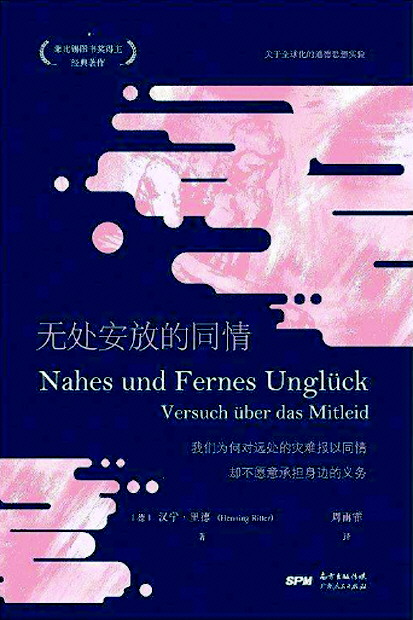阅读的力量
齐鲁晚报 2020年03月21日
□曲鹏
一张照片,让在武汉方舱医院读书的“清流哥”意外走红。在疾病面前,在浮躁面前,他依然能和自己安然相处。可见,一个习惯阅读的人,更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内心的力量是强大的。
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对艾滋病认知历程的《世纪的哭泣》一书,英文原版于1987年问世,三十多年之后中文版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作者兰迪·希尔茨是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意识到艾滋病问题的美国记者之一。当时,美国人仍然相信,不幸罹患此症的只能是同性恋者或某些阶层的弃儿和贱民,而国家的相关机构——医疗、公共卫生、科研、大众传媒等——都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直到1985年夏天,一位电影明星被诊断为艾滋病患者,公众才真正重视起这种疾病,而此时病毒已在全国肆虐,无法控制。“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艾滋病并不是平白无故在美国蔓延的。”希尔茨本人也是艾滋病的受害者,在服用抗艾滋病药物几年后,他在1994年死于艾滋病并发症。但幸运的是,他的这本《世纪的哭泣》为我们还原了这场隐秘灾难的始末,也揭示了身处其中的民众的轻视、制度的冷漠以及反抗者的重重艰难。
去年,日剧《坡道上的家》因为切中了日本社会“女主内男主外”家庭结构所造成的“丧偶式育儿”症结,在影评网站上获得9.1分的高分,引发巨大关注,在中国女性观众中也反响强烈。日前,《坡道上的家》原著同名小说由磨铁·文治图书引进出版。小说作者为日本直木奖作家角田光代,擅长写当代女性的生存状况,代表作有《第八日的蝉》《空中庭园》《纸之月》《我是纱有美》《对岸的她》等。小说新作《坡道上的家》塑造了一位女性陪审员形象,她在一桩母亲杀害幼女案件中,随着庭审深入,从被告的经历中反观自身,进而重新审视职业女性在今日婚姻、家庭中的身份与关系。已婚未育的角田光代表示自己未曾想过要生小孩,经常听到身边很多当了妈妈的朋友抱怨“带孩子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在她看来,“育儿”并非是一个个体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家庭的问题,这其实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如果女性想要一个孩子,我们整个社会怎么来帮她达成愿望,这是全社会必须共同努力的一件事情”。
现任微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南希·K.拜厄姆,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传播学教授,参与创立互联网研究者协会并曾担任主席。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互联网,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传播、新媒体和粉丝文化。其著作《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将学术研究和生活实例相结合,讨论了我们应该如何使用中介化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来发展社区和社交网络,又如何建立线上的新关系、维系线下的旧关系。中介化互动可以是温情和私人化的吗?人们在线上会撒谎吗?在线上建立的关系可靠吗?数字媒体会破坏我们的其他关系吗?对于这些常有的疑虑,拜厄姆指出,我们当下对新媒体的评价与历史上关于早期通信技术的讨论其实并无两样——“当讨论技术时,我们会表达某些社会层面的担忧。其实,在没有这些技术时,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担忧,因为这些担忧的本质是一直存在的。比如说,如何成为真正的自己,如何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如何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如何在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中安身立命。”
同情和共感,原本是人们对身边的同胞所抱有的情感。当全球化使世界变得看似越来越小,当传媒技术足以将灾难的现场在视觉和听觉上带到我们身边,当世界各地发生的不幸都能够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们是否会对不相识的他者产生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同情呢?而这种看似普世的同情心,将指引人们走向无边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抽象的伪道德,不指向任何具体的道德行为,最终让人们在伦理方面成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呢?哲学散文集《无处安放的同情》即是德国作家汉宁·里德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的思索。里德将读者带回18世纪道德哲学的讨论现场,狄德罗笔下“残暴的思考者”、卢梭笔下“捂住耳朵的哲学家”、亚当·斯密虚构出的“富有人性的伦敦人”等悉数登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在道德方面所抱有的不安。这场关于同情心的跨时空大辩论,对解读当下的道德处境颇有裨益。里德是卢梭的忠实粉丝,曾翻译过卢梭全集的德文版,《无处安放的同情》中关于卢梭的文本,是对卢梭思想极好的现代版注解。“无处安放的同情”让我们时时处在焦虑之中,如何摆脱这种情绪,里德并未在书中给出明确答案,不如引用卢梭的一句话:“关键是,我们要对身边人好。”看似简单,却不易做到吧。
一张照片,让在武汉方舱医院读书的“清流哥”意外走红。在疾病面前,在浮躁面前,他依然能和自己安然相处。可见,一个习惯阅读的人,更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内心的力量是强大的。
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对艾滋病认知历程的《世纪的哭泣》一书,英文原版于1987年问世,三十多年之后中文版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作者兰迪·希尔茨是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意识到艾滋病问题的美国记者之一。当时,美国人仍然相信,不幸罹患此症的只能是同性恋者或某些阶层的弃儿和贱民,而国家的相关机构——医疗、公共卫生、科研、大众传媒等——都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直到1985年夏天,一位电影明星被诊断为艾滋病患者,公众才真正重视起这种疾病,而此时病毒已在全国肆虐,无法控制。“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艾滋病并不是平白无故在美国蔓延的。”希尔茨本人也是艾滋病的受害者,在服用抗艾滋病药物几年后,他在1994年死于艾滋病并发症。但幸运的是,他的这本《世纪的哭泣》为我们还原了这场隐秘灾难的始末,也揭示了身处其中的民众的轻视、制度的冷漠以及反抗者的重重艰难。
去年,日剧《坡道上的家》因为切中了日本社会“女主内男主外”家庭结构所造成的“丧偶式育儿”症结,在影评网站上获得9.1分的高分,引发巨大关注,在中国女性观众中也反响强烈。日前,《坡道上的家》原著同名小说由磨铁·文治图书引进出版。小说作者为日本直木奖作家角田光代,擅长写当代女性的生存状况,代表作有《第八日的蝉》《空中庭园》《纸之月》《我是纱有美》《对岸的她》等。小说新作《坡道上的家》塑造了一位女性陪审员形象,她在一桩母亲杀害幼女案件中,随着庭审深入,从被告的经历中反观自身,进而重新审视职业女性在今日婚姻、家庭中的身份与关系。已婚未育的角田光代表示自己未曾想过要生小孩,经常听到身边很多当了妈妈的朋友抱怨“带孩子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在她看来,“育儿”并非是一个个体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家庭的问题,这其实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如果女性想要一个孩子,我们整个社会怎么来帮她达成愿望,这是全社会必须共同努力的一件事情”。
现任微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南希·K.拜厄姆,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传播学教授,参与创立互联网研究者协会并曾担任主席。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互联网,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传播、新媒体和粉丝文化。其著作《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将学术研究和生活实例相结合,讨论了我们应该如何使用中介化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来发展社区和社交网络,又如何建立线上的新关系、维系线下的旧关系。中介化互动可以是温情和私人化的吗?人们在线上会撒谎吗?在线上建立的关系可靠吗?数字媒体会破坏我们的其他关系吗?对于这些常有的疑虑,拜厄姆指出,我们当下对新媒体的评价与历史上关于早期通信技术的讨论其实并无两样——“当讨论技术时,我们会表达某些社会层面的担忧。其实,在没有这些技术时,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担忧,因为这些担忧的本质是一直存在的。比如说,如何成为真正的自己,如何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如何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如何在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中安身立命。”
同情和共感,原本是人们对身边的同胞所抱有的情感。当全球化使世界变得看似越来越小,当传媒技术足以将灾难的现场在视觉和听觉上带到我们身边,当世界各地发生的不幸都能够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们是否会对不相识的他者产生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同情呢?而这种看似普世的同情心,将指引人们走向无边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抽象的伪道德,不指向任何具体的道德行为,最终让人们在伦理方面成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呢?哲学散文集《无处安放的同情》即是德国作家汉宁·里德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的思索。里德将读者带回18世纪道德哲学的讨论现场,狄德罗笔下“残暴的思考者”、卢梭笔下“捂住耳朵的哲学家”、亚当·斯密虚构出的“富有人性的伦敦人”等悉数登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在道德方面所抱有的不安。这场关于同情心的跨时空大辩论,对解读当下的道德处境颇有裨益。里德是卢梭的忠实粉丝,曾翻译过卢梭全集的德文版,《无处安放的同情》中关于卢梭的文本,是对卢梭思想极好的现代版注解。“无处安放的同情”让我们时时处在焦虑之中,如何摆脱这种情绪,里德并未在书中给出明确答案,不如引用卢梭的一句话:“关键是,我们要对身边人好。”看似简单,却不易做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