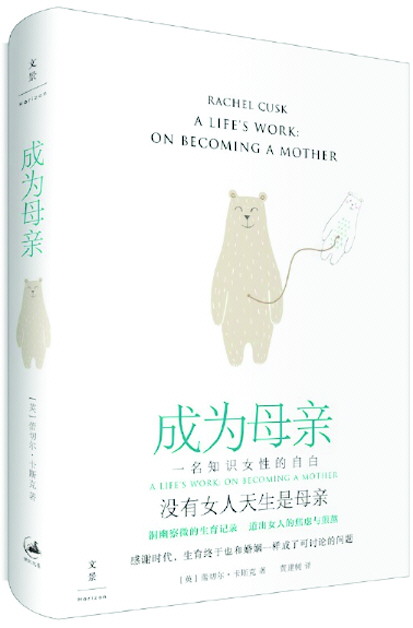今天我们如何做母亲
齐鲁晚报 2020年05月09日
近期引进出版的日韩小说《坡道上的家》《82年生的金智英》聚焦现代女性的处境,其中被“母亲”这一身份绑架了的女人更引发了读者的关注。在《奇葩说》的一期节目中,詹青云说:“妈妈是超人这句话,是在强调和神化母爱的本能。如果强调一个身份的本能,就是在漠视所有个体的付出和牺牲。当一个身份被赋予了神圣感,是不是意味着这类人就要承担着和普通人不同量级的压力?是不是哪个要被赞美、被期待,就必须全力以赴去做好自己的角色?是不是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就是超人应该做的事情?”这一连串拷问,瞬间戳中无数母亲的内心。
“感谢时代,生育终于也和婚姻一样成了可讨论的问题。”在《成为母亲》的书封上有这样一句话。这本书的作者、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生下第一个女儿艾伯丁几个月后,渴望做回当母亲之前的那个自己,那个回不去的自己,她渴望获得自由,生孩子之前她从来没有珍惜过的自由。母性仿佛变成了一座与外部世界隔离开的围城,她想要从里面逃出来。在艾伯丁六个月大时,卡斯克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比起第一次,她不至于那么手足无措,因而也有了余暇去省思。她放弃了逃跑的念头。就是在那时,在那种念头消失之后,卡斯克再次感受到做母亲既真实又奇怪,在怀孕二女儿杰西以及她出生的头几个月里,她写完了这部《成为母亲》。
卡斯克在书中忠实地记录下自己生育期间生理和心理变化,分析“成为母亲”这件事,希望与那些在向母亲转变的过程中饱受折磨的女性沟通,同时也为她们发声。
工作
艾伯丁出生的头六个月,我在家照顾她,我的伴侣则继续上班。这段经历很有说服力,它向我揭示了之前我从未认真考虑过的一件事:孩子出生后,母亲和父亲的生活轨迹便不同了;两人之前地位基本平等,如今却处在了某种彻底敌对的关系之中。
在家照顾孩子和在办公室上班的一天截然不同。不论它们各自有何利弊,这两种生活都有着天壤之别。在我看来,孩子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从最开始便相互对立,此后,男性的统治地位必然愈发牢固:父亲逐渐得到了外界、金钱、权威和名望的保护,而母亲的职权范围则扩展到整个家庭领域。
众所周知,若夫妇双方均有全职工作,母亲一方通常要承担的繁重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远超她们应做的份额,因此,她们必须减少自己的工作时间,以应对孩子会出现的紧急情况。
此议题事关性别政治,但哪怕是在最开明的家庭——我承认我家便是如此——育儿者和工作者之间也存在一道鸿沟。跨越这条鸿沟异常困难。对父亲来说,一种对策是自己待在家而让母亲去工作: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与女性差别如此巨大,并深受保守主义影响,因此也许男人们在照顾孩子时并不觉得自己是伴侣的仆从。然而,几乎没有男性会容忍这种安排可能会给自己事业带来的坏处;言下之意是,能够容忍这一点的男性比大多数同胞更加致力于性别平等,这让他们冒着颜面扫地的风险,同样的风险也让女性做全职母亲的前景暗淡。
父母双方也可以雇奶妈或保育员,然后都去工作,有时候也可以各自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某几天在家带孩子,另外几天去上班。若两人中有一人在家办公,这种模式便会更难操作,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了孩子,像我这样的职业可谓“理想职业”。在家工作的那位在家务活分配上难免会遭到不公正待遇。
还没生孩子时,我曾不动感情、轻松愉快地以为,雇人去专职照顾孩子能解决既工作又当母亲的难题。那时候对我来说,公平似乎便是一切。我不知道怀孕生子的经历对性别平等这一概念有多大的冲击。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人区分开来,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来,于是女性对于存在的意义的理解发生了巨变。她体内存在另一个人,孩子出生后便受她的意识所管辖。孩子在身边时,她做不了自己;孩子不在时她也做不了自己。于是,不管孩子在不在身边,你都觉得很困难。一旦发现这一点,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陷入矛盾之中、无法挽回,或是陷入某种神秘的圈套,你被困在其中,只能不停地做无用的挣扎。
爱
女儿六周大时,某天早上我独自在家,试图让她入睡。我异常疲惫。十小时之内,这也许是我第二十次喂她,并将她放入摇篮。此刻,我不是只想让她睡觉。她必须睡觉,不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的处境突然变得合乎情理起来,非常绝望,且不容置喙。我把她稳稳放入摇篮,然后抽身去了卫生间并关上了门。她在隔壁哭了起来。睡觉去!我一边叫,一边站在她的摇篮前。我之所以大叫,不是因为我觉得她也许会听我的话,而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特别想把她扔到窗外。她异常惊恐地看着我,这是她这辈子头一次坦诚地带着情绪看我。
我向好几个人忏悔了我的行为,可他们都未给予我期待中的那种宽恕。他们说,天啊,宝贝这可怜。他们说的不是我。他们又说,别担心,我猜她会忘掉的。我明白,我只能靠自己来消化我那些过激情绪,我已经失去了爱的庇护。作为母亲,我无法得到他人的谅解。我意识到,这便是所谓的负责任。
若父母的爱是一切爱的蓝图,那它也是一种对于自爱的重新演绎、修订和调查。照顾女儿时,我再次想到了自己的脆弱和与生俱来的无助感。在争吵不休且浪漫的爱的处境中生活了许久以后,仿佛我突然被推下了地下室。我任劳任怨地照顾着宝宝,不惜时间、心情和能力,从不止息养育着宝宝,这一切都被人忽视了。
分离
母亲是我们的故乡:有时,我抱着自己的女儿,试着为了她去理解这种归属感,感受自己的可靠与固执,并捕捉自己的气味、形状和气场。我试着还原她刚出生时的场景。我试着想象有我这样一个母亲到底是种什么滋味。
等我真的这么去做的时候,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笔重要的神秘交易已经在此完成了,就在我家。我提到的交易并非那场将我女儿带到这个世上来的交易:其实是让我成为一名母亲的那个过程。我知道这是我做过的最难的一件事,可我还是担心自己在做这件事时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瑕疵,而且不够可靠,就像一道烧煳了的菜,一张弄得一团糟的画布。
也许只有孩子才能将这种我觉得自己欠缺的意义赋予他们的父母。我不以为意。相反,我认为家庭构造中存在一些固有的保守主义,恰恰是父母将麻烦的领导文化强加给了自己的孩子,因此,孩子一旦自己开始掌权,便会像政客一般,通过确保其艰辛且枯燥的衣钵来扮演他们儿时所惧怕的权威角色。他们忘掉了自己的决心,成了自己曾有过抱怨与抗议的对象。他们尊重自己讨厌过的人。那些曾激怒他们的话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了一种奇特且神秘的宁静感。
我常听人们说,因为自己做了父母,他们真能理解自己的父母了。这种情绪让我很不安,也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仿佛某种错误像疾病被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去。这感觉让我想要容忍我的女儿,直至我的容忍不起作用,因此岁月不会败给误解。我发誓要拥有这种别扭和不真实的感觉。我发誓要结束这种继承关系,结束统治与被统治的历史,就在这里,由我亲自来终结。
(摘编自《成为母亲》,作者蕾切尔·卡斯克,标题为编者所加)
“感谢时代,生育终于也和婚姻一样成了可讨论的问题。”在《成为母亲》的书封上有这样一句话。这本书的作者、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生下第一个女儿艾伯丁几个月后,渴望做回当母亲之前的那个自己,那个回不去的自己,她渴望获得自由,生孩子之前她从来没有珍惜过的自由。母性仿佛变成了一座与外部世界隔离开的围城,她想要从里面逃出来。在艾伯丁六个月大时,卡斯克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比起第一次,她不至于那么手足无措,因而也有了余暇去省思。她放弃了逃跑的念头。就是在那时,在那种念头消失之后,卡斯克再次感受到做母亲既真实又奇怪,在怀孕二女儿杰西以及她出生的头几个月里,她写完了这部《成为母亲》。
卡斯克在书中忠实地记录下自己生育期间生理和心理变化,分析“成为母亲”这件事,希望与那些在向母亲转变的过程中饱受折磨的女性沟通,同时也为她们发声。
工作
艾伯丁出生的头六个月,我在家照顾她,我的伴侣则继续上班。这段经历很有说服力,它向我揭示了之前我从未认真考虑过的一件事:孩子出生后,母亲和父亲的生活轨迹便不同了;两人之前地位基本平等,如今却处在了某种彻底敌对的关系之中。
在家照顾孩子和在办公室上班的一天截然不同。不论它们各自有何利弊,这两种生活都有着天壤之别。在我看来,孩子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从最开始便相互对立,此后,男性的统治地位必然愈发牢固:父亲逐渐得到了外界、金钱、权威和名望的保护,而母亲的职权范围则扩展到整个家庭领域。
众所周知,若夫妇双方均有全职工作,母亲一方通常要承担的繁重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远超她们应做的份额,因此,她们必须减少自己的工作时间,以应对孩子会出现的紧急情况。
此议题事关性别政治,但哪怕是在最开明的家庭——我承认我家便是如此——育儿者和工作者之间也存在一道鸿沟。跨越这条鸿沟异常困难。对父亲来说,一种对策是自己待在家而让母亲去工作: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与女性差别如此巨大,并深受保守主义影响,因此也许男人们在照顾孩子时并不觉得自己是伴侣的仆从。然而,几乎没有男性会容忍这种安排可能会给自己事业带来的坏处;言下之意是,能够容忍这一点的男性比大多数同胞更加致力于性别平等,这让他们冒着颜面扫地的风险,同样的风险也让女性做全职母亲的前景暗淡。
父母双方也可以雇奶妈或保育员,然后都去工作,有时候也可以各自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某几天在家带孩子,另外几天去上班。若两人中有一人在家办公,这种模式便会更难操作,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了孩子,像我这样的职业可谓“理想职业”。在家工作的那位在家务活分配上难免会遭到不公正待遇。
还没生孩子时,我曾不动感情、轻松愉快地以为,雇人去专职照顾孩子能解决既工作又当母亲的难题。那时候对我来说,公平似乎便是一切。我不知道怀孕生子的经历对性别平等这一概念有多大的冲击。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人区分开来,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来,于是女性对于存在的意义的理解发生了巨变。她体内存在另一个人,孩子出生后便受她的意识所管辖。孩子在身边时,她做不了自己;孩子不在时她也做不了自己。于是,不管孩子在不在身边,你都觉得很困难。一旦发现这一点,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陷入矛盾之中、无法挽回,或是陷入某种神秘的圈套,你被困在其中,只能不停地做无用的挣扎。
爱
女儿六周大时,某天早上我独自在家,试图让她入睡。我异常疲惫。十小时之内,这也许是我第二十次喂她,并将她放入摇篮。此刻,我不是只想让她睡觉。她必须睡觉,不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的处境突然变得合乎情理起来,非常绝望,且不容置喙。我把她稳稳放入摇篮,然后抽身去了卫生间并关上了门。她在隔壁哭了起来。睡觉去!我一边叫,一边站在她的摇篮前。我之所以大叫,不是因为我觉得她也许会听我的话,而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特别想把她扔到窗外。她异常惊恐地看着我,这是她这辈子头一次坦诚地带着情绪看我。
我向好几个人忏悔了我的行为,可他们都未给予我期待中的那种宽恕。他们说,天啊,宝贝这可怜。他们说的不是我。他们又说,别担心,我猜她会忘掉的。我明白,我只能靠自己来消化我那些过激情绪,我已经失去了爱的庇护。作为母亲,我无法得到他人的谅解。我意识到,这便是所谓的负责任。
若父母的爱是一切爱的蓝图,那它也是一种对于自爱的重新演绎、修订和调查。照顾女儿时,我再次想到了自己的脆弱和与生俱来的无助感。在争吵不休且浪漫的爱的处境中生活了许久以后,仿佛我突然被推下了地下室。我任劳任怨地照顾着宝宝,不惜时间、心情和能力,从不止息养育着宝宝,这一切都被人忽视了。
分离
母亲是我们的故乡:有时,我抱着自己的女儿,试着为了她去理解这种归属感,感受自己的可靠与固执,并捕捉自己的气味、形状和气场。我试着还原她刚出生时的场景。我试着想象有我这样一个母亲到底是种什么滋味。
等我真的这么去做的时候,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笔重要的神秘交易已经在此完成了,就在我家。我提到的交易并非那场将我女儿带到这个世上来的交易:其实是让我成为一名母亲的那个过程。我知道这是我做过的最难的一件事,可我还是担心自己在做这件事时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瑕疵,而且不够可靠,就像一道烧煳了的菜,一张弄得一团糟的画布。
也许只有孩子才能将这种我觉得自己欠缺的意义赋予他们的父母。我不以为意。相反,我认为家庭构造中存在一些固有的保守主义,恰恰是父母将麻烦的领导文化强加给了自己的孩子,因此,孩子一旦自己开始掌权,便会像政客一般,通过确保其艰辛且枯燥的衣钵来扮演他们儿时所惧怕的权威角色。他们忘掉了自己的决心,成了自己曾有过抱怨与抗议的对象。他们尊重自己讨厌过的人。那些曾激怒他们的话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了一种奇特且神秘的宁静感。
我常听人们说,因为自己做了父母,他们真能理解自己的父母了。这种情绪让我很不安,也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仿佛某种错误像疾病被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去。这感觉让我想要容忍我的女儿,直至我的容忍不起作用,因此岁月不会败给误解。我发誓要拥有这种别扭和不真实的感觉。我发誓要结束这种继承关系,结束统治与被统治的历史,就在这里,由我亲自来终结。
(摘编自《成为母亲》,作者蕾切尔·卡斯克,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