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2年02月04日
作者:
-
 【PDF版】 【PDF版】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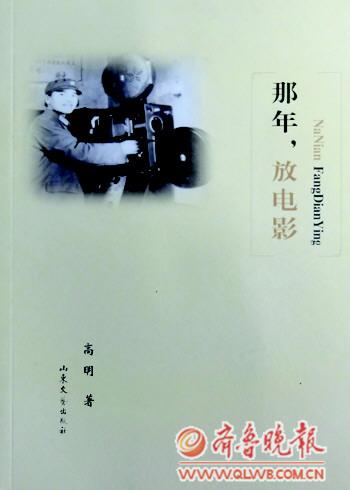 | 《那年,放电影》
高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0年8月出版 |
|
在以往的大历史和单线历史之下,新历史主义力图发掘多元化、个体化、民间化的小历史和复线历史,从而尽可能地、多视域地呈现历史的多样面孔及其复杂表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明的《那年,放电影》以其个体性、民间化的独特生命情感和心灵记忆,为我们呈现了关于历史的鲜活细节和微观现实,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物质和精神存在。
在《那年,放电影》作品集中,高明首先向我们展现了沂蒙“红嫂”的故事和南泥湾的风景。“清明时节,我来到了横河村”,随着作者的叙述视线,我们看到了高明眼中的“红嫂”:“老人满鬓银丝,衣衫完整,精神饱满,正坐着板凳在屋檐下晒太阳”;在南泥湾,作者视线中的风景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窑洞住惯了,上天堂也不去”的老红军。“红嫂”和南泥湾的故事所具有的纪念碑性质,在作者那里转换为一种自在自为的生命本真与温情,别具风格。
《那年,放电影》讲述了作者军旅生涯中难忘的一件事。1974年,担任电影放映员的作者到农村慰问,放映样板戏电影《杜鹃山》,帮忙卸车的老刘等三人是村里的“地富反坏分子”。在交谈中,作者了解到老刘是因为跟大队书记闹过矛盾而被定为坏分子的。电影快要开场了,“银幕被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每个人脸上兴高采烈……人人都巴望着电影早点开场。老刘站在我的旁边,也和村里的人一样在焦急地等待,他搓着手,双眼在如水的月光下闪烁着热切渴望的光芒”。开始放映了,喇叭里传来了大队书记的声音:“社员请注意了,大家热烈欢迎解放军放电影。下面请地富反坏分子退场,电影是慰问解放军战士和贫下中农的,不是给你们地富反坏分子看的。”老刘硬是被拉走了。等精彩电影放完了,村民们散去了,老刘他们三个又出现了,来帮助收拾放映设备。“我低声问老刘:‘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那边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听呢,样板戏真好听。’老刘已摆脱了刚才的负面情绪,沉浸在电影情景里,久久回味。”作者没有再多言,老刘的回答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耐人咀嚼。《卖鸡蛋的小姑娘》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对作者所观照到的“他者”进行叙述之外,高明还把叙述的视角转向了自我家族血脉命运的关注,书写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家族史”文学景观。《父亲的信念》中讲述父亲被错划为“右派”而遭受批斗、无休止学习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1979年父亲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彻底平反。“那天,我喜极而泣,竟约战友们喝了个酩酊大醉。”从父亲的人生世界里,作者发现“父亲的血液里,蕴含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无尽的热爱,任何艰难坎坷、曲折反复,都压抑不住,即使在最不堪的境地,也始终放射出矢志不渝、无怨无悔的光芒”,“觉悟出,该怎样像父亲一样做父亲”。
《那年,放电影》里面还有很多这样感人肺腑的作品。高明没有用华丽的词藻,没有用过多的修饰,而是以一种极为简约、质朴的语言,像跟朋友、亲人絮语一般,讲述来自生命历程中亲观、亲闻、亲历的人和事,达到了以简约胜繁复、以质朴达崇高、于无声处惊人的叙事效果。作品中有很多环境或人物形象的白描勾勒片段,看似质朴无华,而读起来非常耐人寻味,细细咂摸,意蕴丰富,大大超出了一般的回忆性散文。这正是大历史之下个人化、民间化的小历史——个体心灵史的独特魅力所在,因为亲历而充满澎湃的生命激情,因为亲历而具有了不被风化和挪移的生命真实。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