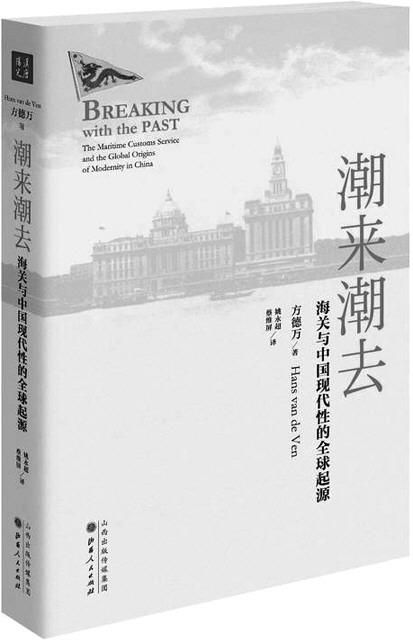普鲁士外交使团随团画家手绘的1861年上海江海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由于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尚在英国,因此海关事务暂时由总务科秘书日籍税务司岸本广吉代理。在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要求下,岸本广吉对海关全体职员发布了抵抗自己日本同胞的命令。
如果站在民族感情立场上,极易误解岸本广吉的行为,事实上岸本广吉后来进入汪伪政府担任了所谓的“总税务司”。而如果将这件事置于近代海关的大背景下不难发现,岸本广吉的所作所为也有其合理性,因为他是中国海关的一名职员。
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现代史教授方德万通过梳理近代中国海关历史发现,从1854年到1949年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海关就像是一个“边界政权”,其对于中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同时也是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这个边界政权有自己的一套制度、规则、实践、官职以及在边界监管货物交易、船只往返、人员进出的规程”,另一方面,“它自身还是一个在边界地带的‘王国’:它是一个‘国中之国’”,“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特征的行政机构,它有自身的结构、气质、团队精神、传统、政策、章程和法规,独立的武装力量以及一套独特的外交。”
撕掉洋人掌舵初衷的
“遮羞布”
提起中国近代由外国人掌舵近百年的海关,常见一些媒体反复提及海关的廉洁与高效,认为这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这是事实,但也极易导致另一种错觉,即把近代海关创设初衷想象成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服务的机构。
打捞历史不难发现,用廉洁与高效的解释为近代海关创立的正当性开脱,多少有点“一俊遮百丑”,或者说像是近代由“洋大人”牢牢把持海关正当性的一块“遮羞布”。在历史发展问题上,没有人先知先觉。当初,谁也无法预见海关在外国人的管理下未来一定能够实现廉洁与高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方德万笔下对于新海关创设初衷的正当性语焉不详。
1853年,小刀会攻占上海,清朝海关骤然停摆。在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的积极倡导下,英、法、美联合成立了新的江海关。1854年7月,江海关在苏州河北岸挂牌办公,22岁的英国驻沪副领事李泰国走马上任英籍税务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通商口岸增加到15个,迫于国际国内形势,清朝同意将江海关的职能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委任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统领各口岸新设海关”。
从江海关的诞生初衷看,显然并非出于捍卫中国的根本利益。相反,只是阿礼国等代表外国利益的欧美领事们担心失去必要管理后,上海边境贸易走向混乱,各国商船间可能因此产生无序乃至恶性竞争。
如果说成立新的江海关只是英美法三国一时的权宜之计,那么,当清朝有能力恢复海关职能时,按理他们当及时奉还,同时一并归还代收税款。然而,当身兼江海关监督职务的上海道台吴健彰试图收回上海海关职权时,却遭到英美等国的百般阻挠,最终流产。待洋人掌舵的新江海关成为既成事实,而清廷不得不屈服后,英美两国仍旧没有如实上缴税款:美国只缴了代收税款的三分之一,英国更是直接宣布此前代收的支票作废。
新江海关诞生后,除了进一步扩充管辖范围外,其对权力的垂涎本色毕显。总税务司李泰国希望建设一支美其名曰的“英中联合舰队”,即中国出钱,英国出人,但舰队由他本人指挥掌控。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只能当“冤大头”。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舰队对饱受列强军事欺凌的清朝而言,无异于又多了一道时时均可被兴师问罪的风险。
再者,在近代海关历史上,外国人始终绝对霸占中上层领导权,薪资待遇更是中外差别巨大。澳大利亚人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在1894年沿长江溯流而上后写道:长江沿岸各海关税务司之中,上海的是一名奥地利人,九江的是一名法国人,汉口的是一名英国人,宜昌的是一名北欧人,重庆的是一名德国人。
有一点或无疑问,当外国人牢牢掌握了海关的领导权,无异于死死控制住了话语权。
被历史推动的现代化
自1854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海关先后经历了李泰国、赫德、裴式楷、安格联、梅乐和、李度六任总税务司,其中对中国近代海关影响最大的当数任职长达48年的赫德。
赫德是李泰国的继任者,有别于李泰国对中国人的不屑与傲慢,赫德在中国接受语言训练和与中国女子阿姚结合的经历,显然更利于他对中国国情与国民习惯的更深了解。
接手海关事务后的赫德,不是像李泰国那样挖空心思拓展势力范围,而是专注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现代化海关队伍。赫德在伦敦设立办事处,招贤纳士。“它的国际化的招聘政策,(还)让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和其他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精英们觉得,让海关运作下去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赫德将英国海关的管理模式导入中国,“制订了规范的用人制度,严密的会计、统计、稽查、复核等业务程序,以及年终层层密报等制度,加上合理的薪酬福利等等,使中国海关成为清朝唯一高效廉洁的衙门”。
廉洁高效的海关队伍,使得海关税收实现快速增长。“从1865年到1875年,海关岁入由白银830万两稳步增加到1200万两,1885年更增至1450万两;而当时的账面岁入不过银6000万两左右,洋税已占近20%”。到了1911年,海关税收有长达20年已经占据清政府总税收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赫德并未满足于单一的征税,从1868年起,他还带领海关着眼于提升海运服务功能,即开始建设灯塔、设置航标、竖起信标、管理港口、提供气象资料等,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
海关在与国际快速接轨的同时,也利用自身优势,努力推动闭关自守的清朝打开视野,甚至走出国门。除了在义和团期间促成清朝与八国联军的谈判,避免中国被瓜分,海关还资助使臣出访,其中就包括1896年3月18日—10月3日,李鸿章历时190天,横跨三大洋,对欧美8个国家的出访。方德万认为,正是因此,海关“把中国带入一个由主权民族国家和跨国系组织所建构的新世界外交秩序”。
相较于前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居高临下不断威逼清政府,赫德更像是一个问题解决专家,不断给火烧眉毛的清政府雪中送炭。没有比赔款更令清廷焦头烂额的了,“1895年后,海关深深地涉入中国的外债事物”,如《马关条约》赔款和庚子赔款,后来还积极介入民国善后大借款和内债等事务。
赫德之所以能够取得空前影响,与其说是时势造英雄,不如说赫德充分利用了海关的特殊身份,即“面对清海关监督时,他可以直接越过他们,向北京的总理衙门反映;面对外籍领事时,他又可以越过他们,直接诉诸在英国的政治核心”。有直达“天庭”的尚方宝剑,自然不必畏惧下面那些难缠的“小鬼”。也正是因为推动中国海关努力与国际接轨,同时尽可能促使闭关自守的清朝官员走出国门,熟悉国际规则,所以海关没有“被视为只是某个强国的工具,而是被认为对所有国家都十分有用——这当然也包括清朝在内”。
勿被“光芒”遮望眼
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年代,海关职能之所以没有中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外国势力的这道护身符。毫无疑问,海关在自身建设和推动清朝与国际接触对话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不能不说的是,“当海关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掌握了关税和相关港口收费的征收权后,便变成了为外国财政利益和庚子赔款债权国服务的国际公共收债代理机构”。海关管辖范围一再扩充,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贷款超过了海关的预期税收,所以不得不把其他行政控制权也转交海关,其中包括了大的厘金、盐务稽核所,以及邻近50里内的常关”,本质上还是为了提高借债和偿债能力。
众所周知,国人争取海关主权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1895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否定了海关“中国人很难避免腐败”的论调,并主张“海关是国家主权很重要的一部分”。清朝势力最大的两位封疆大吏张之洞和刘坤一也对由洋人把持的海关多有不满。
虽然海关表现了廉洁高效的一面,但在历史关键时刻,代表外国资本家利益的海关便会露出尾巴。方德万指出,之所以是袁世凯而非孙中山赢得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伦敦的银行家们(首推汇丰银行的查尔斯·艾迪斯)相信袁世凯比孙中山更值得信赖”。也因此,“辛亥革命第三天,安格联就命令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想办法将海关税款转入汇丰银行”。
这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应因为近代海关取得了一些成绩,至而认为这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近代海关的发展历史充分表明,其在确保与外国领事和商人保持顺畅沟通的同时,实际上也让渡了诸多利益。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海关之所以能够因为廉洁而被誉为“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很重要的一条便是高薪养廉。但这种养廉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限于上层结构即外国人把持的那些重要岗位。
相较而言,中下层岗位薪水低得多,管理也是漏洞百出,只是不被重视。比如前文提到的莫理循在行走笔记中就曾对底层海关人员吃拿卡要现象深恶痛绝。由于历史信息的缺失,无法判断那些拿着优厚报酬的外国管理人员到底是深入不够,从而对下面这些“微腐败”完全不知,还是原就存在利益输送链条,上下本来就是沆瀣一气。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