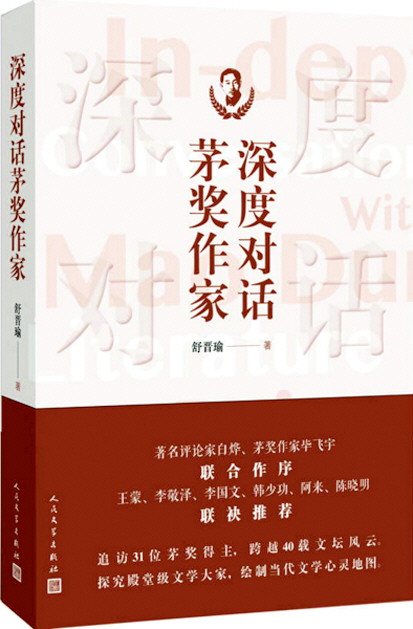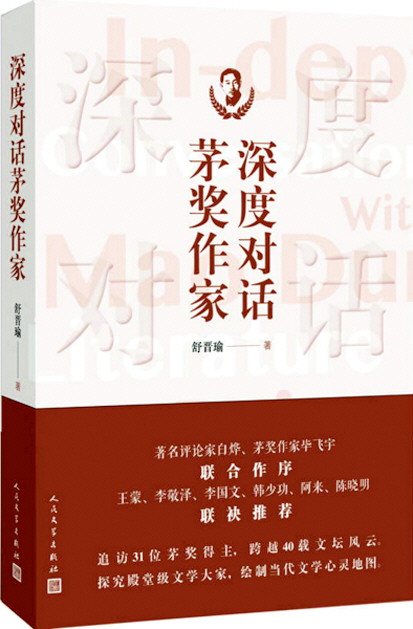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舒晋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是中华读书报著名文学记者舒晋瑜的第三部访谈专著。我一听说书名,立即被“深度”二字吸引住了。待读了该书,更加认可这两个字。
舒晋瑜虽然在访谈中没有提过“文学哲学”这个词儿,却贯串了文学哲学的路径,以她特有的执着,深厚的素养,秀和的风貌,不断向作家们叩问着“为什么”。
她向写出《白鹿原》的大作家陈忠实发问:为什么要在开篇引用了巴尔扎克关于“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话,“这是不是也体现了您的一种创作野心”?
陈忠实作为一位史诗性的大作家恰好喜欢这种追问,回答中承认自己在最初构思时,就是在索问中国这个“有着特殊记忆的民族,他们怎样脱下长袍?为什么要脱下长袍?他们怎样剪去那长长的辫子?为什么要剪去那长长的辫子?”
舒晋瑜紧接着得出了结论:正是在这种追问性的构思和主人公白嘉轩娶了六个老婆都死了的故事架构中,呈现出《白鹿原》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极具史诗气魄的大手笔”。
这就是富有历史哲学和文学哲学的对话,这些追问“为什么”的对话在书中随处可见,所以使这部书达到了少见的“深度”。
既是文学访谈,当然要突出文学性。舒晋瑜与毕飞宇的对话正是在探究文学的“之所以然”。
毕飞宇在我心目中是极具艺术品质、最懂得文学的当代作家,他最好的作品是《平原》,并不是获得茅奖的《推拿》。这可能与评奖的时间性有关。舒晋瑜似乎跟我的艺术感觉相通,问毕飞宇道:“以往获得茅奖的作品,多是宏大叙事,但《推拿》不算是。”
这样一问,引出了毕飞宇极为精辟的回答:“我非常热爱宏大,但问题是对宏大的理解可能不一样。所谓史诗模式是宏大,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小的,跟叙事者内心的宏大几乎无关,真正的宏大是留在人物的内部。内部的宏大是非常惊人的。”“从我写作开始,兴奋点就在内部而不是外部。写一个小说,写战争,写来写去都是外部不涉内心、不涉及感受,对我来说不可想象。王安忆评价迟子建的时候,说:‘她知道小说在哪儿。’这个话说得特别好,每个人都有一个判断,每个写作的人都知道‘在哪儿’,因为这个判断,导致每个作家不一样,我所理解的宏大,永远在内部。”
“知道小说在哪儿”这个说得特别好的话,其实就是懂得文学。文学在哪儿?就在人的心里。题材再大,写世界大战,写了很多战争过程,却没有写战争中人的心理活动和人生感受、曲折命运。就不算文学!因为文学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军事战术学,而是要生动、深刻、鲜活地写人,写人的心灵,是由语言构成的人与心的形象画。这实质是文学哲学最根本的课题。很多搞了一辈子文学的人,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始终懵懵懂懂,弄不清楚,到死还在概念化的泥淖里瞎折腾。虽然其中有人著作等身,声名显赫,但到头来不过留下一堆垃圾。最后,烟消云散,除了做反面教材之外,一点儿痕迹都留不下。
王安忆与舒晋瑜的对话题目是“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我无法归纳成概念”。正是真正懂文学的文学家说出的真理:文学与概念无缘。
一位哲人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理解了文学的“之所以然”,为什么是如此的,不是如彼的?究竟是什么,究竟在哪儿?才能实现文学的自觉。王安忆、迟子建和毕飞宇都应该归属这一类作家,而舒晋瑜能够和她(他)们对话,就因为她也属于这一类懂得文学“在哪儿”的记者和作家。这部《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对文学的理解达到了惊人的“深度”,是懂文学的人之间的对话。
“深度”不是因为你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也不是因为你的问题多么锋芒毕露,而是说,你具有充足底气、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能引发作家的深度思考,拓展相关的话题。舒晋瑜面对采访对象,都怀有尊重和深入的理解并善于提出问题。所以她也同样受到这些一流大作家们的敬重与欢迎。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