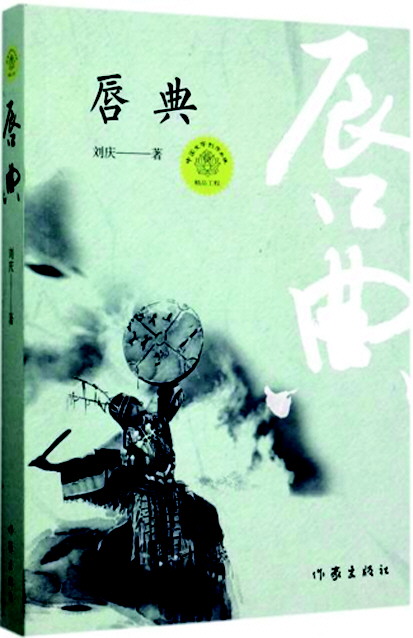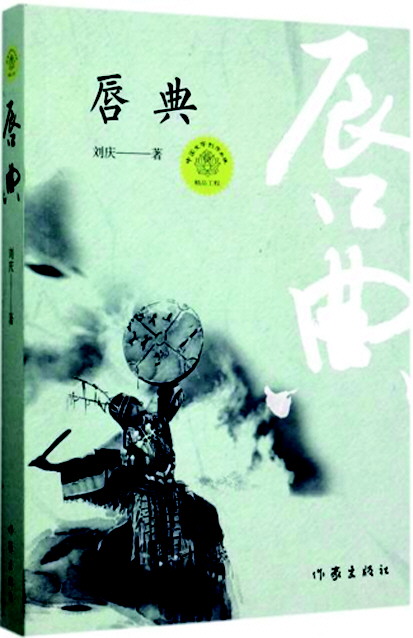
《唇典》
刘庆 著
作家出版社
9月20日,第七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作家刘庆凭借长篇小说《唇典》获得首奖。《唇典》是刘庆历时十年完成的一部54万字的长篇小说,现场答谢时他谈道:“文明撒下了许多智慧的种子,有许多种子被风吹到了河里和海里,有的落在了沙石地上,茂盛地开放的种子是最幸运的。《唇典》是幸运的那一粒种子,我希望它能够种进人心,茁壮成长。”
我习惯在一部作品开始时写下时间。《唇典》写下第一行的时间是2005年2月18日22:03,我在2015年9月3日上午10:26写完最后一行。《唇典》的创作竟然历时十年。我从未想过这部书会耗费我十年的时间,十年太漫长了,在我的认知里,只有曹雪芹的《红楼梦》才配得上这么长时间的写作。
《唇典》的构思比写作还早五年。2000年12月10日,当时我是一张都市报主管新闻的副总编辑,夜班编辑提交的一条新华社的简讯引起了我的注意。简讯说,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在吉林省的森林山。我将这条新闻定发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问题来了,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市的地图上,我们找不到森林山。于是,我签发了第二篇稿件,发动读者寻找森林山。一位热心的读者在一张军用地图上找到了森林山的位置,那个地方叫做老爷岭。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策划迎接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报道,报社派出几路记者去珲春老爷岭采访。当时有一个特稿记者阿芒采写了两篇报道,刊发时题目是《生生死死森林山》。故事由一个满族老人郎傻子自述,森林山是一个传奇的地方,是满族的分支库雅拉满族的生长地,珲春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老人讲述了他和土匪阿玛白五爷、朝鲜额娘和俄国额娘的故事。
坦率地讲,我并不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我怀疑郎傻子是一个有讲故事天才的老人。东北的乡下,有许多这样的人,我小时候村子里常常供电不足,没有电的漫漫长夜,总有人绘声绘色地讲一个极有可能是他自己吹牛的故事,我就听说过一个人骑着野猪打野猪,讲故事的人又矮又小,讲话时脸上的麻子坑都闪闪发亮,听故事的人抽着烟袋锅,一听一乐并不认真。郎傻子可能也是这样的人,他编造了自己的传奇故事。我还怀疑里边有记者阿芒参与编造的成分。但故事实在太吸引人了,引起了我创作的冲动。我向阿芒要了电话,决定利用元旦休息的时间亲自去见一见郎傻子。我做好了进山的一切准备,买了很厚的羽绒服,还有大棉鞋。
2000年12月26日,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唇典”两个字。我觉得这两个字会成为一本好书的名字,为了这个书名我兴奋了好久。唇典的原意是东北土匪的“黑话”,比如”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之类,但我将其引申为口口相传,唇典——口口相传的民族史,民间史,既贴切又传神。在商业文化浸淫的今天,有多少民族化个性化的东西兑进了三聚氰胺和工业糖精,或者归入故纸堆腐烂消亡,或被历史和记忆彻底抹杀。我一定要让真正的“唇典”发扬光大,使其源远流长。
12月31日,我值了一夜的夜班,感到深深的疲惫,觉得自己没有了踏上旅途的力量,我更需要的是睡眠和休息,我迷迷糊糊地回家了,放弃了去珲春采访的打算。
2004年初,右腿莫名的疼痛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这样的日子长达大半年,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只有写作才能让我获得一些快乐。《唇典》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候,我重新想起了那位珲春森林山的故事大王,几次试图联系那位姓郎的老人都没有结果,而采访郎傻子的记者阿芒两年前被人杀死在住处的走廊里。
长篇小说的写作真是一种冒险,最初的时候,仅仅是一个火花,照亮了你的心灵,在笔尖和键盘上熠熠生辉,你高兴你捕捉到了它。然后,你中招了,你不得不用两手将那火花捧在手心里,而你的四周长风呼啸。又像一个大风夜室外的一点烛火,随时都会被风吹灭。一堆柴草点燃了,浓烟滚滚,呛你的嗓子,熏你的眼睛。风越来越大,这堆无用的柴草根本无法战胜黑暗,温暖不了你的手脚。可是这堆火已经点燃了,要么你任由它熄灭,要么你让它燃烧起来。写作的过程总是细若游丝,随时断掉的光景。这是一次你无法回头的冒险,你已经投入了几年的经历,船在水中浸淫已久,波掀浪涌,随时可能倾覆。冰冷,要靠更多一点希望来点燃。绝望,要靠无望的对抗来战胜。要么前功尽弃,要么去争取完成。我常常问自己,你的自信心足吗?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
写作时间长还有一个好处,随着你自己的认识,甚至是年龄的变化,还有你阅读量的增加,你的故事会更厚重,思考也会更深入。我将我能找到的关于萨满教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去研究东北史和抗联史,向专家求教,我对史料的认知有时让专家们惊讶。我尽我最大的努力要让小说有“烟火气”,我要还原故事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设身处地地去想象人物的思想意志和行为。我发现我不再着急了,对自己的写作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小说的指向也更清晰。
许多朋友看过我的生活状态,他们说无法想象我怎么能写成一部数十万字的书。是啊,除了对文学的热爱和坚持,还有什么理由呢?文明撒下了许多幸运和智慧的种子,有许多种子被风吹到了河海里,有的落在了沙石地上,茂盛地开放的种子是最幸运的。我希望《唇典》是幸运的那一粒种子,能够种进人心,茁壮成长。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