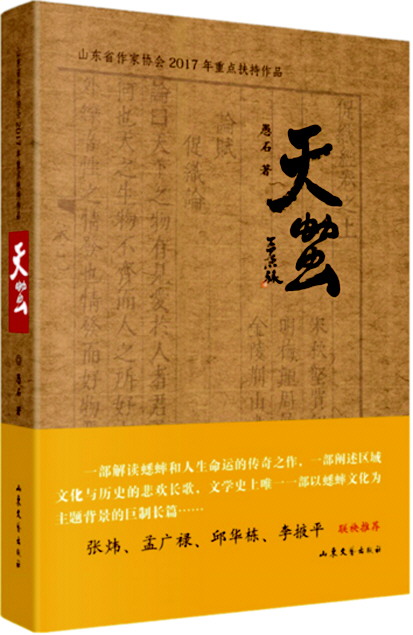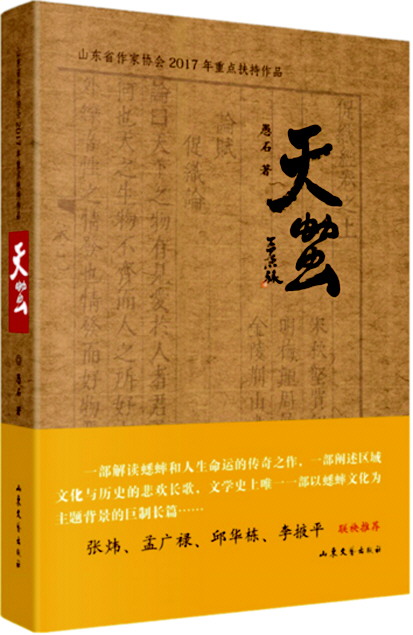
《天虫》
愚石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泰安宁阳是蟋蟀的主产地,全国各地的蟋蟀爱好者都把宁阳作为“蟋蟀王国”。近日,宁阳籍作家愚石推出一部解读蟋蟀和人生命运的传奇之作《天虫》,通过主人公“油爷”生死悲欢的命运,铺陈了一段乡土历史,展示了独到别致的蟋蟀文化。
2016年的5月17日,阳光和我一起穿过弯曲的山路,居于凤凰山下一间不足十个平方米的木屋,我开始了《天虫》的创作。下半年又有近二十天的时间,从小木屋搬到了临近的宽敞明亮的朋友正房内,一边写作,一边体验秋到山涧的阴晴风景。两次闭关写作近两个月的时间,于公务、琐事缠身的人来说,确实不易。但更多的难,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在写作过程中的殚精竭虑。虽然动笔之前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准备,但在情节与人物的塑造、取舍、结构上,仍然几乎耗尽了所有体能和智力。
这段独处的日子,我是不计晨昏的。床与书桌只有一个翻身的距离,随手即可打开的台灯,穿透深山的黝黑,我甚至能听到光亮落到黑暗中的声响。但有时,即使折身起床,想写的文字也会一散而光,便一个人来到房间外的黑暗中,想象哪块石头是草木的前世,哪一声鸣唱是蟋蟀的魂灵。我在自然风声、雨声、万籁之声的交汇处,以万物为镜,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和创作灵感的闪光处。写作的步履蹒跚沉重,我试图发现灵魂的真相并与之结为同盟,打开蜷曲在心中全部的僵硬的绳索,唤醒一条条通往神秘的花园或者炼狱的路径,沉醉于内心的每一次冥想与苦渡,寻找与《天虫》契合的心境与语调。
以虫写人,以虫喻人,是小说的创作基调。《天虫》是人的悲欢史,是“虫”的兴衰史,也是民族命运的衍变史。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我该如何厘清传统的文化偏执与道德偏见对蟋蟀文化的戕害,如何写清楚蟋蟀的习性和灵魂,以及它们与主人们的恩怨,与世间万物的互动与感应。这绝世的精灵,美得可以与任何一首诗比拟,《诗经》中说:“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人有天道遵循,虫有自在歌咏,这不就是诗意栖息的美景吗?陆机一句“朗月照闲房。蟋蟀吟户庭”,写出清静与幽鸣;白居易“蟋蟀啼相应,鸳鸯宿不孤”,写出爱恋与缠绵;李白“蟏蛸结思幽,蟋蟀伤褊浅”,道出幽怨与伤感;杜甫一首“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写出痴情蟋蟀的爱情浪漫……
从诗歌中走来的蟋蟀,在时空无尽的笔墨中像一只精灵,从来都是讴歌者的梦幻情缘。然而更多的人,因为诸多的历史缘由,对蟋蟀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文化现象,经常放置于玩物丧志的道德批判场,这也是《天虫》的主人公油爷必须面对的家庭和社会氛围。所以油爷诘问,俗称“八艺”的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既然统称为“艺”,难道“艺”还分贵贱高低?为何偏偏“虫”就比琴或画低贱几分?因为蟋蟀宰相贾似道的奸佞误国而“迁怒”于一只蟋蟀,成为文化史上的最大冤案。说到底,一只蟋蟀承担不起家国荣辱,它只是自然生灵,像一棵树、一朵花、一缕轻风、半湖烟雨一样平常无奇。奇的是它可以像驰骋于疆场的勇士,体现出忠、勇、信、知耻辱、守时节的“五德”情操;可以成为大自然中最美的歌手,唱出无数音律不同、含义不同、情感不同的曲调;更可以作为旷野间最后的骑士,为自己心爱的女人,不计生死地搏杀……所以油爷才在书中一遍遍地说:“如果这个世界有谁像一只蟋蟀一样正直,那他简直比神还伟大。可谁能做得到呢?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像蛐蛐一样正直,那这个世界就不再需要上帝和佛祖。”
由此以观,虫比人高,不仅仅是一个命题,更成为一种真相。一虫一世界,一曲一乾坤,究竟有几个人能听得懂蟋蟀的心事,看得清它的喜怒哀乐?蟋蟀从卵到虫,要蜕七次皮,并且要面对蛇、青蛙、黄鼠狼、鸟等天敌。成虫之后,蟋蟀只能存活一百天,即使它天天歌唱,我们能听到几声?如果再把人类的道德束律强加于一只蟋蟀身上,是否符合自然法道?对这些问题,《天虫》给不出答案,因为“油爷”只是蟋蟀的痴迷者,而我,也只是问题的提出者罢了。
在上一部长篇《人子,人》创作之时,我曾在一湖边借住。某日,眼见着一条闪着光的鱼穿破水浪,不顾一切地向我游来,让立于岸边的我激动不已。尤其在鱼游到离我只有咫尺的小小的水湾,任由我打捞之后,我更觉得这是上苍送给我的礼物,是慰藉辛劳的上上之品。兴奋之后,由食堂师傅做了鱼汤。问及鱼儿为何从水深处游到岸边,师傅告诉我,这鱼应是受了伤,生不如死,它游向岸边,就是赴死的。胸中一阵疼痛闪过,“游命的鱼”几个字突然冒了出来,不是游生,而是赴死。有这样勇气和姿态的鱼,该是承受不起怎样的痛苦,又是否经过多少纠缠和挣扎,我不得而知。自此以后,为这条鱼写点什么的念头一直提醒着我,但我始终未能动笔,因为我自己,又何尝不是那条游命的鱼呢?包括小说的主人公油爷,与生活在漩流中的无数世人,又有什么样的分别?
人的一生,会面临着无数次的选择。选择之后的生命历程,往往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由此,“向难而生”不仅仅是励志之语,更是每个人以不同的姿势“游命”的生存境况。如同在我选择要把《天虫》当作创作的极顶去努力攀登的时候,我已经赌上了多年的创作经验和深厚积累。
在天为龙,在地为虫,是为蟋蟀。《天虫》中的“油爷”说:“蛐蛐有千年万年的轮回,人,只有瞬间的花开。”爱一只虫,又何尝不是悲悯我们自己。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