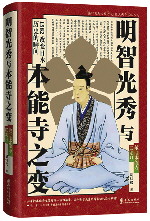跨越400多年的“本能寺之变”
齐鲁晚报 2022年09月03日
□胡炜权
笔者在今年跟华文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本书是利用各种史料,分析一起发生在1582年夏天的政治事件——本能寺之变的经过和原因。发动事变的是日本人家喻户晓的“著名犯人”明智光秀,被他杀害的则是更为有名的日本历史人物织田信长。由于明智光秀直至死去也没有交代犯案动机等细节,因此这场改变日本历史走向的事变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史三大谜团之首(其余两个是“邪马台国的位置在哪里”和“谁是暗杀坂本龙马的主谋”)。
本书是笔者在2017年于台湾省出版的同名书籍简体中文版,在此基础上增补六万字的新内容。这不仅是为了更新知识和补充旧版的不足,同时也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容易理解背景知识。特别是最后,增设了九个“本能寺之变”相关史料的中文翻译,以方便读者了解事变发生后的日本人如何理解和传播事变的来龙去脉。
顺带一提,《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虽然是在2017年首次出版,但早在笔者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便已经开始写作,并在一年半后完成底稿。随后因为在日本攻读硕士学位,有好几年没有时间处理书稿,这一放就是十年。后来,笔者到日本国立一桥大学攻读日本史博士学位期间,才得以再次把书稿拿出来修订,经朋友引荐,出版成书。在这段漫长的研究过程中,除了对事件有了更多、更深的理解,笔者还通过梳理“本能寺之变”的研究史,发现日本人对于疑案、阴谋抱有极为强烈的好奇心和执着,更成为他们对历史的独特观感和态度,而这种历史观至今依然存在。
相信不少读者都看过日本的推理小说,或者是《名侦探柯南》《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等以推理为题材的日本漫画。曾经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推理题材,从小说到漫画,换个包装,反复推出市场?
笔者曾在攻读硕博学位期间参加过各种日本本土文化的考察团,以及民俗学的学术活动。出于自身的研究需要,笔者也曾走访一些日本乡间地区,通过跟不同世代的村民交谈,感觉到日本人对于不可解、不能说明的事情充满了好奇心,而且热衷于讨论各种可能性,这有点像我们在网络上遇到各种未解决的事件时,自然而然地做出各种猜想和推测,这种好奇心可以说是人类共有的本能之一。
当然,作为日本历史的研究者,笔者还是有必要以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和分析“日本人的精神史”。笔者曾统计过自古至今,日本人就“本能寺之变”的所谓“真相”提出了数十种说法。比起历史真相,他们更享受在无法肯定真假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推理力,得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看法;或者寻找其他人的见解,从中获得满足感。
换句话说,日本人对于事情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不是特别在乎,他们反而更珍惜利用这些机会,享受在“历史探案”游戏之中的快乐。
日本著名民俗学者柳田国男和折口信夫都谈到过日本的推理解谜小说可以追溯到日本江户时代(17世纪—19世纪中期),日本识字率和印刷技术极速发展,大量读物涌现,同时也刺激了创作欲望和市场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期日本解谜文学热潮的其中一个源流,跟当时日本商人从中国(清朝)输入的文学作品有关。柳田国男曾经推测,其中一个关键作品就是宋人桂万荣的《棠阴比事》。这部以作者整理的古今公案判例为题材的作品,自17世纪初引进日本后大受欢迎,在元禄时代以后还催生出各种受其启发的本土衍生作品,一直延续到明治大正时代。
除了外在的影响,非常多的日本古典作品都蕴含了为血亲、挚友报仇雪恨,或是为自己挽回名誉而报复的情节。更重要的是,日本自古以来奉行“自力救济”主义,即“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而且执着地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获得保障。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日本各个时代政权的统治者均没能做到将权力渗透到社会底层,依然保留着比较松散的分权体制,因此,律法和司法因地而异,没有一个绝对稳定的标准和守护者,且统治者对于维护正义和介入民间纷争的态度显得很消极,结果形成了遇到纠纷、困难的当事人都得靠自己和身边的亲友同道去实现“正义”,以保护“正义”及其背后的权益能够长久地获得保障。
这种历史背景对日本人评价本能寺之变以及其他历史事件的角度和感受也是息息相关的。明智光秀发动“本能寺之变”,杀害主君织田信长,因此在封建时代背负上弑君犯上的骂名。但这不过是统治阶层的视角,当时的平民百姓并不这样理解,各处跟他有关系的地方纷纷举办活动纪念他,并且延续至今。
在当今日本人的心目中,明智光秀并非违背道德的恶人,反而各种脑补和辩护随处可见,如“信长也不是好人”“光秀必定有难言之隐”等等。“本能寺之变”能够跨越400多年,至今依然是日本人十分关心的话题,而且只要新闻报道说发现一些新线索,就立刻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各位读者如果有兴趣阅读《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这本书,特别是后半部分内容,就能跟笔者一样,感受到日本人这种独特的心性了。
笔者在今年跟华文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本书是利用各种史料,分析一起发生在1582年夏天的政治事件——本能寺之变的经过和原因。发动事变的是日本人家喻户晓的“著名犯人”明智光秀,被他杀害的则是更为有名的日本历史人物织田信长。由于明智光秀直至死去也没有交代犯案动机等细节,因此这场改变日本历史走向的事变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史三大谜团之首(其余两个是“邪马台国的位置在哪里”和“谁是暗杀坂本龙马的主谋”)。
本书是笔者在2017年于台湾省出版的同名书籍简体中文版,在此基础上增补六万字的新内容。这不仅是为了更新知识和补充旧版的不足,同时也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容易理解背景知识。特别是最后,增设了九个“本能寺之变”相关史料的中文翻译,以方便读者了解事变发生后的日本人如何理解和传播事变的来龙去脉。
顺带一提,《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虽然是在2017年首次出版,但早在笔者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便已经开始写作,并在一年半后完成底稿。随后因为在日本攻读硕士学位,有好几年没有时间处理书稿,这一放就是十年。后来,笔者到日本国立一桥大学攻读日本史博士学位期间,才得以再次把书稿拿出来修订,经朋友引荐,出版成书。在这段漫长的研究过程中,除了对事件有了更多、更深的理解,笔者还通过梳理“本能寺之变”的研究史,发现日本人对于疑案、阴谋抱有极为强烈的好奇心和执着,更成为他们对历史的独特观感和态度,而这种历史观至今依然存在。
相信不少读者都看过日本的推理小说,或者是《名侦探柯南》《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等以推理为题材的日本漫画。曾经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推理题材,从小说到漫画,换个包装,反复推出市场?
笔者曾在攻读硕博学位期间参加过各种日本本土文化的考察团,以及民俗学的学术活动。出于自身的研究需要,笔者也曾走访一些日本乡间地区,通过跟不同世代的村民交谈,感觉到日本人对于不可解、不能说明的事情充满了好奇心,而且热衷于讨论各种可能性,这有点像我们在网络上遇到各种未解决的事件时,自然而然地做出各种猜想和推测,这种好奇心可以说是人类共有的本能之一。
当然,作为日本历史的研究者,笔者还是有必要以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和分析“日本人的精神史”。笔者曾统计过自古至今,日本人就“本能寺之变”的所谓“真相”提出了数十种说法。比起历史真相,他们更享受在无法肯定真假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推理力,得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看法;或者寻找其他人的见解,从中获得满足感。
换句话说,日本人对于事情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不是特别在乎,他们反而更珍惜利用这些机会,享受在“历史探案”游戏之中的快乐。
日本著名民俗学者柳田国男和折口信夫都谈到过日本的推理解谜小说可以追溯到日本江户时代(17世纪—19世纪中期),日本识字率和印刷技术极速发展,大量读物涌现,同时也刺激了创作欲望和市场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期日本解谜文学热潮的其中一个源流,跟当时日本商人从中国(清朝)输入的文学作品有关。柳田国男曾经推测,其中一个关键作品就是宋人桂万荣的《棠阴比事》。这部以作者整理的古今公案判例为题材的作品,自17世纪初引进日本后大受欢迎,在元禄时代以后还催生出各种受其启发的本土衍生作品,一直延续到明治大正时代。
除了外在的影响,非常多的日本古典作品都蕴含了为血亲、挚友报仇雪恨,或是为自己挽回名誉而报复的情节。更重要的是,日本自古以来奉行“自力救济”主义,即“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而且执着地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获得保障。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日本各个时代政权的统治者均没能做到将权力渗透到社会底层,依然保留着比较松散的分权体制,因此,律法和司法因地而异,没有一个绝对稳定的标准和守护者,且统治者对于维护正义和介入民间纷争的态度显得很消极,结果形成了遇到纠纷、困难的当事人都得靠自己和身边的亲友同道去实现“正义”,以保护“正义”及其背后的权益能够长久地获得保障。
这种历史背景对日本人评价本能寺之变以及其他历史事件的角度和感受也是息息相关的。明智光秀发动“本能寺之变”,杀害主君织田信长,因此在封建时代背负上弑君犯上的骂名。但这不过是统治阶层的视角,当时的平民百姓并不这样理解,各处跟他有关系的地方纷纷举办活动纪念他,并且延续至今。
在当今日本人的心目中,明智光秀并非违背道德的恶人,反而各种脑补和辩护随处可见,如“信长也不是好人”“光秀必定有难言之隐”等等。“本能寺之变”能够跨越400多年,至今依然是日本人十分关心的话题,而且只要新闻报道说发现一些新线索,就立刻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各位读者如果有兴趣阅读《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这本书,特别是后半部分内容,就能跟笔者一样,感受到日本人这种独特的心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