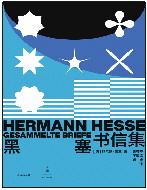书信中的黑塞
齐鲁晚报 2023年07月15日
□谢莹莹
黑塞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有收藏信件的习惯,黑塞继承了这一传统。他是个几乎有信必回的人,这是对写信人的尊重,也是黑塞发表自己观点的方式。写信是一时给特定个人发出的信息,书信既有目的性,更有私人性。黑塞的书信有些是在冷静地分析问题,带着自己的价值观,难以取悦收信人;有些是以真诚、真实的笔触剖析自己,一丝不苟,没有丝毫的粉饰痕迹;有些是与朋友热切的讨论;除了写给家人朋友之外,还有许多是仔细回应读者和陌生人的询问、求助甚至谩骂,处处带着对个体、社会和文学艺术的关怀。他认真诚挚地回答各种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只要求自己,并不要求他人。许多我们在小说、散文中无法得知的事,却能在书信中娓娓呈现,特别是黑塞从小到老的病痛、对家庭的态度等等,这些是更加具有私人性质的。
书信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黑塞。他从小就想做个诗人,却因神学院的教育过分僵化死板,无法忍受无聊的课程,于是向往自由的小诗人逃学、濒临死亡,被捉回学校后,接着生病,休学。父母焦虑无奈之下,辗转将他送到儿童精神病院疗养,在此,他的精神肉体备受折磨。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他愤怒、痛苦、无奈,不断要求父母把他接出疗养院,疗养院的生活使他接近疯狂,他宁愿以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少年称“从我的立场出发,我要像席勒那样说:我是人,有个性有人格的人”。这个立场贯穿黑塞的一生。少年黑塞就是在这样不断的反抗中努力救赎自己,而后自学成就自己的。从父母、祖父母、老师、牧师给他的信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教育工作者不懂得儿童的心理、不懂得人的灵魂需求,即使出于好意,他们的行为却在打击少年的意志,消灭少年的本能,少年黑塞在家庭、学校、神学等传统诸种权威的压迫之下没有被毁掉,说明他内心的力量多么强大!
相比于家庭,黑塞似乎更加注重友情。因为一生不被理解,所以一生寻求理解,他的不少信件表达了他需要朋友们的理解,需要人听他讲述心中的感情、酝酿改变思想及写作风格的必要和艰难,以及混乱中对自己的疑问。我们看到他和巴尔、茨威格、罗曼·罗兰、苏尔坎普等人的真挚友谊。与茨威格的通信始于他青年时代,直到茨威格在纳粹时代登上逃亡美国的船只为止。与罗曼·罗兰的深厚友谊建立于“一战”之前,在黑塞备受精神煎熬时,罗兰向他伸出了手,他们两人同样反对战争与流血,反对任何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相信存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艺术文学。苏尔坎普受尽纳粹监狱的酷刑折磨,“二战”结束后,黑塞坚决支持他重新投入出版事业。“苏尔坎普对我而言,主要是个男子汉、是个人物、是有性格的人,我只能说,如果德国拥有千百个这种有性格的人,那么德国就有救了。”黑塞的作品至今仍是苏尔坎普出版社的重点。
至于婚姻,他最初两段婚姻并不美满。第三次婚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26年,他与研究艺术史、有犹太血统的妮侬·多尔宾相识,经过几年的磨合,到1931年终于结婚。这段婚姻使黑塞有了稳定的家庭生活,妮侬保护着黑塞,同时也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他们和谐相处,直到他1962年去世。
“一战”对黑塞整个人生影响巨大,他见到的现实世界与自己的内心完全无法和解,于是孤独无援,深陷痛苦。他感到原先的生活过分舒适,与世无争让自己付出了太多代价,作品中的和谐其实是虚幻,他必须好好内省在这个充满罪行的纷乱世界中到底应该如何自处,觉得必须改变写作风格,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说。此时的他,失去家庭、财产、房子,于1919年独自躲到瑞士偏僻的蒙塔诺拉隐居,生活简朴,在树林中散步时,捡起几颗栗子就是一顿饭。而他的新作,如《童话》《德米安》,受到友人和读者的质疑和不解,他们认为他失去了早期作品中和谐美妙的氛围。他自己也质疑写作的意义,将画画作为精神的依托。这是黑塞生命中第二次的蜕变,和少年时代挣脱出樊笼一样痛苦而艰辛。在不断的求索中,他逐渐写出了《窥探混沌》《悉达多》《荒原狼》《纳齐斯与戈德蒙》《玻璃球游戏》等名作。
在书信中,我们见到走在深渊边缘的黑塞,也见到充满爱和希望的黑塞,见到不断埋怨与满是愤怒的黑塞,也见到温柔幽默的黑塞,但也可以说,我们见到的黑塞只有一个,那就是毕生寻找自我、坚守自我、成为自我的黑塞。黑塞始终忠于灵魂深处的召唤,始终相信每一位个体存在于世的使命和价值,当我困于病榻阅读他的书信时,仿佛一位老友在耳畔娓娓诉说生命的真义,为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慰藉。我曾将部分译好的书信分享给年轻的朋友,他们说,在这个依然存在着战争、动荡和诱惑的时代,黑塞具有永恒的魅力,这让我感到高兴。我衷心希望能通过本书,将这份慰藉带给更多的朋友。
(本文为《黑塞书信集》译者序,内容有删节)
黑塞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有收藏信件的习惯,黑塞继承了这一传统。他是个几乎有信必回的人,这是对写信人的尊重,也是黑塞发表自己观点的方式。写信是一时给特定个人发出的信息,书信既有目的性,更有私人性。黑塞的书信有些是在冷静地分析问题,带着自己的价值观,难以取悦收信人;有些是以真诚、真实的笔触剖析自己,一丝不苟,没有丝毫的粉饰痕迹;有些是与朋友热切的讨论;除了写给家人朋友之外,还有许多是仔细回应读者和陌生人的询问、求助甚至谩骂,处处带着对个体、社会和文学艺术的关怀。他认真诚挚地回答各种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只要求自己,并不要求他人。许多我们在小说、散文中无法得知的事,却能在书信中娓娓呈现,特别是黑塞从小到老的病痛、对家庭的态度等等,这些是更加具有私人性质的。
书信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黑塞。他从小就想做个诗人,却因神学院的教育过分僵化死板,无法忍受无聊的课程,于是向往自由的小诗人逃学、濒临死亡,被捉回学校后,接着生病,休学。父母焦虑无奈之下,辗转将他送到儿童精神病院疗养,在此,他的精神肉体备受折磨。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他愤怒、痛苦、无奈,不断要求父母把他接出疗养院,疗养院的生活使他接近疯狂,他宁愿以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少年称“从我的立场出发,我要像席勒那样说:我是人,有个性有人格的人”。这个立场贯穿黑塞的一生。少年黑塞就是在这样不断的反抗中努力救赎自己,而后自学成就自己的。从父母、祖父母、老师、牧师给他的信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教育工作者不懂得儿童的心理、不懂得人的灵魂需求,即使出于好意,他们的行为却在打击少年的意志,消灭少年的本能,少年黑塞在家庭、学校、神学等传统诸种权威的压迫之下没有被毁掉,说明他内心的力量多么强大!
相比于家庭,黑塞似乎更加注重友情。因为一生不被理解,所以一生寻求理解,他的不少信件表达了他需要朋友们的理解,需要人听他讲述心中的感情、酝酿改变思想及写作风格的必要和艰难,以及混乱中对自己的疑问。我们看到他和巴尔、茨威格、罗曼·罗兰、苏尔坎普等人的真挚友谊。与茨威格的通信始于他青年时代,直到茨威格在纳粹时代登上逃亡美国的船只为止。与罗曼·罗兰的深厚友谊建立于“一战”之前,在黑塞备受精神煎熬时,罗兰向他伸出了手,他们两人同样反对战争与流血,反对任何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相信存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艺术文学。苏尔坎普受尽纳粹监狱的酷刑折磨,“二战”结束后,黑塞坚决支持他重新投入出版事业。“苏尔坎普对我而言,主要是个男子汉、是个人物、是有性格的人,我只能说,如果德国拥有千百个这种有性格的人,那么德国就有救了。”黑塞的作品至今仍是苏尔坎普出版社的重点。
至于婚姻,他最初两段婚姻并不美满。第三次婚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26年,他与研究艺术史、有犹太血统的妮侬·多尔宾相识,经过几年的磨合,到1931年终于结婚。这段婚姻使黑塞有了稳定的家庭生活,妮侬保护着黑塞,同时也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他们和谐相处,直到他1962年去世。
“一战”对黑塞整个人生影响巨大,他见到的现实世界与自己的内心完全无法和解,于是孤独无援,深陷痛苦。他感到原先的生活过分舒适,与世无争让自己付出了太多代价,作品中的和谐其实是虚幻,他必须好好内省在这个充满罪行的纷乱世界中到底应该如何自处,觉得必须改变写作风格,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说。此时的他,失去家庭、财产、房子,于1919年独自躲到瑞士偏僻的蒙塔诺拉隐居,生活简朴,在树林中散步时,捡起几颗栗子就是一顿饭。而他的新作,如《童话》《德米安》,受到友人和读者的质疑和不解,他们认为他失去了早期作品中和谐美妙的氛围。他自己也质疑写作的意义,将画画作为精神的依托。这是黑塞生命中第二次的蜕变,和少年时代挣脱出樊笼一样痛苦而艰辛。在不断的求索中,他逐渐写出了《窥探混沌》《悉达多》《荒原狼》《纳齐斯与戈德蒙》《玻璃球游戏》等名作。
在书信中,我们见到走在深渊边缘的黑塞,也见到充满爱和希望的黑塞,见到不断埋怨与满是愤怒的黑塞,也见到温柔幽默的黑塞,但也可以说,我们见到的黑塞只有一个,那就是毕生寻找自我、坚守自我、成为自我的黑塞。黑塞始终忠于灵魂深处的召唤,始终相信每一位个体存在于世的使命和价值,当我困于病榻阅读他的书信时,仿佛一位老友在耳畔娓娓诉说生命的真义,为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慰藉。我曾将部分译好的书信分享给年轻的朋友,他们说,在这个依然存在着战争、动荡和诱惑的时代,黑塞具有永恒的魅力,这让我感到高兴。我衷心希望能通过本书,将这份慰藉带给更多的朋友。
(本文为《黑塞书信集》译者序,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