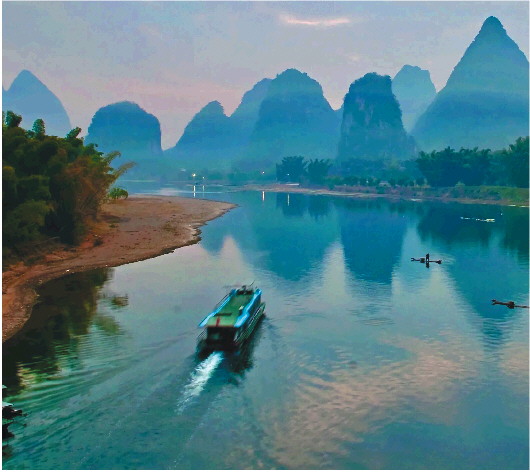大河拐大弯
齐鲁晚报 2023年11月21日
□钟倩
史铁生曾引用西川的诗句,“我打开一本书∕一个灵魂就苏醒……我阅读一个家族的预言∕我看到的痛苦并不比痛苦更多∕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我读过西川的诗,也上过他的文学课,他博学、睿智、幽默,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对诗歌的深刻洞见和现实的认识,能够触发新的思考。
《我的身体就像一座旅馆:西川演讲访谈录》收录西川的演讲和访谈,不啻一本诗歌思想集,读来轻松、智性、有趣。诗人如是说道,“我只是希望能够写出与自己灵魂相当的东西,或者从相反的方向说,我希望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能给出一个我认可的灵魂,并且也能够被这个世界上我尊敬的灵魂们所认可。”他有个生动的比喻,把身体比作旅馆,可谓一语双关。我们都是一介无根的旅人,来到人世间走一趟,精神的漂泊或流亡是命中注定;对诗人来说,身体就像旅馆,里面住着好多灵魂,“它们要求我们说话的时候,有时声音就不是一个声音。所以我写的东西也是乱七八糟的,这里面有一些我自己的原因,那也许是不同的声音在说话,或者是不同的声音合成一个特别浑浊的、听不清楚的、没有明确目的、没有明确方向的、真实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个复数的灵魂开始塑造我的语言,使我的语言变成和别人的语言不太一样的语言。”这正是他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即从“个我”走向“他我”,继而走向“一切我”,在自相矛盾中抵达统一,拥有辽阔的视野和不确定的自我,凸显语言的操练和精神的独立。
“诗是对生活的匡正”。徐怀中当年给学生上课时说过,语言是作家的内分泌。言外之意,语言要有独特之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西川坚持“保持一个艺术家吸血鬼般的开放性”的观点,他写诗、译诗、授课、游走欧美等,都是以诗的名义看到生命的可能性,看到不同的人类困境,抑或说看到苦难本身。先有包容心和悲悯心,后有诗人,这是诗歌的神圣之处。要知道,诗意并非都是美好的,那些卑微的、鄙陋的、污秽的、失意的,也都是诗意,比如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长篇小说《微物之神》,谁能说没有诗的品格呢?或许,我们终其一生也无法写出流传后世的诗章,但是,我们离不开诗意的滋养。好的诗人首先保持一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次葆有处理语言的技艺。马拉美提出“语言之花”,是说一个诗人必须首先让他的诗歌语言触及那真实的花朵,然后再把它处理成语言之花。可见,真实是诗歌的命脉,所以发现诗歌之美是件困难的事,这正是创作的永恒课题。
我喜欢写诗、读诗以及诗话、诗论,那些闪烁思想火苗的诗论也是诗。用诗来制横内心的世界,放慢生活的节奏,从而抵抗庸俗与喧嚣,这不过是自己独处的方式。除此之外,我还享受诗歌里的韵律和节拍,好的诗歌与音乐媲美,读的过程沉湎其中,触摸到美,哪怕是哀婉的、忧伤的、沉痛的,也有撼人心魄的力量。
多年前,楼上住着一位大学老师,教语文课,他脚蹬运动鞋,头戴棒球帽,每天按部就班地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回家路上两人有说有笑。冬天下雪天,他从外面回来,拎着一兜馄饨皮、几棵香菜,还有绞好的肉馅,俨然是回家包馄饨吃。那绿油油的香菜,格外惹眼,像是旁逸斜出的春天,一直蔓延到人的心里。偶尔,会遇见他搬着折叠自行车上楼,但很少与外人交流,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著名的诗人,偶然机会读到另一位诗人写给他的诗,“他的智慧让他卑微而勇敢地生活∕笑容常在∕像浑浊世界里的一块光斑∕走路、买菜、坐单位的班车……∕他酿造一种口味复杂的酒∕把自己给灌醉了。”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了他的沉默——“出乎其外”相对容易,“入乎其内”实在太难,他用这种方式保持内在的清洁和独立,以此进入语言的肺腑之间。同样的话史铁生也说过,“你不必非得看过多少本书,但你要看重这沉默,这黑夜,它教会你思想而不单是看书。”正如西川在访谈中所说的“离经叛道”,“我们应该调动我们的一切可能性,反叛我们的阅读经验。”与此同时,要有开拓精神。说到底,诗歌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精神,一如在不可能中修行,探索和寻求未知。倘若把文学比作一条大河,那么诗歌是时候需要“拐大弯”了——思想逆流而上,诗歌才能生气淋漓。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在诺奖演说中回忆儿时那只敏感的水桶,“不知道历史,不懂性,悬浮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我们就像我们餐具洗涤室内一桶饮用水那样易受感染和易受影响:每当一列经过的火车带来大地的震动,水面便会微妙地、同心地泛起涟漪,并且是在绝然的寂静中。”今天,那只敏感的水桶仍在荡起涟漪,试图建立起音乐秩序,“忠实于外部现实的冲击,敏感于诗人生命的内部规律”的秩序,这正是思想的升华,亦是语言的锤炼。语言即思想,保持那只水桶的敏感、潮湿、开阔,是我们的基本功课,就像保持与大明湖为邻的关系,澄澈、明净、辽阔,以明湖为镜擦拭内心,调适语言,从而扭亮精神的苍穹,抵达生命的真谛。
史铁生曾引用西川的诗句,“我打开一本书∕一个灵魂就苏醒……我阅读一个家族的预言∕我看到的痛苦并不比痛苦更多∕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我读过西川的诗,也上过他的文学课,他博学、睿智、幽默,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对诗歌的深刻洞见和现实的认识,能够触发新的思考。
《我的身体就像一座旅馆:西川演讲访谈录》收录西川的演讲和访谈,不啻一本诗歌思想集,读来轻松、智性、有趣。诗人如是说道,“我只是希望能够写出与自己灵魂相当的东西,或者从相反的方向说,我希望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能给出一个我认可的灵魂,并且也能够被这个世界上我尊敬的灵魂们所认可。”他有个生动的比喻,把身体比作旅馆,可谓一语双关。我们都是一介无根的旅人,来到人世间走一趟,精神的漂泊或流亡是命中注定;对诗人来说,身体就像旅馆,里面住着好多灵魂,“它们要求我们说话的时候,有时声音就不是一个声音。所以我写的东西也是乱七八糟的,这里面有一些我自己的原因,那也许是不同的声音在说话,或者是不同的声音合成一个特别浑浊的、听不清楚的、没有明确目的、没有明确方向的、真实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个复数的灵魂开始塑造我的语言,使我的语言变成和别人的语言不太一样的语言。”这正是他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即从“个我”走向“他我”,继而走向“一切我”,在自相矛盾中抵达统一,拥有辽阔的视野和不确定的自我,凸显语言的操练和精神的独立。
“诗是对生活的匡正”。徐怀中当年给学生上课时说过,语言是作家的内分泌。言外之意,语言要有独特之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西川坚持“保持一个艺术家吸血鬼般的开放性”的观点,他写诗、译诗、授课、游走欧美等,都是以诗的名义看到生命的可能性,看到不同的人类困境,抑或说看到苦难本身。先有包容心和悲悯心,后有诗人,这是诗歌的神圣之处。要知道,诗意并非都是美好的,那些卑微的、鄙陋的、污秽的、失意的,也都是诗意,比如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长篇小说《微物之神》,谁能说没有诗的品格呢?或许,我们终其一生也无法写出流传后世的诗章,但是,我们离不开诗意的滋养。好的诗人首先保持一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次葆有处理语言的技艺。马拉美提出“语言之花”,是说一个诗人必须首先让他的诗歌语言触及那真实的花朵,然后再把它处理成语言之花。可见,真实是诗歌的命脉,所以发现诗歌之美是件困难的事,这正是创作的永恒课题。
我喜欢写诗、读诗以及诗话、诗论,那些闪烁思想火苗的诗论也是诗。用诗来制横内心的世界,放慢生活的节奏,从而抵抗庸俗与喧嚣,这不过是自己独处的方式。除此之外,我还享受诗歌里的韵律和节拍,好的诗歌与音乐媲美,读的过程沉湎其中,触摸到美,哪怕是哀婉的、忧伤的、沉痛的,也有撼人心魄的力量。
多年前,楼上住着一位大学老师,教语文课,他脚蹬运动鞋,头戴棒球帽,每天按部就班地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回家路上两人有说有笑。冬天下雪天,他从外面回来,拎着一兜馄饨皮、几棵香菜,还有绞好的肉馅,俨然是回家包馄饨吃。那绿油油的香菜,格外惹眼,像是旁逸斜出的春天,一直蔓延到人的心里。偶尔,会遇见他搬着折叠自行车上楼,但很少与外人交流,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著名的诗人,偶然机会读到另一位诗人写给他的诗,“他的智慧让他卑微而勇敢地生活∕笑容常在∕像浑浊世界里的一块光斑∕走路、买菜、坐单位的班车……∕他酿造一种口味复杂的酒∕把自己给灌醉了。”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了他的沉默——“出乎其外”相对容易,“入乎其内”实在太难,他用这种方式保持内在的清洁和独立,以此进入语言的肺腑之间。同样的话史铁生也说过,“你不必非得看过多少本书,但你要看重这沉默,这黑夜,它教会你思想而不单是看书。”正如西川在访谈中所说的“离经叛道”,“我们应该调动我们的一切可能性,反叛我们的阅读经验。”与此同时,要有开拓精神。说到底,诗歌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精神,一如在不可能中修行,探索和寻求未知。倘若把文学比作一条大河,那么诗歌是时候需要“拐大弯”了——思想逆流而上,诗歌才能生气淋漓。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在诺奖演说中回忆儿时那只敏感的水桶,“不知道历史,不懂性,悬浮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我们就像我们餐具洗涤室内一桶饮用水那样易受感染和易受影响:每当一列经过的火车带来大地的震动,水面便会微妙地、同心地泛起涟漪,并且是在绝然的寂静中。”今天,那只敏感的水桶仍在荡起涟漪,试图建立起音乐秩序,“忠实于外部现实的冲击,敏感于诗人生命的内部规律”的秩序,这正是思想的升华,亦是语言的锤炼。语言即思想,保持那只水桶的敏感、潮湿、开阔,是我们的基本功课,就像保持与大明湖为邻的关系,澄澈、明净、辽阔,以明湖为镜擦拭内心,调适语言,从而扭亮精神的苍穹,抵达生命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