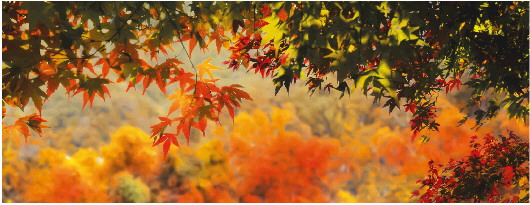金克木的良师益友
齐鲁晚报 2025年01月15日
□李怀宇
金克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他受到的正规学校教育,只到小学毕业为止,后来完全是凭借自学。1946年,他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印度哲学;1948年到北京大学任东方语文系教授。从小学生到大学教授,这个人生的谜语引人猜想。我读金克木的《续断编:金克木述生平》,观其一生的良师益友,以求知人论世的一点心得。
金克木的学问,好像一个活图书馆。许多生友回忆,和金克木聊天,几乎是任何话题他都能接上,天南地北无所不知。而他家里几乎没有藏书,因为从武大到北大,他总是傍着图书馆:将书房设在图书馆里。黄永玉回忆钱锺书,钱家的书架和书也不多,黄永玉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钱先生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金克木与钱锺书皆是渊博之士,借图书馆之妙可谓异曲同工。
在《风义兼师友》一文中,金克木说:“我平生有很多良师益友,但使我最感受益的不是人,而是从前的图书馆。”1930年秋天,金克木到北平,发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有市立的公共图书馆。他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随后在北海旁边修起的“北平图书馆”,成为金克木的第二家庭。后来金克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职员,他管借书,利用时间翻看同学借去还回的书,增长了不少知识。从此以后,他每到一地,有可能就去找当地图书馆,好像找老朋友。他曾到香港大学去看“冯平山图书馆”,还见到了馆长许地山,也就是他所佩服的作家“落花生”。在缅甸仰光图书馆看书,他第一次见到披着袈裟的和尚在一页一页翻读贝叶经文。在印度加尔各答,到“帝国图书馆”看书成为他每日自定的功课。那时他觉得仿佛进了古代,看到有字无字的活图书馆。他说:“我在十岁前后,大约十年间看到家中几代累积的杂乱的书像个小书库。离家以后,有不少生活时光是在免费的图书馆中度过的。我看书如同见活人,读书如听师友谈话。”
1935年,金克木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有一天,一个借书人忽然隔着柜台对他轻轻说:“你是金克木吧?你会写文章。某某人非常喜欢你写的文。”从借书证上看出这个人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邓广铭。有一次,邓广铭竟把毕业论文稿带来给金克木看,就是在胡适指导下做的《陈亮传》。又有一次,邓广铭拿来一本装订成册的铅印讲义给金克木看。原来是傅斯年讲的中国文学史。金克木说,傅是五四运动的“新潮派”,怎么留学回来成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邓广铭说:“你先看这本书,看他有没有学问。”金克木拿回一看,不像讲义,是一篇篇讲演稿或笔记。开头讲《诗经》的“四始”,说法很新,但金克木觉得有点靠不住。看到后来种种不同寻常的议论,虽然仍有霸气,但并非空谈,是确有见地,值得思索。
1939年,金克木以意外机缘到湖南大学教法文。暑期到昆明时,他便去访罗常培。罗常培知道金克木竟能教大学,很高兴,临走时给他一张名片,介绍他去见在昆明乡间的傅斯年。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傅斯年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傅斯年没几句便说到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金克木打断他,提出一位教授。傅斯年吧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这时金克木才发现烟斗里装的是云南烟叶碎片,不是外国烟丝,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烟,不冒烟。“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傅斯年接着讲一通希腊、罗马,忽然问金克木:“你学不学希腊文?我有一部用德文教希腊文的书,一共三本,非常好,可以送给你。”金克木连忙推辞,说自己德文程度还不够用作工具去学另一种语言。傅斯年接着闲谈,不是说历史,就是说语言,总之是中国人不研究外国语言、历史,不懂得世界,不行。临行,傅斯年送给金克木一本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凯撒著的《高卢战记》。别后,金克木试着匆匆学了后面附的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去。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兴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语言,奇特的书。他仿佛听到恺撒大将军的三个词的战争报告:“我来到了。我见到了。我胜利了。”读时每告一段落,金克木便写信给傅斯年,证明没有白白得到赠书,并收到复信。
1946年,武汉大学战后复员到武昌珞珈山。有四位新结识不久的教授,分属四系,彼此年龄不过相差一两岁,依长幼次序便是:外文系的周煦良,历史系的唐长孺,哲学系的金克木,中文系的程千帆。珞珈山下在一起散步的四人教的是古典,而对今俗都很注意,谈的并非全是雅事。唐长孺多年不读《红楼梦》,而对红楼中大小人物事件如数家珍,不下于爱讲“红学”的吴宓。周煦良从上海带来两本英文小本子小说,还带来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说是当时上海最风行的小说,写了西南少数民族,有些“法宝”是大战前想不到的。金克木还曾到租书铺租来《青城十九侠》《长眉真人传》等等还珠楼主的小说。四人都对武侠流行而爱情落后议论纷纷,觉得好像是社会日新而人心有“返祖”之势。雅俗合参,古今并重,中外通行,是珞珈四友的共同点。大学本来是“所学者大”,而没有“小家子气”和“行会习气”。四人之外的沈祖棻是程千帆的妻子,以诗词名家,1977年在武汉因车祸故去。沈的诗中有一些《岁暮怀人诗》,忆金克木云:“月里挑灯偏说鬼,酒阑挥麈更谈玄。斯人一去风流歇,寂寞空山廿五年。”
金克木的妻子唐季雍是唐长孺的妹妹。1955年9月19日,陈寅恪致信唐长孺:“长孺先生左右:今日奉到来示并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前数岁曾托令妹季雍女士及金君克木转达钦服之意,想早尘清听矣。……”唐长孺一生没有见过陈寅恪,连“私淑”都怕不敢自认,更谈不上“亲炙”。唐长孺写纪念陈先生百岁诞辰的诗的末句是“教外何妨有别传”。陈先生在信中含蓄承认他是同行,大概可以说唐是闻风兴起者,够不上“亲炙”受教者。而金克木一生见过两次陈寅恪。
1948年四五月间,金克木从武汉到北平,见到老朋友邓广铭,邓广铭引金克木在北大校长室里见到胡适校长,谈了中国佛教史半小时以上。邓广铭还说,他将借用胡校长的汽车去清华大学接陈寅恪进城到中山公园看牡丹花,请季羡林作陪,也邀金克木参加。在中山公园的茶座中,四人围坐一个桌子饮茶。陈寅恪兴致很好,谈了不少话,其中一条是,人取名号也有时代风气,光(绪)宣(统)时期,一阵子取号都是什么“斋”,一阵子又换了什么“庵”。当时,金克木想起小时候有两位本家的哥哥,一个号少斋,一个号幼斋,证明他们的父亲的号必是什么斋;教金克木的一位小学教师的号是少庵,他的父亲的号必是什么庵。恰好证明陈寅恪的话。随后不久,金克木和唐季雍结婚。婚后过了几天,金克木夫妇同去清华园拜访陈寅恪夫妇。金克木将唐长孺交他转呈的论文《白衣天子试释》奉上,说了武汉大学的一些人的近况,其中有陈先生的弟弟陈登恪和好友吴宓。陈寅恪对金克木说《妙法莲华经》的梵文名字慢而发音很准确。金克木回忆:“假如能够预知永别,就会有不少闲话、旧话可以谈,说不定能多少安慰一下他们两位的晚年寂寞。”
金克木一生多遇良师益友,终于成就了百科全书式的学问。但他自称:“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子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学者是指学成功了一门学问的人,我也不是。说我是教员也许还可以。因为我从乡间小学教到初中、高中、大学,除了当过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以外就是当教员。”虽然他只是小学毕业,但一生好学不倦:“人一出生就要学习,也就是在这世界上,宇宙中,探路,一直探到这一生的终点。”
1998年,钱锺书去世后,李慎之问陆灏:钱先生之后,谁最有学问?陆灏说:金克木。
(本文作者系知名媒体人、出版人、作家)
金克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他受到的正规学校教育,只到小学毕业为止,后来完全是凭借自学。1946年,他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印度哲学;1948年到北京大学任东方语文系教授。从小学生到大学教授,这个人生的谜语引人猜想。我读金克木的《续断编:金克木述生平》,观其一生的良师益友,以求知人论世的一点心得。
金克木的学问,好像一个活图书馆。许多生友回忆,和金克木聊天,几乎是任何话题他都能接上,天南地北无所不知。而他家里几乎没有藏书,因为从武大到北大,他总是傍着图书馆:将书房设在图书馆里。黄永玉回忆钱锺书,钱家的书架和书也不多,黄永玉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钱先生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金克木与钱锺书皆是渊博之士,借图书馆之妙可谓异曲同工。
在《风义兼师友》一文中,金克木说:“我平生有很多良师益友,但使我最感受益的不是人,而是从前的图书馆。”1930年秋天,金克木到北平,发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有市立的公共图书馆。他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随后在北海旁边修起的“北平图书馆”,成为金克木的第二家庭。后来金克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职员,他管借书,利用时间翻看同学借去还回的书,增长了不少知识。从此以后,他每到一地,有可能就去找当地图书馆,好像找老朋友。他曾到香港大学去看“冯平山图书馆”,还见到了馆长许地山,也就是他所佩服的作家“落花生”。在缅甸仰光图书馆看书,他第一次见到披着袈裟的和尚在一页一页翻读贝叶经文。在印度加尔各答,到“帝国图书馆”看书成为他每日自定的功课。那时他觉得仿佛进了古代,看到有字无字的活图书馆。他说:“我在十岁前后,大约十年间看到家中几代累积的杂乱的书像个小书库。离家以后,有不少生活时光是在免费的图书馆中度过的。我看书如同见活人,读书如听师友谈话。”
1935年,金克木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有一天,一个借书人忽然隔着柜台对他轻轻说:“你是金克木吧?你会写文章。某某人非常喜欢你写的文。”从借书证上看出这个人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邓广铭。有一次,邓广铭竟把毕业论文稿带来给金克木看,就是在胡适指导下做的《陈亮传》。又有一次,邓广铭拿来一本装订成册的铅印讲义给金克木看。原来是傅斯年讲的中国文学史。金克木说,傅是五四运动的“新潮派”,怎么留学回来成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邓广铭说:“你先看这本书,看他有没有学问。”金克木拿回一看,不像讲义,是一篇篇讲演稿或笔记。开头讲《诗经》的“四始”,说法很新,但金克木觉得有点靠不住。看到后来种种不同寻常的议论,虽然仍有霸气,但并非空谈,是确有见地,值得思索。
1939年,金克木以意外机缘到湖南大学教法文。暑期到昆明时,他便去访罗常培。罗常培知道金克木竟能教大学,很高兴,临走时给他一张名片,介绍他去见在昆明乡间的傅斯年。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傅斯年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傅斯年没几句便说到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金克木打断他,提出一位教授。傅斯年吧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这时金克木才发现烟斗里装的是云南烟叶碎片,不是外国烟丝,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烟,不冒烟。“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傅斯年接着讲一通希腊、罗马,忽然问金克木:“你学不学希腊文?我有一部用德文教希腊文的书,一共三本,非常好,可以送给你。”金克木连忙推辞,说自己德文程度还不够用作工具去学另一种语言。傅斯年接着闲谈,不是说历史,就是说语言,总之是中国人不研究外国语言、历史,不懂得世界,不行。临行,傅斯年送给金克木一本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凯撒著的《高卢战记》。别后,金克木试着匆匆学了后面附的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去。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兴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语言,奇特的书。他仿佛听到恺撒大将军的三个词的战争报告:“我来到了。我见到了。我胜利了。”读时每告一段落,金克木便写信给傅斯年,证明没有白白得到赠书,并收到复信。
1946年,武汉大学战后复员到武昌珞珈山。有四位新结识不久的教授,分属四系,彼此年龄不过相差一两岁,依长幼次序便是:外文系的周煦良,历史系的唐长孺,哲学系的金克木,中文系的程千帆。珞珈山下在一起散步的四人教的是古典,而对今俗都很注意,谈的并非全是雅事。唐长孺多年不读《红楼梦》,而对红楼中大小人物事件如数家珍,不下于爱讲“红学”的吴宓。周煦良从上海带来两本英文小本子小说,还带来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说是当时上海最风行的小说,写了西南少数民族,有些“法宝”是大战前想不到的。金克木还曾到租书铺租来《青城十九侠》《长眉真人传》等等还珠楼主的小说。四人都对武侠流行而爱情落后议论纷纷,觉得好像是社会日新而人心有“返祖”之势。雅俗合参,古今并重,中外通行,是珞珈四友的共同点。大学本来是“所学者大”,而没有“小家子气”和“行会习气”。四人之外的沈祖棻是程千帆的妻子,以诗词名家,1977年在武汉因车祸故去。沈的诗中有一些《岁暮怀人诗》,忆金克木云:“月里挑灯偏说鬼,酒阑挥麈更谈玄。斯人一去风流歇,寂寞空山廿五年。”
金克木的妻子唐季雍是唐长孺的妹妹。1955年9月19日,陈寅恪致信唐长孺:“长孺先生左右:今日奉到来示并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前数岁曾托令妹季雍女士及金君克木转达钦服之意,想早尘清听矣。……”唐长孺一生没有见过陈寅恪,连“私淑”都怕不敢自认,更谈不上“亲炙”。唐长孺写纪念陈先生百岁诞辰的诗的末句是“教外何妨有别传”。陈先生在信中含蓄承认他是同行,大概可以说唐是闻风兴起者,够不上“亲炙”受教者。而金克木一生见过两次陈寅恪。
1948年四五月间,金克木从武汉到北平,见到老朋友邓广铭,邓广铭引金克木在北大校长室里见到胡适校长,谈了中国佛教史半小时以上。邓广铭还说,他将借用胡校长的汽车去清华大学接陈寅恪进城到中山公园看牡丹花,请季羡林作陪,也邀金克木参加。在中山公园的茶座中,四人围坐一个桌子饮茶。陈寅恪兴致很好,谈了不少话,其中一条是,人取名号也有时代风气,光(绪)宣(统)时期,一阵子取号都是什么“斋”,一阵子又换了什么“庵”。当时,金克木想起小时候有两位本家的哥哥,一个号少斋,一个号幼斋,证明他们的父亲的号必是什么斋;教金克木的一位小学教师的号是少庵,他的父亲的号必是什么庵。恰好证明陈寅恪的话。随后不久,金克木和唐季雍结婚。婚后过了几天,金克木夫妇同去清华园拜访陈寅恪夫妇。金克木将唐长孺交他转呈的论文《白衣天子试释》奉上,说了武汉大学的一些人的近况,其中有陈先生的弟弟陈登恪和好友吴宓。陈寅恪对金克木说《妙法莲华经》的梵文名字慢而发音很准确。金克木回忆:“假如能够预知永别,就会有不少闲话、旧话可以谈,说不定能多少安慰一下他们两位的晚年寂寞。”
金克木一生多遇良师益友,终于成就了百科全书式的学问。但他自称:“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子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学者是指学成功了一门学问的人,我也不是。说我是教员也许还可以。因为我从乡间小学教到初中、高中、大学,除了当过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以外就是当教员。”虽然他只是小学毕业,但一生好学不倦:“人一出生就要学习,也就是在这世界上,宇宙中,探路,一直探到这一生的终点。”
1998年,钱锺书去世后,李慎之问陆灏:钱先生之后,谁最有学问?陆灏说:金克木。
(本文作者系知名媒体人、出版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