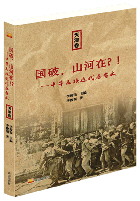【文化小史】 兰花背后的“植物文化”
齐鲁晚报 2025年08月15日
□刘夙
作为一名植物学研究者,我很喜欢《兰花诸相》这类植物文化史著作的写法,即把科学与文化结合起来。本书作者恩德斯比在导言中明确写道:“本书的核心,是我们从科学上了解兰花的历史。”因此,读者可以利用这类著作中讲述的科学知识,对植物建立起一种客观的认识,再在这个超然的基础之上,去审视千百年来人们施加在植物之上的那些文化意象,从而可以更好地感受到它们的精妙和幽默,也能体会其中的沉重和荒谬。
当然,我知道在信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读者眼中,我所谓的“客观”“超然”,也只是一种偏见,只是施加在植物之上的“科学文化意象”。即便如此,哪怕只是换个视角去打量植物身上的那些人文涂抹,我相信你同样可以更好地感受到其中的精妙和幽默,以及沉重和荒谬。
以樱花为例。从科学上来说,它们不过就是蔷薇科李属的一群温带植物,出于繁衍后代的需要,在春天的时候开出灿烂的花朵,借此吸引昆虫传粉,然后结出种子。正巧,人类是一种很容易被美丽的花朵所吸引的动物。演化心理学认为,这是因为人类的祖先曾经以果实为食,而花朵可以兆示果实的出现。如果一只古猿可以掌握分辨花朵的能力,而且能记住开花植物所在的位置,那么等到植物结果的时候,它就可以比其他古猿更早找到果实食用。因此,演化会青睐人类祖先对花朵感兴趣的能力,久而久之,就让对花朵的喜爱内化为人类的一种情感。
演化心理学的这个理论,为全世界的人类普遍喜欢樱花这样又多又浓艳的花卉提供了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在这样一种超然的科学知识基础上,你就会发现,争论樱花的产地在哪里,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庸人自扰。我觉得这就是文化施加的魔咒,它让人迷失在花卉附带的外部意象中,丧失了从本真的内心出发感受花卉之美的能力。
兰花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兰花诸相》在开篇的导言中就指出,全世界两万多种兰花中,只有少数生活在地上的兰花(所谓“地生兰”)会在地下长出一对块根。但这类地生兰偏偏在地中海地区分布较多,古希腊人觉得它们像是睾丸,于是通过“取象比类”的传统思维,认定它们可以入药,用于催发人的性欲,结果就让西方的兰花意象怎么也无法摆脱与性的关联。“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人对全世界的殖民,以及对异域珍稀兰花的疯狂搜集,又让兰花成为令人畏惧的热带丛林以及发生在丛林内外的杀戮的象征,于是又与死亡的意象挂起钩来。假如兰花像人一样有意识的话,它大概会觉得这一切都太荒唐了——我不过是一株小小的草本植物,老老实实地过我的日子,应付大自然的胁迫,天晓得怎么就会被附加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联想,有的甚至还成了刻板印象。
恩德斯比敏锐地指出,假如兰花的故事开始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比如中国和日本),那么“可能从来都不会与人类的性欲产生什么关联”。不过,因为本书“主要关注欧洲文化(以及明显受到欧洲人影响的文化)”,所以他没有提及中国和日本的兰花文化。然而,暂且不论日本,中国的兰花意象与西方的兰花意象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往小小的草本植物身上强加了联想和刻板印象。
正如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在《鲜花人类学》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花卉文化,由士大夫阶层主导。这些士人从儒家思想出发,不喜欢樱花、桃花这样又多又浓的花卉,认为它们俗艳而轻佻,象征着奢靡和堕落。当然,这种对抗奢侈和颓废的价值观,并非中国士人所独有,在古罗马、印度等其他多种古代文明中也都有所体现,是理解花文化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士大夫们喜欢的花卉,则以“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为代表。它们都不以花又多又浓取胜,而是靠一种克制、坚忍的气质和风骨来博得士人的青睐。其中的兰,既不是今天广泛栽培的这些花又大又艳的“洋兰”,也有别于地中海地区那些在地下长有两枚块根的地生兰,而主要是兰属的几个种,通称“国兰”。它们在野外多生长于人迹稀少的山林,其花排列稀疏,多为黄绿色调,并不显眼,但非常芳香,再配合形态优雅的长条形叶片,就体现出了独处空谷、孤芳自赏的高洁气质。其实无论是美艳的花色,还是飘荡的花香,目的无非都是为了吸引动物传粉,服务于生殖活动,繁衍后代,但这丝毫不妨碍文人雅客把自身的精神追求投射到国兰身上,给它涂上中华文化的浓重色彩。
当然,我并不想一味批评中西的植物文化。我只是认为,我们对于植物的认识,可以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受从小耳濡目染的文化所遮蔽,带着文化的有色眼镜去看待植物;第二重境界,是知道这些文化油彩都是人类强加给植物的涂饰,于是学会从科学的客观角度去看待植物;第三重境界,则是明白无论科学知识还是植物文化,都是人类的智慧,都可以丰富我们的心灵。就像英国动物学家、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说的,我们完全可以一边理性地了解彩虹的形成原理,一边被彩虹的美丽激发心底的感性赞叹。只有对世间万物同时具备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而且不为这二者所束缚,才能够达成一种理想状态的知识自由。
(作者为上海辰山植物园研究员)
作为一名植物学研究者,我很喜欢《兰花诸相》这类植物文化史著作的写法,即把科学与文化结合起来。本书作者恩德斯比在导言中明确写道:“本书的核心,是我们从科学上了解兰花的历史。”因此,读者可以利用这类著作中讲述的科学知识,对植物建立起一种客观的认识,再在这个超然的基础之上,去审视千百年来人们施加在植物之上的那些文化意象,从而可以更好地感受到它们的精妙和幽默,也能体会其中的沉重和荒谬。
当然,我知道在信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读者眼中,我所谓的“客观”“超然”,也只是一种偏见,只是施加在植物之上的“科学文化意象”。即便如此,哪怕只是换个视角去打量植物身上的那些人文涂抹,我相信你同样可以更好地感受到其中的精妙和幽默,以及沉重和荒谬。
以樱花为例。从科学上来说,它们不过就是蔷薇科李属的一群温带植物,出于繁衍后代的需要,在春天的时候开出灿烂的花朵,借此吸引昆虫传粉,然后结出种子。正巧,人类是一种很容易被美丽的花朵所吸引的动物。演化心理学认为,这是因为人类的祖先曾经以果实为食,而花朵可以兆示果实的出现。如果一只古猿可以掌握分辨花朵的能力,而且能记住开花植物所在的位置,那么等到植物结果的时候,它就可以比其他古猿更早找到果实食用。因此,演化会青睐人类祖先对花朵感兴趣的能力,久而久之,就让对花朵的喜爱内化为人类的一种情感。
演化心理学的这个理论,为全世界的人类普遍喜欢樱花这样又多又浓艳的花卉提供了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在这样一种超然的科学知识基础上,你就会发现,争论樱花的产地在哪里,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庸人自扰。我觉得这就是文化施加的魔咒,它让人迷失在花卉附带的外部意象中,丧失了从本真的内心出发感受花卉之美的能力。
兰花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兰花诸相》在开篇的导言中就指出,全世界两万多种兰花中,只有少数生活在地上的兰花(所谓“地生兰”)会在地下长出一对块根。但这类地生兰偏偏在地中海地区分布较多,古希腊人觉得它们像是睾丸,于是通过“取象比类”的传统思维,认定它们可以入药,用于催发人的性欲,结果就让西方的兰花意象怎么也无法摆脱与性的关联。“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人对全世界的殖民,以及对异域珍稀兰花的疯狂搜集,又让兰花成为令人畏惧的热带丛林以及发生在丛林内外的杀戮的象征,于是又与死亡的意象挂起钩来。假如兰花像人一样有意识的话,它大概会觉得这一切都太荒唐了——我不过是一株小小的草本植物,老老实实地过我的日子,应付大自然的胁迫,天晓得怎么就会被附加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联想,有的甚至还成了刻板印象。
恩德斯比敏锐地指出,假如兰花的故事开始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比如中国和日本),那么“可能从来都不会与人类的性欲产生什么关联”。不过,因为本书“主要关注欧洲文化(以及明显受到欧洲人影响的文化)”,所以他没有提及中国和日本的兰花文化。然而,暂且不论日本,中国的兰花意象与西方的兰花意象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往小小的草本植物身上强加了联想和刻板印象。
正如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在《鲜花人类学》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花卉文化,由士大夫阶层主导。这些士人从儒家思想出发,不喜欢樱花、桃花这样又多又浓的花卉,认为它们俗艳而轻佻,象征着奢靡和堕落。当然,这种对抗奢侈和颓废的价值观,并非中国士人所独有,在古罗马、印度等其他多种古代文明中也都有所体现,是理解花文化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士大夫们喜欢的花卉,则以“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为代表。它们都不以花又多又浓取胜,而是靠一种克制、坚忍的气质和风骨来博得士人的青睐。其中的兰,既不是今天广泛栽培的这些花又大又艳的“洋兰”,也有别于地中海地区那些在地下长有两枚块根的地生兰,而主要是兰属的几个种,通称“国兰”。它们在野外多生长于人迹稀少的山林,其花排列稀疏,多为黄绿色调,并不显眼,但非常芳香,再配合形态优雅的长条形叶片,就体现出了独处空谷、孤芳自赏的高洁气质。其实无论是美艳的花色,还是飘荡的花香,目的无非都是为了吸引动物传粉,服务于生殖活动,繁衍后代,但这丝毫不妨碍文人雅客把自身的精神追求投射到国兰身上,给它涂上中华文化的浓重色彩。
当然,我并不想一味批评中西的植物文化。我只是认为,我们对于植物的认识,可以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受从小耳濡目染的文化所遮蔽,带着文化的有色眼镜去看待植物;第二重境界,是知道这些文化油彩都是人类强加给植物的涂饰,于是学会从科学的客观角度去看待植物;第三重境界,则是明白无论科学知识还是植物文化,都是人类的智慧,都可以丰富我们的心灵。就像英国动物学家、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说的,我们完全可以一边理性地了解彩虹的形成原理,一边被彩虹的美丽激发心底的感性赞叹。只有对世间万物同时具备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而且不为这二者所束缚,才能够达成一种理想状态的知识自由。
(作者为上海辰山植物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