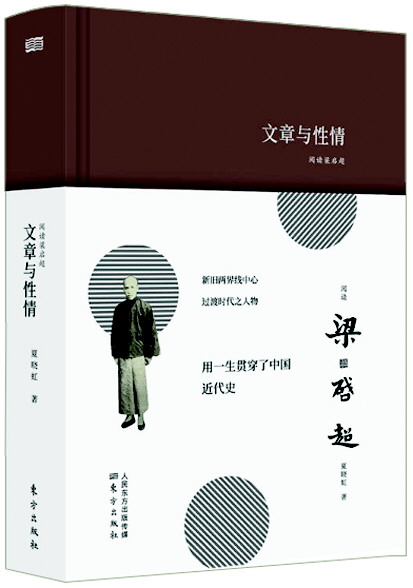与梁启超结缘三十年
齐鲁晚报 2019年08月17日
□夏晓虹
自从1983年开始阅读《饮冰室合集》,梁启超即成为我关注最久、投入最多的研究对象,迄今为止,我出版过三本有关梁启超的研究著作。愿意为一个研究对象付出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可想而知,此人之于我必定意义重大或魅力十足。仔细想来,梁启超有如下三方面优长对我深具吸引力:
首先,我做近代文学研究,是从梁启超起步的。日后回想,我一直很庆幸这一选择的正确,甚至可以说是英明。因为从哪里入手,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学者将来的研究格局。我非常欣赏梁启超关于“理想专传”的构想:“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此处的“伟大”不单指“人格的伟大”,也包括“关系的伟大”,后者甚至更重要。因此,传主应是“可以做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或“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一类人物,亦即“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如果倒转此一借人物写时代的角度,而从观照一个时代的政治、学术以至于文学的流变着眼,那么,这些处在关系网络中心的人物,无疑会带给研究者更开阔的视野,展现更精确的图景。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伟大人物。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文学变革、学术思潮更迭、社会政治改良,梁启超不仅亲身经历,且均为引领潮流的中坚。追随梁启超,也使我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得以进入更为广大的史学领域,让我因此能够走得更远。
其次,很多曾经处于时代中心的人物,已被掩埋在历史深处,不再引起今人的兴趣与关心。但梁启超不同,学术论著不必说,即使影视作品中,也不时可见其身影。起码,到现在为止,梁启超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探求个中原因,可以发现,世人对梁启超尽管有多种概括,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等等,不过,若从根本而言,实在只有“启蒙者”的称号对其最适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也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子,“开通民智”始终是其一贯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然不乏专门,却多为现代国民所应了解与实践。何况,与其师康有为的治学三十岁后即“不复有进”不同,梁启超“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谓之“善变”也罢,“与时俱进”也好,直到去世,梁启超留在时人印象中的“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他所写下的带有启蒙气息的巨量文字,今日读来照样新鲜感人。其年轻时的自我期待“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二首》其二),也大可如愿以偿。
最后,在为时代写照而挑选作传人物时,“人格的伟大”虽不及“关系的伟大”更获优待,但若要长期保持关注,则此一研究对象在品格、性情上,必定应有使人感佩或愿意亲近之处。梁启超虽也投身政治活动,并一度进入官场,却绝少此间常见的恶习。胡适眼中的梁启超,“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1929年1月20日胡适日记),此说最传神。而能够拥有林长民、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劢、丁文江、徐志摩等一班俊彦爱戴的梁氏,其人格之光明磊落亦可想见。而其“善变”虽也会遭人诟病,但在梁启超本人,都是出以真诚,“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非如政客的投机逢迎、朝三暮四。况且,即或在变中,梁氏也自有其不变的坚持在,如郑振铎指出的“爱国”宗旨(《梁任公先生》),如我前面提及的启蒙立场。梁启超又自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学问之趣味》),这让他做起事来总是兴会淋漓,富有感染力。其爱家人,爱朋友,爱文学,爱书法,爱生活中所有新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使人乐于与之长久盘桓。
与这样一位时代伟人、启蒙先驱、可爱长者相遇,结缘三十多年,至今仍不厌不弃,并且,这一缘分还会继续下去,实为本人学术生涯中最大的幸事。
《本文为《阅读梁启超》序言,有删节)
自从1983年开始阅读《饮冰室合集》,梁启超即成为我关注最久、投入最多的研究对象,迄今为止,我出版过三本有关梁启超的研究著作。愿意为一个研究对象付出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可想而知,此人之于我必定意义重大或魅力十足。仔细想来,梁启超有如下三方面优长对我深具吸引力:
首先,我做近代文学研究,是从梁启超起步的。日后回想,我一直很庆幸这一选择的正确,甚至可以说是英明。因为从哪里入手,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学者将来的研究格局。我非常欣赏梁启超关于“理想专传”的构想:“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此处的“伟大”不单指“人格的伟大”,也包括“关系的伟大”,后者甚至更重要。因此,传主应是“可以做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或“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一类人物,亦即“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如果倒转此一借人物写时代的角度,而从观照一个时代的政治、学术以至于文学的流变着眼,那么,这些处在关系网络中心的人物,无疑会带给研究者更开阔的视野,展现更精确的图景。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伟大人物。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文学变革、学术思潮更迭、社会政治改良,梁启超不仅亲身经历,且均为引领潮流的中坚。追随梁启超,也使我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得以进入更为广大的史学领域,让我因此能够走得更远。
其次,很多曾经处于时代中心的人物,已被掩埋在历史深处,不再引起今人的兴趣与关心。但梁启超不同,学术论著不必说,即使影视作品中,也不时可见其身影。起码,到现在为止,梁启超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探求个中原因,可以发现,世人对梁启超尽管有多种概括,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等等,不过,若从根本而言,实在只有“启蒙者”的称号对其最适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也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子,“开通民智”始终是其一贯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然不乏专门,却多为现代国民所应了解与实践。何况,与其师康有为的治学三十岁后即“不复有进”不同,梁启超“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谓之“善变”也罢,“与时俱进”也好,直到去世,梁启超留在时人印象中的“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他所写下的带有启蒙气息的巨量文字,今日读来照样新鲜感人。其年轻时的自我期待“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二首》其二),也大可如愿以偿。
最后,在为时代写照而挑选作传人物时,“人格的伟大”虽不及“关系的伟大”更获优待,但若要长期保持关注,则此一研究对象在品格、性情上,必定应有使人感佩或愿意亲近之处。梁启超虽也投身政治活动,并一度进入官场,却绝少此间常见的恶习。胡适眼中的梁启超,“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1929年1月20日胡适日记),此说最传神。而能够拥有林长民、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劢、丁文江、徐志摩等一班俊彦爱戴的梁氏,其人格之光明磊落亦可想见。而其“善变”虽也会遭人诟病,但在梁启超本人,都是出以真诚,“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非如政客的投机逢迎、朝三暮四。况且,即或在变中,梁氏也自有其不变的坚持在,如郑振铎指出的“爱国”宗旨(《梁任公先生》),如我前面提及的启蒙立场。梁启超又自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学问之趣味》),这让他做起事来总是兴会淋漓,富有感染力。其爱家人,爱朋友,爱文学,爱书法,爱生活中所有新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使人乐于与之长久盘桓。
与这样一位时代伟人、启蒙先驱、可爱长者相遇,结缘三十多年,至今仍不厌不弃,并且,这一缘分还会继续下去,实为本人学术生涯中最大的幸事。
《本文为《阅读梁启超》序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