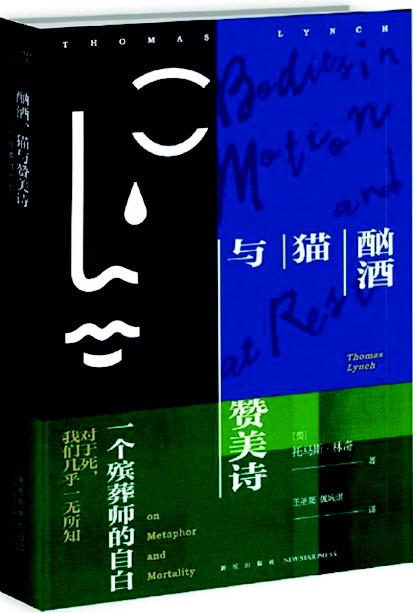生与死的沉思默想
齐鲁晚报 2019年04月27日
□王淼
托马斯·林奇是一位殡葬师——准确地说,是一位殡葬师兼诗人,或者说是一位喜欢写作的殡葬师。至于林奇写作的理由,说起来非常简单,首先,他不打高尔夫,这让他一周有两到三天的空当儿;其次,他戒酒了——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他喝得很凶,因为酒,他已经失去太多的东西,他现在不想失去更多的东西了——戒酒,让他一周又多出两三晚神志清醒的时间。当然,更重要的是,林奇享受写作的过程,他需要一个文字编织的包,能够把生活中的悲欢忧喜的感悟与聚散离合的际遇都收进去。林奇欣喜地写道,在那些宁静的时刻,“文字就会迎向你,无论这些文字是出自自己还是他人,是你自己的声音还是上帝的声音。身体一边流汗,灵感一边涌现,感觉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
作为一位家族产业的继承者,林奇的殡葬师生涯起始于他二十六岁那年。数十年来,林奇主持过成百上千的葬礼,可谓看惯了人世间的生生死死,也难免会产生一些联想和感慨。《酗酒、猫与赞美诗》中收录的文章,其实正是林奇平素沉思冥想的结果,他攫取了日常生活中的三个关键词,以之构成他写作的三个意象,围绕这三个意象,铺陈开他对于生命的种种奇思妙想:关于生死,关于两性,关于欲求,关于梦想……林奇首先把生死看作人之为人的基点,因为有生,人类才能有忧伤,有欢喜,有欲望,有追求;因为有死,人类才会只争朝夕,及时行乐,秉烛夜游,分秒必争。林奇既讲生的事情,也讲死的事情,尽管生的事情远比死的事情有趣,但生命终归是一个消逝的过程,人类在世间所做的一切,说穿了就是一种计算——加法,减法,乘法,除法,最后的结果,“不是埋在每英亩葬一千人的地里,就是变成两千克左右的骨灰”。
但终归会消逝的人生就不值得认真去过了吗?显然不是,在林奇看来,恰恰正是因为生命易逝,每个人都是生命的过客,人生才值得拥有,生命才变得格外珍贵。与易逝的人生相比,反而是臆想中的天堂有点可疑,那里天气宜人,食物充足,没有纷争,没有死亡……一切似乎都完美无缺,唯独缺少的,只是需求。人类向往的天堂其实就是一种无所事事、懒惰无用的生活——没有死亡,生命失去了紧迫感;没有需求,人生失去了向上的动力。殊不知人类的本质,原本是与希望、受伤、挨饿、恳求、流泪、欢笑……如此等等的激烈情感紧密相连的。世间最真实的存在,不是天真无邪与懵懂无知的天堂至乐,而是心痛与渴望,贪欲与疑惑,生命之所以进化,社会之所以进步,端赖需求为之促动,而这一切都是与人类的生死分不开的。所以,林奇把夏娃视作商业之母、需求与发明的保护神,因为没有她对禁果的渴望,人类将永远是白板一块。
当然,身为殡葬师,林奇主要的工作就是照料死者,服务生者,他关注更多的则是人类如何来,人类如何去。林奇觉得,死亡的真相和生命的真相一样,都是人类的必修课,“我死,故我在”,死与生其实代表着生命的一体两面。而一场葬礼决不仅仅是一个花销的数字,它同时也有着宗教的、非宗教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意义,从某种角度上甚至可以这么说,一场好的葬礼就像一首好诗,让参与其中的人们得到提升,然后回到认知、想象和情感的领域。
总之,人生在世,仿佛与时光做一场抓住与放手的永恒游戏,人类想让生命静止下来,时光却永远不会停止脚步。但无论是生,还是死,生命与死亡的事实不会改变——林奇这样说道:“我们爱,也悲伤。我们繁衍后代,然后消失。而在这些存在的引力拉扯之间,我们寻找意义,保存回忆,也为会记住我们的人留下纪念。”
托马斯·林奇是一位殡葬师——准确地说,是一位殡葬师兼诗人,或者说是一位喜欢写作的殡葬师。至于林奇写作的理由,说起来非常简单,首先,他不打高尔夫,这让他一周有两到三天的空当儿;其次,他戒酒了——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他喝得很凶,因为酒,他已经失去太多的东西,他现在不想失去更多的东西了——戒酒,让他一周又多出两三晚神志清醒的时间。当然,更重要的是,林奇享受写作的过程,他需要一个文字编织的包,能够把生活中的悲欢忧喜的感悟与聚散离合的际遇都收进去。林奇欣喜地写道,在那些宁静的时刻,“文字就会迎向你,无论这些文字是出自自己还是他人,是你自己的声音还是上帝的声音。身体一边流汗,灵感一边涌现,感觉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
作为一位家族产业的继承者,林奇的殡葬师生涯起始于他二十六岁那年。数十年来,林奇主持过成百上千的葬礼,可谓看惯了人世间的生生死死,也难免会产生一些联想和感慨。《酗酒、猫与赞美诗》中收录的文章,其实正是林奇平素沉思冥想的结果,他攫取了日常生活中的三个关键词,以之构成他写作的三个意象,围绕这三个意象,铺陈开他对于生命的种种奇思妙想:关于生死,关于两性,关于欲求,关于梦想……林奇首先把生死看作人之为人的基点,因为有生,人类才能有忧伤,有欢喜,有欲望,有追求;因为有死,人类才会只争朝夕,及时行乐,秉烛夜游,分秒必争。林奇既讲生的事情,也讲死的事情,尽管生的事情远比死的事情有趣,但生命终归是一个消逝的过程,人类在世间所做的一切,说穿了就是一种计算——加法,减法,乘法,除法,最后的结果,“不是埋在每英亩葬一千人的地里,就是变成两千克左右的骨灰”。
但终归会消逝的人生就不值得认真去过了吗?显然不是,在林奇看来,恰恰正是因为生命易逝,每个人都是生命的过客,人生才值得拥有,生命才变得格外珍贵。与易逝的人生相比,反而是臆想中的天堂有点可疑,那里天气宜人,食物充足,没有纷争,没有死亡……一切似乎都完美无缺,唯独缺少的,只是需求。人类向往的天堂其实就是一种无所事事、懒惰无用的生活——没有死亡,生命失去了紧迫感;没有需求,人生失去了向上的动力。殊不知人类的本质,原本是与希望、受伤、挨饿、恳求、流泪、欢笑……如此等等的激烈情感紧密相连的。世间最真实的存在,不是天真无邪与懵懂无知的天堂至乐,而是心痛与渴望,贪欲与疑惑,生命之所以进化,社会之所以进步,端赖需求为之促动,而这一切都是与人类的生死分不开的。所以,林奇把夏娃视作商业之母、需求与发明的保护神,因为没有她对禁果的渴望,人类将永远是白板一块。
当然,身为殡葬师,林奇主要的工作就是照料死者,服务生者,他关注更多的则是人类如何来,人类如何去。林奇觉得,死亡的真相和生命的真相一样,都是人类的必修课,“我死,故我在”,死与生其实代表着生命的一体两面。而一场葬礼决不仅仅是一个花销的数字,它同时也有着宗教的、非宗教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意义,从某种角度上甚至可以这么说,一场好的葬礼就像一首好诗,让参与其中的人们得到提升,然后回到认知、想象和情感的领域。
总之,人生在世,仿佛与时光做一场抓住与放手的永恒游戏,人类想让生命静止下来,时光却永远不会停止脚步。但无论是生,还是死,生命与死亡的事实不会改变——林奇这样说道:“我们爱,也悲伤。我们繁衍后代,然后消失。而在这些存在的引力拉扯之间,我们寻找意义,保存回忆,也为会记住我们的人留下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