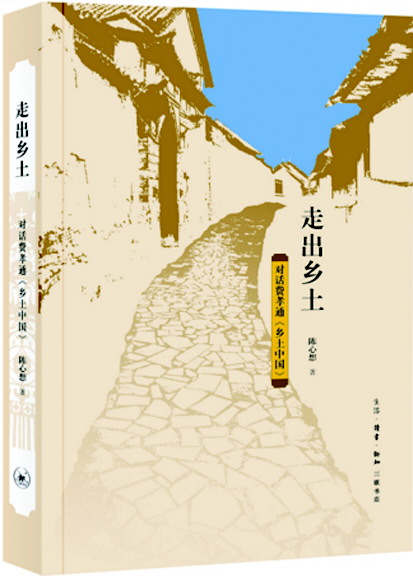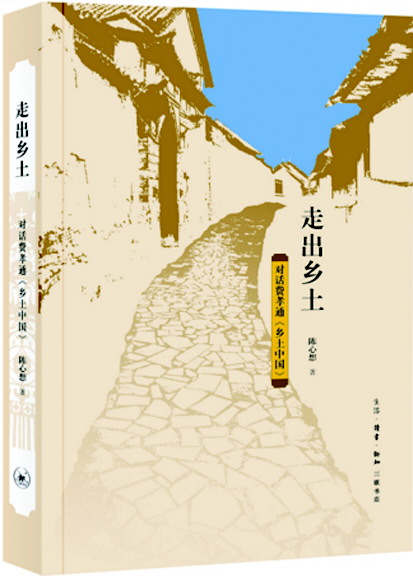
《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
陈心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郑也夫
少年时代身处文化沙漠的学人,初读费孝通民国时代的作品,每每震惊和钦佩。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读过了民国版的《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以后随着读书、阅世,费头上的光环在我心中渐渐退去。1994年写作的《读费孝通的〈皇权与绅权〉》堪称我对他的告别礼。因为读费的热情早已消退,1986年《江村经济》中译本出版,之后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江村经济》绝不下于《乡土中国》。完成前书时费28岁,后书时38岁。跨越十年的这两书实为姊妹篇。一个微观,一个宏观;一个是对某一村庄生活的面面俱到的事实勾画,一个是对传统社会秩序的融会贯通的理论思考。
两相对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定位《乡土中国》。笔者以为,《乡土中国》是一本通俗的理论著作,他形成了概念,讲出了自家的道理。通俗的理论也是理论,艰深的理论史也不是理论。而《乡土中国》是通俗理论著作中的精品。
我定义《江村经济》是经验研究、田野研究。费曾说:他做学生时就不喜欢《定县调查》式研究的肤浅。他日后的研究在两端上反其道行之,《江村经济》在深入调查一端,《乡土中国》在理论思辨一端。而二者在他那里发生了关联,没有《江村经济》和“魁阁”六年(1939—1945)的乡村研究,就不会有《乡土中国》的宏观思考。
费孝通在开弦弓村做了一个月的调查,离开村庄整理调查20天后,返回村庄补充调查10天。就是如此短时间的调查托举起这个“里程碑”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语)。第一,当然在于他天分高。第二,他是本土人,他在该县的另一村庄生活到10岁,离乡后少不了听说乡间的事情。因此调查的效率一定高于地道的外乡人。第三,他对这项调查的巨大热忱,他在调查刚刚结束后撰写的《江村通讯》中说:“虽说我是个本乡本地的人,而回去一看,哪一样不是新奇巧妙得令人要狂叫三声。这一个月紧张工作,只令人愈来愈紧张。”如此状态,不出成果都难。
《乡土中国》论述的不是社会的局部,而是整体。而他此前的主要力量是花费在一个个乡村,即社会局部上面的。在概括中,他扔掉了他判断为局部的个性,整合出各局部的共性。从局部推断整体,当然不能说不会失误,但是舍此该如何认识整体呢?不是每个研究者,甚至不是多数研究者,可以完成从局部推断整体。但是能完成“微型社会学”研究的人较多。他们的成果,为理解中国社会之整体准备了基础。况且,为理解整体做准备,只是“微型社会学”的功能之一。如果认为微观研究的功能仅限于帮助理解庞大的中国,便是头脑僵化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中。一个村庄的研究,可以直接服务于该村庄,以及同类型的村庄的改善;还可以服务于若干小专题。其功能不一而足。
费孝通作为学者与社会活动家的一生如果简单地划分,就是两段:20岁至39岁的20年;39岁至95岁的56年。
第一段共20年,几乎他的全部闪光的思想、作品都完成于这期间。以费1938年完成的《江村经济》为坐标,他仅用了八年时间。以后,他在教学、著书、时评三个领域耕耘,名声卓著,是学者兼公知。
1949年后,判若两人。他不再是学者和公知。笔者以为,从1949年至2005年费孝通的作品乏善可陈,无一部可以称作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背离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身份的一个原因,是1952年院系调整中社会学被取缔。他的专业不能做了,他只能当一名失去了自己专业的教授,讲授所谓民族学。还有就是做学术行政工作。笔者一直惊异和不解民族学院当年何以拥有那批资历和水准极高的教授群,原来是费请来的,他当然懂得各色教授的斤两。他说:“我在民族学院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找一批教授,他们不知道要找谁呀,那么我开单子要,通过中央的力量,把历史、语言两门打稳了,到现在还靠这两门。”在学术受打压,令其难酬经世济民之志时,他就真的不做学术了。与吴文藻、谢冰心合译海斯的《世界史》这样小儿科的东西,或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这样的大众读物,与其说是做学术,毋宁说是高雅地打发时光。所以他晚年曾说:哀莫大于心死,他早就放弃社会学了。
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满打满算20年的学术生涯,去掉拿到博士学位前的八年就只有12年,其中产生的思想、文字,50多年后还被阅读和称道。
他是个悲剧人物。享九五之寿,文曲星之命自戊寅(1938年)到己丑(1949年)仅一个地支数。如果费孝通的学术生命不中辍,追赶潘光旦是可以期待的。当然以其性格,胜出的不太可能是学问,而思想其实尤为宝贵。因主客观的原因,1977年以后留给费孝通的不是学者与公知的生涯。
他晚年对中国社会学是悲观的。我在《读费孝通的〈皇权与绅权〉》一文中说:
我的好友薛涌一次与我夜宿外地旅馆,晚间长谈,说及他在80年代中叶对费孝通的采访。他对我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中国再过多少年能出现一个您这样水准的社会学家?”他说:“费孝通思考了一会儿,给了我答复,你能猜出来吗?”我真的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费孝通说出来的是“50年”!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我读研究生时读过费孝通50年代之前的所有主要著作。就著作的印象,我以为他知人且自知,是这个时代的智者,他有过吴文藻、潘光旦这样的师友,他平和不偏激。因而我以为“50年”绝非他个人的自负,而是透露出他对时下的教育环境与文化氛围的深彻的悲哀。一座楼房可以在一年间盖成,一棵树木可以在十年中长成。而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失落,崇尚学术与真理的风气的消散,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来挽回呢?我想,不会有人能确定地回答出来的。
笔者经阅读费孝通步入社会学,观其一生轨迹以借鉴,念其“50年内无大学者兴”而自省。以世俗眼光看,本文或有大不敬处。但我们是学人,这里是学界。研讨一个学者的著作是对他的最高礼节,而批评是研讨的当然的组成部分。
(本文选自《走出乡土》序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