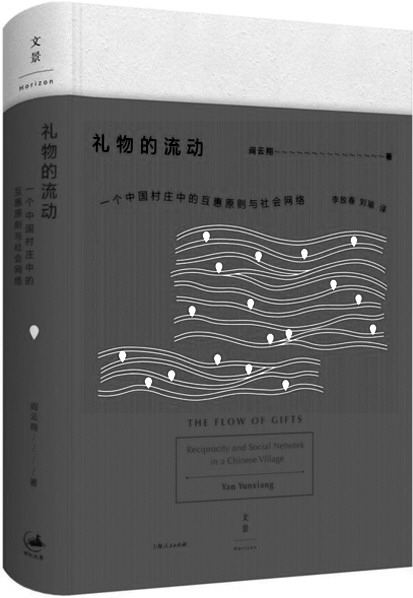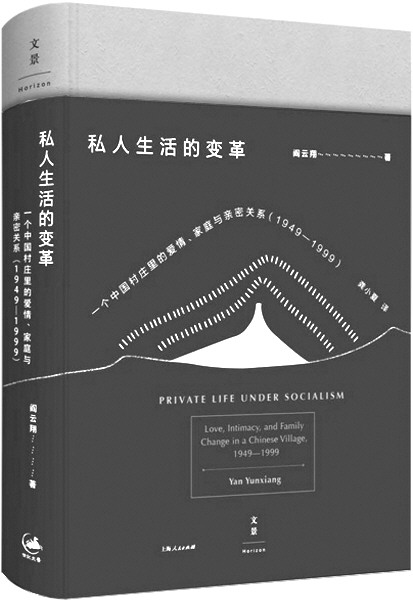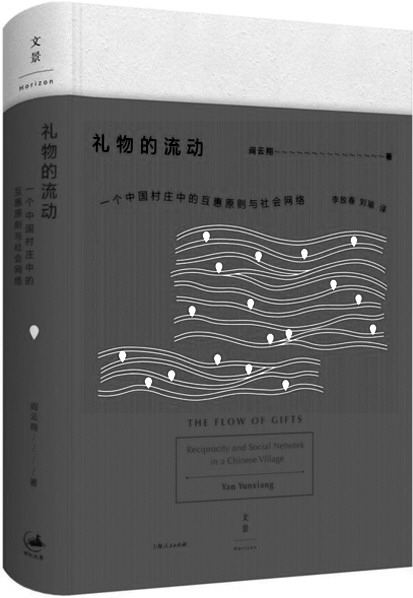
《礼物的流动》
阎云翔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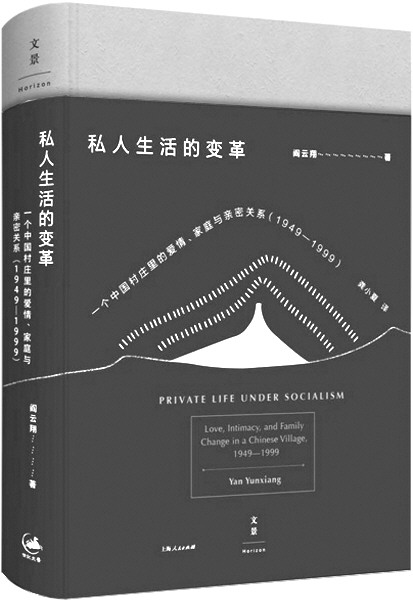
《私人生活的变革》
阎云翔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阎云翔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流浪进村的外乡人
1971年8月,17岁的阎云翔为了逃离饥饿,从山东临邑农村独闯关东。流浪到黑龙江省下岬村,在此务农7年。1978年,阎云翔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9年后到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但是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没有离开过普通人。谈及他在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的指点下,选择人类学的原因,他说:“我就想找一个学科,研究普通人的生活。”
1989年阎云翔回到中国,选取他要研究的农村原型,探讨中国社会里的文化人格问题。走了十几个村子,都没有感觉。直至来到告别11年之久的下岬村,村里人仍然记得他,他们议论他、评价他,最终认为他“没变”,仍亲热地把他当成一分子。
阎云翔认为,人类学家必须在他们所研究的社区与研究对象共同生活一年以上。而那种手持录音机和笔记本四处访谈的调查方式也是人类学家的大忌,因为“如此收集来的是零碎的、抽离于生活之流的资料”。许多人类学家终其一生只在一个或两个社区内从事研究,并因此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怀有深切的同情和强烈的道义责任,这是那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队”式的调查所无法达到的境界。
为了能够找到村民而不是学者的视角,为了能够体验而不仅仅是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阎云翔跟村民一起吃住,一起干活,聊家长里短。村里许多人都尽其所能地回答关于生活、工作、家庭、社会的各种问题,尽管那些问题似乎无穷无尽。因为谦虚或者不好意思,村民们有的会夸张,有的会说谎,但最终都说出了真心话。
礼单里的人情世界
阎云翔发现下岬村民有保存礼单的习俗,就选择“礼物交换”这样一个切入点,在1989年和1991年两次实地调查之后,完成了博士论文,随后改写成第一本著作《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离不开礼物交换,而由熟人构成的中国乡村更是一个逃不开的人情世界。“礼物交换”是人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经典的研究问题,阎云翔通过参与观察、深描等人类学方法,关注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礼物交换及其文化意义。《礼物的流动》从每个家庭都有的“礼单”出发,洞察“人情”与“面子”,以及处于关系网络中的中国社会。阎云翔说,由于对收礼的期望,下岬村民相互攀比随礼圈子的大小,而不是为送礼而送礼。单向送礼的模式也几乎涉及所有村民,有的是村民送给村干部,有的是底层干部送给上级,还有的是村民送给城里的亲戚。
尽管社会变迁,但下岬村民对礼物交换的热衷从未中断,还出现了新的随礼形式。建房仪式便是一个新近的发明。上世纪70年代,阎云翔住在村里的时候,只有近亲会给房主赠送红布等庆祝新居的礼物,还有些村民为房主提供无偿劳动。到了90年代,村民不再提供无偿劳动,即便给亲戚邻居盖房,也要领取报酬,但送礼却一直保持了下来,以便维持良好关系。
阎云翔指出,礼物交换的大量涌现,并非传统的复兴,不过是“传统再利用”。随礼的形式增多,但传统仪式却渐渐变得简单而枯燥,比如婚礼上随礼时的传统演说已经被干部的官方公证所代替,建房仪式和生日庆典中的祝词也被取消。尽管礼物交换在维持社会关系上的重要性在增强,但礼物交换中传统的、精致的礼节消失之后再没有恢复,当今的随礼越来越把重点放在礼物的物质属性而不是精神方面。
“爷爷变孙子”,“妇女上了天”
1996年,《礼物的流动》在美国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影响。阎云翔后来又多次返回下岬村进行实地调查,对村民私人生活变革持续考察12年后,完成了关于该村的另一本民族志《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在《礼物的流动》一书中,阎云翔发现在礼物交换中下岬村人已经打破了亲缘体系,以友谊为基础建立了各种个人的关系网,《私人生活的变革》则重点分析在个体化进程中村民的主体性和情感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在阎云翔看来,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次变革,都是以觉醒的个人反抗祖荫的控制为特征的,只是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知识精英的这种主张才真正传播到基层社会,并改变了千千万万工农大众的日常生活。国家在推动私人生活的转型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强化了家庭的核心作用,家庭目标从为集体生存奋斗,演化成为家庭成员提供幸福与安全感,并开始影响青年人的择偶观。
在采访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时,阎云翔不经意用了文绉绉的“择偶”一词,这个词在村里的年轻人那里成了“找对象”,体现了年轻一代的独立倾向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向往。在老人这里,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老人眼中所谓婚姻对男人来说就是“说媳妇”,对于女人则是“找婆家”。
村民的两句玩笑话概括了50年来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一是“爷爷变孙子”,二是“妇女上了天”。前一句指的是父母对儿女的权利下降,年轻一代自主性上升;后一句是因为夫妻关系的变化,妻子在家中地位上升。
由于对自由独立的私人空间的追求,建房装修成为热潮,新的住宅设计出现了明显的功能划分,卧室、客厅、厨房等区分出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当代农村青年夫妇更愿意尽早组建自己的家庭,婚后“分家”的时间在不断提前。
2001年,《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的初稿已经完成大半的时候,大量资料似乎表明“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新文化运动理想历经百年沧桑,终于在当代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阎云翔却有了新的发现——许多女青年在赢得婚姻自主权的同时,依然向未来的公婆索取高额彩礼;分家时年轻夫妇索要家庭财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份份额时大胆而坚决,但还是得依赖男方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在赡养老人方面,年轻一代在一心追求自己利益时很少顾及长辈的利益。年轻一代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及对个人义务的忽视,令阎云翔开始考虑新兴起的个人主义是否具有真正的独立意义。
作者指出,走出祖荫的个人很可能成为极端自我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这种情形在城市同样存在。尽管城市青年不会直接向父母索要高额彩礼,但很多人成年之后依然期待着父母为他们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准备一套舒适的住房,同时却不问自己为父母做了什么。媒体上常见的关于“道德滑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阎云翔看来,同样也是权利与义务失衡的问题。
被孙辈拧在一起的三代人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是阎云翔的一本论文集,也都取材于下岬村的田野调查资料,重点考察1990年代及其之后的转型期内个体的迅速崛起。尽管用了三本书来描述下岬村的社会生活,但阎云翔说,“下岬村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他在2006年和2008年对下岬村的访问发现,不同于1990年代时,年轻村民婚后不愿与父母长期同住,现在他们反而更愿意与父母组成“主干家庭”,即便分家,时间也被延迟。针对这种趋势,今年6月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阎云翔将之称为“新家庭主义”,其中包含了相当程度的旧家庭主义,同时还有某种意义上的改变。
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生活的意义寄托在下一代,以此来追求自己生活中的意义;在消费主义浪潮中成长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小孩刚刚出生或者在上幼儿园的阶段。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让自己全部生活的意义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但同时又不能放弃自己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只能依靠他们的父母来做牺牲、做奉献。于是便形成了紧密团结的三代人。即使在农村也是如此。
在新家庭主义下,父母权利在某些方面回归。2015年,阎云翔研究发现80后的离婚案例急剧增加,大部分个案中,父母起了决定性作用。“法庭上小两口坐在一起玩手机,双方父母在打离婚官司。”阎云翔分析这其中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父母在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介入过多;二是婚后双方父母考虑的都是自己孩子的幸福,而不是从小夫妻的利益考虑问题。当发生冲突的时候,80后小夫妻更容易向自己的父母求救,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中,生活的意义是向后看,人们的终极目标是光宗耀祖,把家庭、亲属纽带、宗族组织传下去,发扬光大。而在现代,祖先不再成为寄托,生活的意义寄托在孙辈上,祖父母和父母这两代人的关怀、爱和资源都向孙辈转移。但阎云翔并不觉得这意味着孙辈幸福,因为在父母和祖父母的关爱下,背后是有期待的,期待他们成为一个完美的孩子,一个完美的青年,最后是一个完美的成功人士,所有的这些投资都要回报。特别是当家庭生活的意义从祖辈向孙辈转移,原来的旧家庭主义中潜在的那一点公共性也随之消失,家庭主义成为人们唯一可以依赖的安身立命的资源,这对公共生活领域的影响令人担忧。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