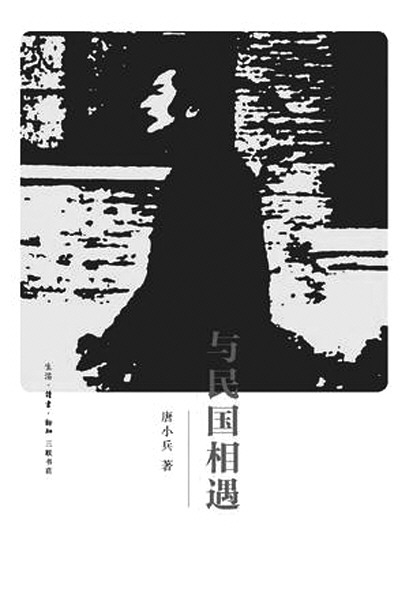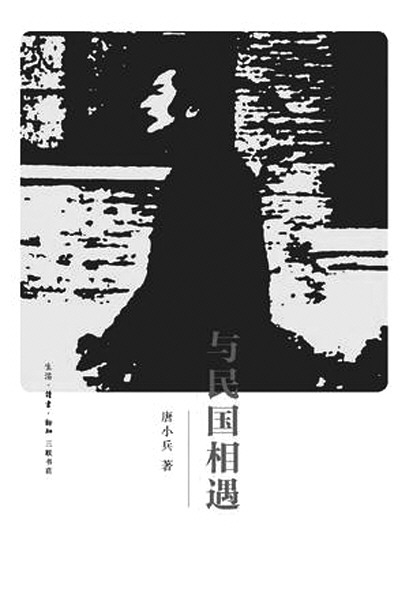
《与民国相遇》
唐小兵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近些年,学院体制内外兴起了对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热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史学博士唐小兵新近出版的《与民国相遇》,是一部从史学家的角度聚焦民国知识分子、钩沉民国往事的随笔集,并试图将历史的复杂性呈现出来。当今社会公共领域,经常会看到符号化和标签式的非左即右的思维方式。在唐小兵看来,对于复杂性的理解、认同和接纳,是一个民族走向心智成熟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而他的历史写作也是在不断清理和反思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认知和理解。
>> 历史上的民国并非“花好月圆”
上世纪90年代兴起了“民国热”写作潮,不仅历史学者在研究民国、关注民国,一大批非历史学者,如研究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的人也参与其中。很多关于民国的书,特别是文学家的一些作品中,对民国有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想象,民国成了一种典范,民国的人物、历史被想象成一个花好月圆的图景,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唐小兵的困惑。
“一味地讴歌甚至渲染民国的精气神,甚至不惜扭曲历史来迎合当下写作的价值需求。”唐小兵在《与民国相遇》“后记”中批评这种写作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的确,如果民国这般花好月圆,那么“如何能够解释民国时期的战乱流离、死难与贫困,更无从解释像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冯雪峰、王元化等这样的一时俊杰会选择‘异议者’与‘反对党’的角色”。
所谓昔年那般岁月静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在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眼中,其时普通人的遭遇就是“火光血影,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人不像人”。年逾古稀的他,不忍忆及当时的颠沛——“我逃亡的经过,没讲得很惨,再讲我自己会哭”。
武昌起义发生时,17岁的吴宓正是清华学堂的学生。在他的日记中,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接受新知识和新式教育的青年人对“革命胜利”的欢呼,而是他对乱世飘零的失落与无助:“余等既忧国势之将来及世界之变迁,复以乱耗迭传并为故乡虑,为家中虑,而又为一己生命之安危虑”。
还原历史真相,不代表完全抹杀一切。唐小兵在书中提醒:民国纵有千般不是,亦有其无从取代、不容抹杀之处,务必注意“矫枉过正也是‘佛头着粪’”。
>> 边缘化的“多余人”
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和1912年帝制崩溃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边缘化,还有部分知识分子主动自我边缘化,最后沦落为完全服从型的理论工作者,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性。唐小兵认为只有在此背景下,才可以更清晰理解近些年来的民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热潮。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自己是“高等游民”“废物”,觉得自己身上有“文人意识”是不好的。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申报》“自由谈”副刊也弥漫着对文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存在的必要性的深度怀疑。左翼文人徐懋庸在题名“读书人”的文章中说:“至于在今日以‘读书人’‘知识分子’自居,与生产劳动游离,而不以为憾,至以为自己于社会有用的人们……口说着未来社会,而连友人和敌人都分不清,然而,这些人对于社会的用处在哪里呢?”“读书人”成为那个急剧变迁时代的“多余人”,“无用”的意识深深困扰追求对国家民族有用的知识人。在一篇探讨知识分子出路的文章里,作者甚至用挖苦的语气写道:“男的不妨去当‘茶房’之类,女的不妨去当‘姨娘’之类。”
同样处在一个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历史背景中,胡适与聚集在他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传媒、社团与大学等传统社会不曾有过的空间,使文人重返社会中心。“以大学为空间,以报刊为平台,以知识为基础,创造理性的舆论来渐进地塑造公民文化。”傅斯年在与胡适通信时曾讲到:知识分子在这个动荡年代的选择应该是“与其入阁,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胡适在《政论家与政党》一文中,自诩他与其同人要做“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超然而客观地提供理性的政治评论和裁断,相信政论家影响巨大,“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在唐小兵看来,胡适以这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舍我其谁的气概自许,事实上却又是高度精英化的政论话语,在生活方式上也隔离于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
>> 用“无从裁剪的历史细节”健全公众历史记忆
钱理群曾经说过,我们历史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因此他的写作,也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表达”。唐小兵在新书里运用“无从裁剪的历史细节”,引领读者体悟难以被标签化的历史复杂性,这在钱理群看来,有“如获知音之感”。
唐小兵在书中记录了全面抗战爆发后逃难出去的沈从文与留守北平的妻子张兆和的通信。张常常抱怨丈夫明明是乡下人,在北平却总想把自己装成一个绅士,花钱大手大脚,还逼她穿高跟鞋、烫头发,不准她洗东西做事,以免把一双手弄粗糙。唐小兵将此归结为沈从文骨子里的“士大夫情结”。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既有传统士大夫文化的流风余韵,又有乡土中国生生不息的气味,沈从文很是适应与喜欢。可这种对精英知识分子文化的融入与认同,却遭到张兆和的不满和指责。
唐小兵在《曹汝霖的“五四”记忆》一文中,提到了曹汝霖晚年对北大学生“火烧赵家楼”情节的记忆。曹妻面对学生们的打打砸砸,并无惊慌,只是平静地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面对前来执勤的警察官员,惊魂甫定的曹汝霖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有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当时有报纸报道称,曹汝霖“曾经替整个北洋军队筹措到所有的军费和军火,却被青年学生把自己的房子一扫而光,竟没有一个人来替他开一枪做一臂之助!”时过境迁,曹汝霖对“五四”的评价相当温和:“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太大。学生运动……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
1947年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之际,清华女生以“妇女如何为社会贡献力量”为主题,采访一些教师配偶。陈寅恪的妻子唐筼实话实说:“妇女为家庭做出贡献也很重要……”当场遭到采访女生的批驳:作为新时代的新女性,岂可将人生的价值完全安放在家庭这个狭小天地,而依然沿袭旧时代旧女性的依附男性的人生模式?在唐小兵眼里,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教育的唐筼,早期献身中国教育,后来毅然回归家庭,在“娜拉出走”成为新时代“政治正确”选择的时候,她的做法更凸显了不降格以屈从时势和主流的独立人格。
面对民国文人的精神与生活,唐小兵意识到,只有“从这些细小的路径进入历史人物的底色与心灵”时,才可能“真正与那些覆盖在主流叙述上的空洞硬壳告别,切实触摸到隐含在历史深处的真正的伦理性困境与文明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