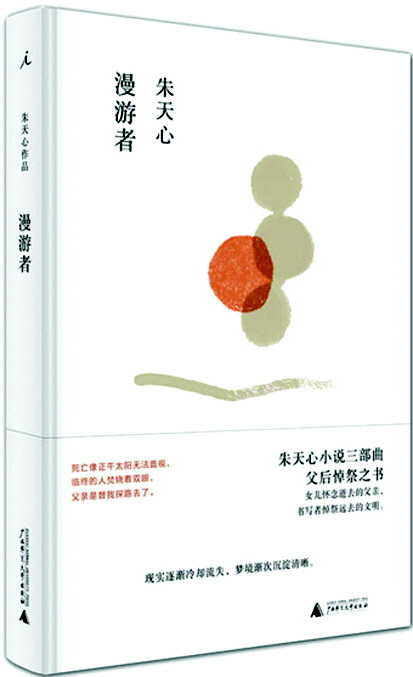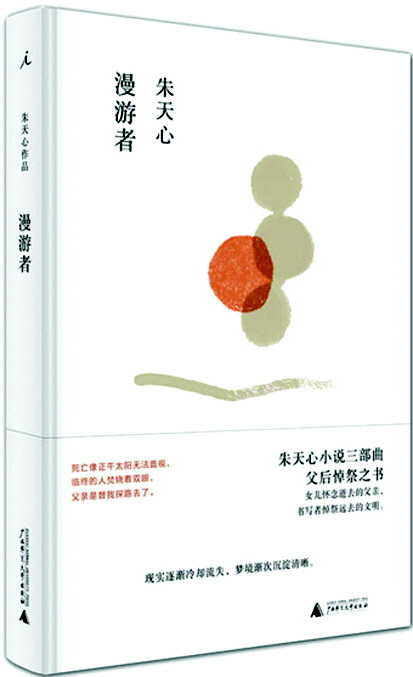
《漫游者》
朱天心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亲人的证词效力极有限,因此这只是实话实说,事关我自己的文学思索,所以非得诚实不可——朱天心的《漫游者》是我最喜欢她的一部作品,喜欢的基调是惊奇,一步一步惊奇不已,不晓得下一句又会看到什么,以及通往哪里去,更不知道她能怎么从这样的书写回来。《漫游者》是一本奇特的小说,忽然,在那一刻,几乎没预警的,朱天心写到了某个颤巍巍的异样高度,小说切线般岔了出去,或者说起飞了,这对小说书写一事颇危险,也对自己危险。
这是小说没错,但《漫游者》更像是赋。赋这个古老的文体,原是向着某个巨大而神圣的对象写的,一对一,仰头,不容(无暇在意)他人,竭尽所能。所以,或极奢华大言,或极度悲伤。
《漫游者》一书共五篇小说加一篇名为《〈华太平家传〉的作者与我》的短文,书写时间从1997年底到2000年深秋。所以说,我所谓的“那一刻”历时近三年。但是,如果我们把1997年底孤零零的《五月的蓝色月亮》暂时移开,就集中于1999年4月到2000年秋,“那一刻”凝结为世纪之交的那一年半时间——一年半,日替星移,依旧是好长的“那一刻”。
但这里有一个确确实实的时间定点,时间长河里的一个锚,一件大事,那就是朱天心的父亲、我的老师,也正是写《华太平家传》的小说家朱西甯病逝于1998年3月22日。这样,《漫游者》一书的时间图像便清清楚楚了——《漫游者》是一部死亡之书,是死亡直接驱动了这一趟书写,死亡在小说中展开了、极细节地分解开来,之中、之后、之前。
我不太想多说朱天心写《漫游者》之时之后的生活和身心样态,这确实有一点不堪回首之感,即便我以为书写成果惊人,但代价仍然太大。更重要的,我以为这是一个书写者皆当谨守的专业性根本规范,不由谁外加,也不仅仅是礼貌教养,而是原生于某个书写核心之处,直接决定着书写成果的高度、广度和好坏甚至成败——我以为,一个作家不应该多谈自己如何受苦,即便这全部是真的、刻骨铭心的;这是书写大神极冷血的一个要求。
如今,此一要求似乎越来越不被讲究,不记得了或者根本不知道。大陆的状况较令人不忍心,因为的确有太多苦恸的记忆犹鲜明才如昨日,历史有着太多凌驾于人的不公正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所以上代人写自身受苦的故事,这代人接续着写自己父母长辈的故事;台湾则让人有些不知如何是好,由于诸如此类的真实记忆稀薄到几近归零(抛弃记忆又是当前台湾的另一波潮水),受苦一事遂被逼往形而上的高处,或直接就是自己百病缠身的身体(但大多数人却又如此年轻,就像他们换篇文章所宣称的,自己年纪还小,还“来不及长大”)。几年前我去大陆评施耐庵文学奖,忍不住讲了:“书写者的悲伤超过了读者,这会让人读起来很尴尬。”
尴尬,然后就是不耐,最终则干脆冷血,十九世纪的旧俄书写显然也有此倾向,所以最终莱蒙托夫的诗这么说那些叫苦叫痛的书写者:“他痛苦或不曾痛苦,这和我有什么相干呢?”
是的,人人皆有父母,到我们这般年岁,更人人都有已离去、正离去的父母。仔细回想,这里有一个其实相当奇异的书写选择,那就是《漫游者》为什么不是散文?散文多通畅淋漓?散文可直抒胸怀,散文甚至不必讲理,事实支撑住它(所以在读到一个不合理的书中人物时,博尔赫斯极聪明地指出:“我猜这是依据真人实事写的。”)。但我以为朱天心做了很“正确”的、至少是很好的书写选择,隔了一层的小说体例,帮了她打开单子似的封闭悲伤,让她不致一直深陷进去,帮她回到世界,让这个悲伤可以被包裹、被携带、被思索。
散文里的我只有一个,书写者的我和被书写者的我合而为一,独处,集中,专断,强大如矢;而小说的我则是分离的甚至远距的,现实里的那个我(朱天心用的是‘你’,这无妨)只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站在人群之中,站在流动不居的时间大河里,自自然然地和他者相互比较、交换着悲伤,轮流地听和讲。或直接这么残忍点地说吧,父亲的辞世由此进入到人类从古至今亿亿万万如星辰如细砂的普遍死亡之中,进入大自然无可违背的规则里,人与他者的经历、话语、感受交叠在一起,其细节甚至是可交换的,如此,他者的经历、话语、感受复原了(或首次以如此清明完整、“像雨过后的晴天”的样态呈现出)意义。小说里的死亡因此是讲理的,也必须讲理。
道理,必定会替换掉(一部分的)悲伤。道理是光,射进来。
(摘自朱天心的先生唐诺为本书所写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