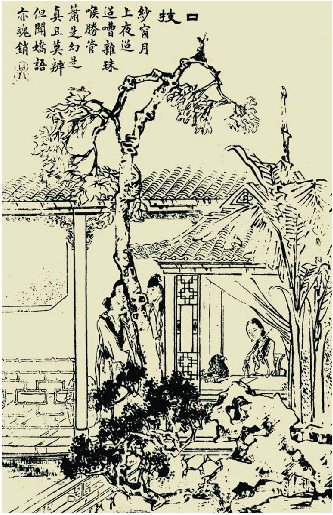
《聊斋志异》中《口技》的配图
□李学朴
翻阅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不仅被书中描写的人鬼狐妖所吸引,深感其个性鲜明、寓意深刻,而且书中那些“偶述琐闻”形式的记载也长人见识。书中对杂技艺术涉及的面很广泛,而蒲松龄文章之妙,更令人倍增兴趣。
杂技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萌芽,至汉代趋于形成,这些在《汉书·武帝记》和东汉张衡《西京赋》中都有丰富的记载。到了蒲松龄生活的清初,由于经济的繁荣,杂技艺术更是多种多样。《聊斋志异》对之做了逼真、传神的描写,让人看到那时的许多杂技已经达到了十分高超的水平。
口技,亦作“口伎”,是一种运用口腔发音技巧来模仿各种声音的杂技表演,属于传统杂技的一种形式。因其主要是模仿各种声音,故又称“像声”,又因其古时常隔壁表演,所以也称“隔壁戏”。清代张潮《虞初新志》卷一引用清什林嗣环《秋声诗自序》的记载:“京中有善口技者,会宾客大燕,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封台》也载:“像声即口技,能学百鸟音,并能作南腔北调,嬉笑怒骂,以一人而兼之,听之历历也。”
《聊斋志异》的《口技》一篇,写到一卖药女子运用高超的口技,假装真神下凡,以蛊惑病者、招徕生意的情形。文中说,她在晚上把自己独自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让众人在门窗外侧耳静听。过了一会儿,众人忽然听到里面传出九姑、六姑、四姑及三个婢女先后来到的声音,还有小儿、猫儿的声音。九姑的声音清脆响亮,六姑的声音缓慢醇厚,四姑的声音娇柔婉转,三个婢女的声音也各有特色,一个个可以分辨得清清楚楚……故事中的女子并非真的请得神仙下凡,而是一个人能模仿出七八个人说话的声音,以及猫儿叫等诸多声响。蒲松龄不仅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一场神奇的口技表演场景,也为后人保留了珍贵的风俗文化资料。
现在的口技表演,大多借助扩音器,而且拟声复杂时,多为两人合作,从内容讲,大多是模拟动物或物体发出的声音。但在《聊斋志异》的《口技》一篇中,这个卖药的年轻女子却主要模拟各种不同人的声音,而且仅仅隔一条帘子,靠一张嘴就能完成。难怪有人赞叹说“一女子之口能为九姑之声,六姑、四姑之声,三婢、小儿之声。时而窃窃语,时而絮絮语,时而乱言,时而笑,时而哗。且参差并作,喧繁满室,俱能清越娇婉,使听者信其神而不疑,购其方而恐失。富家则千金不失,贫士亦三顾弗顾,术盖奇哉!”大约明末清初,口技很是流行,精于此道以谋生者不在少数吧!
蒲松龄在讲完这个女子的故事后,又引述王心逸的见闻,说当时北京有一个少年,“曼声度曲,并无乐器,惟以一指捺颊际,且捺且讴;听之铿铿,与弦索无异”,以口技模拟乐器演奏乐曲,这也可以算得是口技中的一个独特“流派”。《虞初新志》则描述了一个口技艺人模拟一家人晚上的生活情景及街坊失火的情景,也是活灵活现,以至于听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可见,其技艺已经达到以假乱真的境地。
中国戏法的历史颇为悠久,据汉代张衡《西京赋》载,远在汉代就有吞刀、吐火、画地成川等节目。到了宋代称之为“藏挟技”,明清称“戏法”或“戏术”,今多称魔术或杂技。
《聊斋志异》中的《戏术》两则,一则是讲“桶戏”:有桶戏者,桶可容升;无底,中空,亦如俗戏。戏人以二席置街上,持一升入桶中,即有白米满升,倾注席上;又取又倾,顷刻两席皆满。然后一一量入,毕而举之,犹空桶,奇在多也。从无底空桶中变出白米。这已有魔术意味,在今天的杂技艺术中也还保留类似节目。不同的是,今天这类节目虽也有东西“层出不穷”,但多是纸、帛之类,不像这里所写的白米。另一则写得更为神奇,说李见田一夜之间将未出窑的六十多只大甕搬到离窑场三里多远的地方,而老板请人运回时,却整整花了三天时间。这个故事似乎是夸张地写杂技艺术中的“大力士”了。
有意思的是,《聊斋志异》中还描写了一则外国杂技的故事。《番僧》一篇写两个从西域来的和尚,晚上向中国人表演他们的“奇术”:一个能把“高才盈尺,玲珑可爱”的掌中小塔,投掷到“壁上最高处”的“小龛”中,使它“矗然端立,无少偏奇”,而用手一招,又会落回到自己的手掌中。另一个更妙,一个西域和尚光着胳膊,能把左臂伸长六七尺,而右臂完全收缩掉,接着又把右臂伸长六七尺,而左臂完全收缩掉。这里写的两个外国僧人一个是掷功过硬,一个则是软功,都近似于武术和气功之道。
杂耍,一般解释为杂技,有时亦兼指曲艺。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虹桥录下》中写道:“杂耍之技,来自四方,集于堤上。如立竿百仞,建帜于颠,一人盘空拔帜,如猱升木,谓之竿戏。长剑直插喉嗉,谓之饮剑。”震钧《天咫偶闻》卷七中说:“余髫年时,如泰华轩、景泰轩、地安门之乐春芳,皆有杂爨,京师俗称杂耍,其剧多鱼龙曼衍、吐火吞刀及平话、嘌唱之类。”这里说的不是由人演出,而是由动物演出的另类杂技,比如《聊斋志异》中出现的鸟语、蛙曲、鼠戏、驯蛇等。
禽言不但为诗人写入诗中,小说家也把它写进小说里,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九的《鸟语》,和宣鼎《夜雨秋灯录》卷七的《谏鸟》。《鸟语》写了一个邑令因贪污而丢官的故事,其中不时以禽言穿插,而各种禽言的声音都酷似禽类原来的叫声。如鹂鸟的叫声是:“大火难救,可怕!”皂花雀的叫声是:“初六养之,初六养之,十四、十六殇之!”鸭的叫声是:“罢罢!偏向他!”杜宇的叫声是:“丢官而去!”拟声非常精确,而且富于幽默感。
驯兽也是杂技中的一个重要项目,现在多为驯虎、驯熊、驯狗之类,在《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则多是驯蛇、驯鼠、驯蛙之类,如《蛙曲》描写的:“……一人作剧于市。携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细杖敲其首,辄哇然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宫商词曲,了了可辨”。
《聊斋志异》的《鼠戏》一篇中说,“一人在长安市上卖鼠戏,背负一囊,中蓄小鼠十余头。每于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俨如戏楼状。乃拍鼓板,唱古杂剧。歌声甫动,则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装服,自背登楼,人立而舞。男女悲欢,悉合剧中关目。” 青蛙善鸣,就训练它来“唱歌”,老鼠机灵,则训练它来跳舞,这是民间艺人按照不同动物特点而施行的训练项目。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一“蛇人”条,写到职业驯蛇人的情况,说:“东郡某甲,以弄蛇为业。尝畜驯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大青’,小曰‘二青’。二青额有赤点,尤灵驯,盘旋无不如意。蛇人受之,异于他蛇。”从“盘旋无不如意”一语,可以揣摩蛇戏表演炉火纯青的程度,文中还写到蛇人“炫技四方,获利无算”,文中又说:“大抵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为率,大则过重,辄便更易。”
《聊斋志异》卷六又有“豢蛇”一条,记泗水山中有道士驯蛇,大蛇“粗十余围”,小蛇“如盎盏者”,都能听从道士呼叱。道士说:“此平时所豢养。有我在,不妨,所患客自遇之耳。”裴铏《传奇》记茅山道士能“召蛇”,王士祯《分甘余话》讲述了真武庙道士遇“听经蛇”。
《聊斋志异》中的《蛇人》一篇虽是寓言,但却别有寄托,所写“东郡某甲”弄蛇、驯蛇的艺术也是很高明的:可以将蛇训练得通灵性,“盘旋无不如意”“旋折辄中规矩”,并且放出之后,还能自己回来。现在看起来,这也并非是信口胡编,而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动物能“认”人,并且能与人产生一定的“感情交流”,早已被科学证明了。
 Q02版:今日青岛·城事
Q02版:今日青岛·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