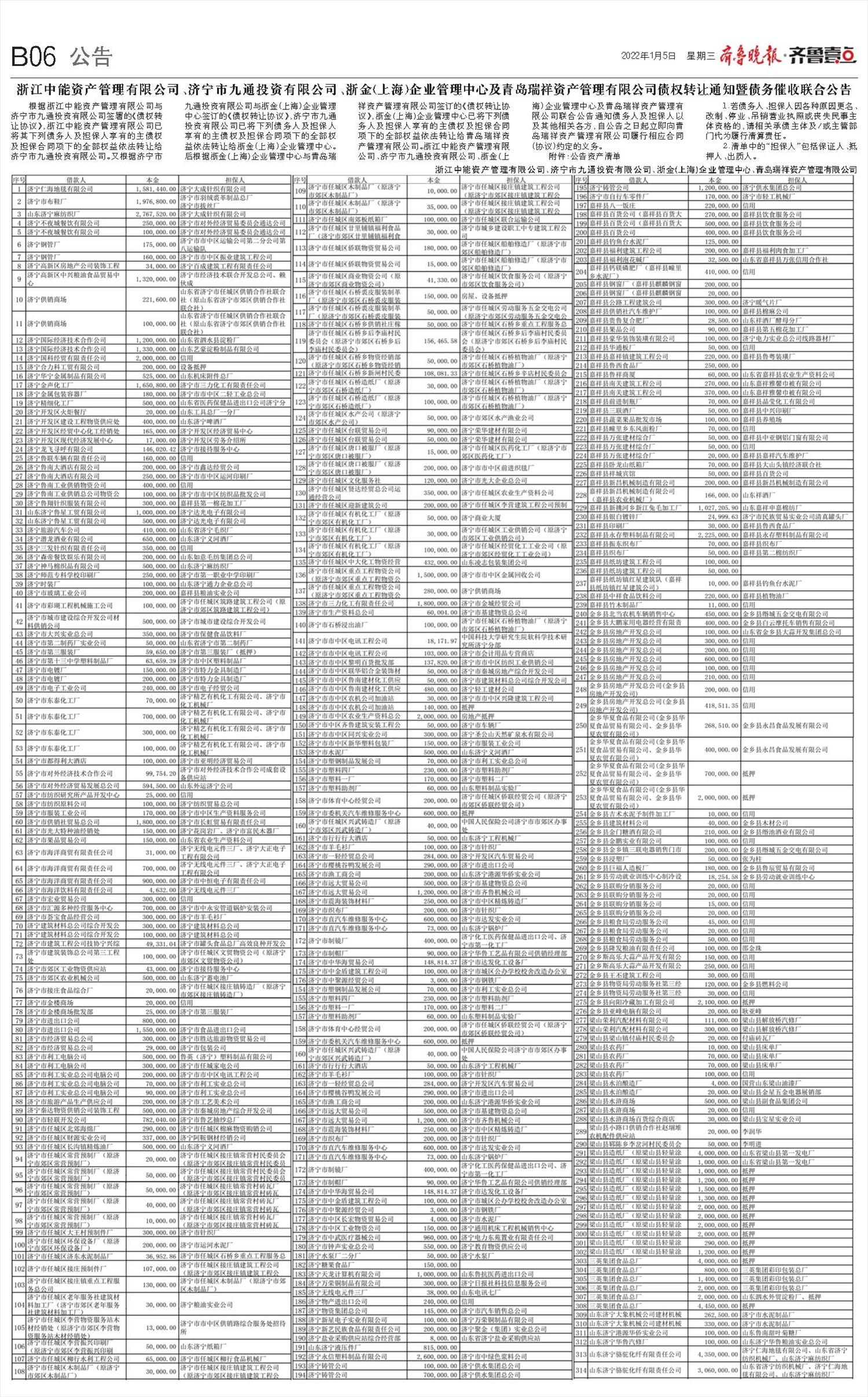□董晓康
人的一生中到底能经历多少场风霜雨雪、多少次花开花谢、多少回月圆月缺?恐怕没有谁会刻意记载这些,因为同样的风霜雨雪里未必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花开花谢际未必有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月圆月缺时未必有同样的故事。
时光流逝,无非是白天追赶黑夜,黑夜反过来再追赶白天。在这白与黑、黑与白的交替中,无数的人、无数的事被稀释、被支离,变得模糊,变得破碎,最终剩下一片虚无。当然,也有无数的人、无数的事被沉积、被封存,变得珍贵,变得清晰,最终成为永恒。
行将不惑之年,却时常感慨自己仍有太多困惑。我想,真正不惑于人生、不惑于生活的时期,或许是在一个人的童年。因为童年时你相信自己看到的世界,也相信所有人描述给你的世界。
然而,我对自己的童年,却是近乎失忆的。
八岁那年的一个正午,我被学校突然倒下的单杠砸中额头,当时头眼鼻口都在流血,在恍惚中听到母亲“小儿嘞,你别怕”的呼喊后,我就昏过去了。后来父亲骑着自行车、母亲怀抱着我赶去医院,我的血染红了母亲的肩膀。她拎着我的一只鞋,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痛哭。
那哭声我似乎清楚地听到了,又似乎没有听到。
后来我被诊断为脑震荡。经过两个多月的调养,重新回归正常。直到好多年以后,我才惊愕地发现自己童年的记忆竟被震荡得所剩无几,仅存的碎片再也拼凑不出完整的童年经历。唯独对一个秋夜的旷野印象深刻,仿佛就在昨夜。
大约六七岁的时候,我得了一种疑似疟疾的病,一吃完饭就肚子疼,疼起来我就去找母亲,让她给我揉肚子。母亲揉完就好多了,但下顿饭后还接着疼。后来,母亲找中医给我开了几服药,在院子里垒起砖台,放上药罐,慢慢熬制,苦苦的药味趁着夜色,顺着轻烟,弥漫了整个小院。
我藏在屋里,透过窗缝看着母亲将汤药倒进一个大碗,又从地上捏了一点土撒进去,就开始喊我出去喝药。那时候我怕苦,捏着鼻子也能闻到那苦味,说什么也不肯喝。母亲拉住我的胳膊,哄着我说一仰脖子就能喝下。那时候哪能听得进去?我一边捂着嘴巴,一边使劲挣脱,跑出院子,跑进胡同,跑过屋后的池塘,跑入村北的树林,跑向秋夜的旷野,身后泛起了一溜烟尘……我小时候是极怕黑的,那一刻,一定是对那汤药的恐惧超过了对黑夜的恐惧,超过了对树林里鸹鸟怪叫的恐惧,超过了对乡野中座座坟茔的恐惧,才只顾着发疯似的跑啊跑。
但是,母亲一直在我身后发疯似的追啊追,还一直大声喊着:“小儿嘞,小儿嘞!你别跑,你别怕……”我像被老鹰追逐的小鸡一样,无法摆脱母亲的视线,最终还是被她牢牢地抓住并摁在地上。
“我让你再跑!你再跑!”母亲生气地朝我屁股上打了几巴掌。我的两条腿只顾在地上乱踢乱蹬,身子像鱼一样在母亲怀里挣扎翻腾。
过了一会儿,二姐也赶来了,她手里竟然还端着那半碗汤药,关切地对我说:“弟弟,你喝了吧,喝了病就好了。”而我只顾号啕着:“我不喝!就不喝!就不喝……”
忽然,母亲平静下来,对我说:“小儿嘞,你别怕。你看看,天上的星星都跑进这碗里了,这是一碗星星粥,星星要到你肚子里跟虫子打架,虫子不咬你的肚子,你就不会肚子疼了。”
听到这些,我就不哭闹了,认真地盯着碗里看,真的看到许多星星漂浮在碗里,一闪一闪的。“星星粥”——当时的我,竟然对母亲的这番话深信不疑,马上接过汤药碗,咕咚咕咚地喝下去,全然感觉不到什么苦味。
回家的路上,母亲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拉着二姐的手。我们走在秋天的旷野,清晰地听见虫鸣,听见鸟叫,听见风吹树叶,听见深巷的犬吠。此时,满天的星光照在乡村坎坷的小路上,也照在一个少年满是泪痕的脸颊上……
关于童年的记忆,这是我能拼凑出的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段经历。多年后,我清楚母亲所说的星星粥不过是夜空中的星星投进碗里的倒影。但是,母亲在那一刻确实是用一个善意的谎言安抚了小小少年的冲动和倔强,消除了我的恐惧。星星粥,多么美好的名字,这何尝不是母亲灵感的赐予,何尝不是母亲内心的诗意!
当然,也是多年后我才领悟到,当时母亲在我身后的一声声呼喊“小儿嘞,小儿嘞!你别跑,你别怕”,何尝不是母亲一次又一次善意的提醒,何尝不是母亲给了我黑夜里奔跑的勇气。
我是一个在秋夜的旷野里喝过星星粥的人,是再也不会惧怕黑夜和任何苦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