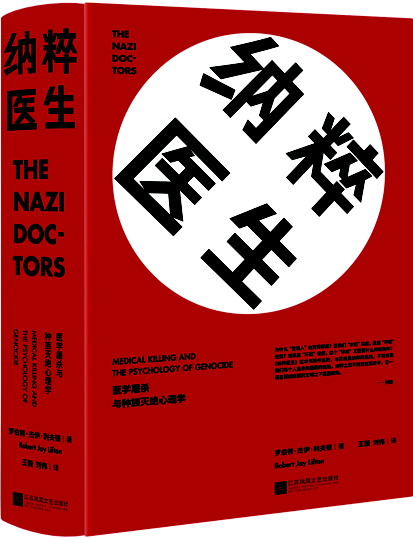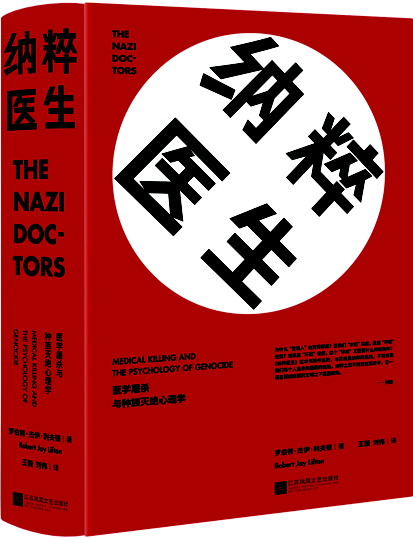
《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
[美]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近日,在《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读书分享会上,雷颐、刘苏里等学者围绕罪恶、环境与历史等话题展开讨论。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历史学者):
普通人在集体的裹挟下,带着对最完美社会的希望,一步步走向罪恶
医生应该救死扶伤、诊治病人,他们怎么会参与集中营的大屠杀?本书作者采访的二十多个纳粹医生都曾是普普通通的人,是医生,有的甚至是很好的医生。整个纳粹国家是个大机器,把零零碎碎的、或强或弱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通过种种手段,通过吸引甚至胁迫,让你逐渐加入到机器当中。一旦成为机器的零件,开始觉得有点被动,但慢慢会变成一种自觉,不知不觉执行命令。
有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青年医生,内心很矛盾,德国复兴、解决社会问题、解决失业的政策,他都很满意,但对纳粹做法很怀疑,不愿加入。后来他到了奥斯维辛。这个人就是书中的恩斯特,他是对纳粹有一定抵触的普通人,他有一个观点,很多医生也秉承这样的观点:我们首先是给人类治病,犹太人是人类的罪奴,给人类治病就得把犹太人干掉。发展到这一步,他认同了,绝大多数在集中营里的医生也没有抵触。
1995年我在《读书》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正是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站杀了很多人。奥姆真理教的教主没有什么文化,但这个教的骨干分子以科学家为主。为什么这些科学家信奉这么一个人?我看过一部片子,他的演讲极具煽动力,击中当下社会的要害,最后他说要建立最完美的社会、最完美的世界。很多人跟着一步一步地走上去了。
这本书里写到的一些医生,也相信德意志帝国代表着人类的未来,能够建成最完美的社会。社会总是不完美的,应该是渐进的、改良的,如果相信能够一下子建立完美社会,就很容易被这类思潮所裹挟。
刘苏里(知名学者):
历史已经发生,我们就朝前看,那么“前”在哪儿?“前”是什么?
德国人的反思和反省,一般给人的印象是比日本人好,日本人到现在为止在教科书问题、修宪上被看做是极右翼的回潮甚至是沉渣泛起。建议大家看看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的《德国天才》(四卷本),第一卷开篇就谈到这个问题。在德国从普通的德国人到大学教授、商人、政客,他们最近这些年一直在抱怨一件事,以至于他们最后忍无可忍地说出来了:“为什么你们只要说德国和德国人时,总是要说1939—1945年这六年时间,难道我们德国就是那六年吗?我们的德国就是大屠杀吗?”德国人在反思的事情上固然做得比日本人好,但整个世界到今天为止还叨叨这件事,他们心里有点不舒服。
我知道有很多人讨厌重提历史,更讨厌所谓反思历史,以至于把重提历史、反思历史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很多民众也有这样的看法:历史已经发生过一遍了,我们就朝前看。那么“前”在哪儿?“前”是什么?历史在德国被重复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德国人已经厌烦了,但世界没有忘记这一段而在不断重复。
建筑一个大厦要有诸多条件,怎么那么巧地在某一个时间段里、在某一个地域建起这样的大厦——第三帝国?奥斯维辛是一个小号的第三帝国,有非常确定的建立时间、确定的建立目的、确定的指挥系统,有确定的任务、实施任务的步骤,以及组成社会所有相关的条件。大厦是怎么建成的?《纳粹医生》可以给我们启示——温水煮青蛙。33℃的时候大家活得很开心,努力工作,结婚生子,是普普通通的人,甚至是普普通通的好人;到33.5℃时,只有0.5℃的变化,没有太多感觉;奥斯维辛建成时相当于水温60℃。《纳粹医生》有非常多的细节告诉我们如何从33.5℃变成60℃,从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甚至好爷爷的状态,变成一个对杀人、瞬间杀人、瞬间杀很多人、用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杀很多人而感到麻木和冷漠的人。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我去过两次,圆形追思堂正面墙上刻了一段话——“仔细守护你自己和你的灵魂,以防忘记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你应该让你的孩子及他们的后代知道这些事情。”光你自己看见、记住还不行,还得让你的后代、你后代的后代记住这些事情。
(本文为发言实录节选,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