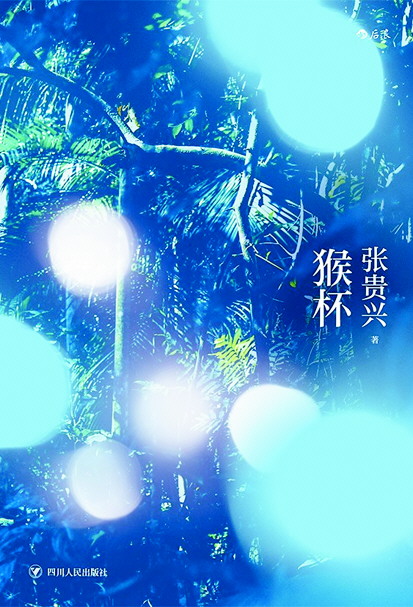
《猴杯》
张贵兴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张贵兴
故乡罗东,开荒前是长尾猴老巢,就像附近的猪芭,开荒前是野猪窝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爆发,胡椒价格飙涨,母亲在老家西南方栽了一座胡椒园。六十年代椒价暴跌后,椒园荒草丛生,回到垦荒时期的山芭模样。中学时期用一把大镰刀在椒园里除草,惊见一片芒草丛和灌木丛中,攀缘着十多株葱绿的猪笼草捕虫瓶,大小恰似西方人爱啃的热狗。椒园荒废后,季候风和鸟类带来了树籽,红毛丹、杨桃树、番石榴、桃金娘、山猪枷,四处滋长。那几株猪笼草,可能已在椒园蔓延了十多年。
猪笼草,热带肉食植物,俗称“猴杯”,正式名称“忘忧草”。
捕虫瓶里的汁液,清凉可口,猴子爱喝,故称猴杯。红毛猩猩喝时,为了不搅散瓶底的虫骸,斯文秀气,好似英国淑女细啜浸泡着柠檬片的红茶。
在贫瘠的、酸性的、缺氮的、寸草不生的荒地中,猪笼草总是第一批滋长的植物。猪笼草需要氮素制造蛋白质,不慎落入猪笼草瓶子里的猎物提供了最佳的蛋白质。
猪笼草溢出的香气,吸引了蜜蜂、蝴蝶、蚂蚁、苍蝇、蟋蟀、蜂鸟和各种昆虫,它们是猪笼草的美食(巨大的猪笼草瓶子可以溺毙老鼠和小猴子),也是植物的播种者。植物学家估计,近七十种动物共生或寄生猪笼草中,包括凶猛的掠食性蜘蛛和螃蟹。
胡椒园曾经盘踞着老家,在高脚屋、鸡寮鸭舍和人迹压制下,莽丛绝迹。老家迁往旁边一块低洼地后,废弃的家园被莽丛占据。莽丛被一把火烧毁后,种了胡椒。胡椒园荒废后,莽丛再度铺天盖地。莽丛蔓延着灌木丛和芒草丛,野生着奇花异草,包括猪笼草。
故乡从前鸟不生蛋。鸟不生蛋的好处是原始野性,像一个不谙世事、大字不识的朴素美女。
鸟生蛋的坏处是糟蹋艳俗,像一个割了双眼皮、隆了鼻、削尖了下巴、拉了皮、植了盐水袋或果冻硅胶、定期注射肉毒杆菌的妖女。
故乡现在鸟生蛋了。建筑商廉价买下那片胡椒园和猪笼草的荒地,盖起了水泥洋房,陌生的外地人大举进驻,虽然他们花了钱,拥有合法的房契和地契,总觉得他们像小偷,愣头呆脑的洋房就像贼寨。老家的四周,甚至出现了大盗似的大型购物场,流寇似的咖啡馆、餐厅和公司行号更不消说了。政客和大官更是以枭雄的姿态和征服者的暴戾,割据那片飞禽走兽曾经的福地。
午夜梦回,故乡面貌模糊神秘。
只有骑着那片飞行的丛林,像坐在飞毡上,才可能回到记忆中的故乡,就像借着东北和西南季候风往返唐山和南洋的祖先。他们搭乘的是帆船,其实是乘风而来。
记忆中的故乡,是一片飞行的、无处着床和不存在的荒原。在绵延黏稠的记忆中,被我写成不好看的小说,凑成几本卑微的小书。
《猴杯》是其中一块飞毡。
新版的《猴杯》,我做了一些改动,删去了累赘的叙述,就像帮一个脏兮兮的孩子搓泥垢、修指甲、理发,恢复较清晰的面貌。
二十年前写《猴杯》前,心里已潜伏着一个结局。接近完稿时,觉得这个结局太惊悚了。我压抑着情绪,没有让这个结局浮上台面来。二十年后重读,发觉种种铺排和暗示,都指向那个结局。它像种子生根发芽、遍地开花,我却放了一把野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