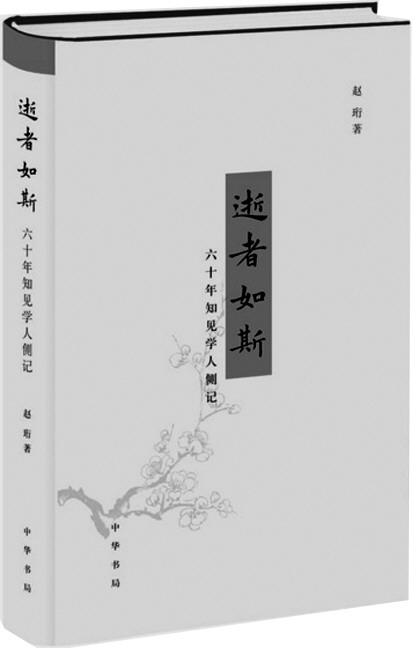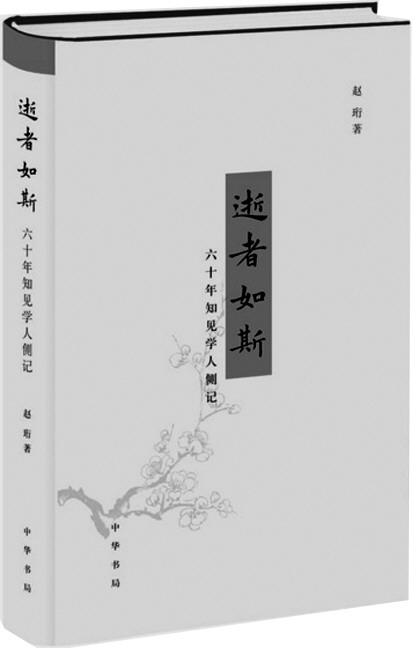
《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
赵珩 著
中华书局

启功

王世襄

朱家溍

陈梦家
启功、王世襄、朱家溍、陈梦家、史树青……六十年来,由于家世的原因与工作的关系,赵珩与这些具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老辈文化人、学者先后结识,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直至他们离世。赵珩将一腔文化乡愁收入《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书中,记录下老一辈学人的德行与风采。“逝者如斯”,是生者对于逝者的怀念,同时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当代文化史。
>> 王世襄清晨六点半拎着冬瓜串门
赵珩曾祖赵尔丰是清廷大吏,曾伯祖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父亲赵守俨执掌中华书局多年,主持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可谓书香世家。赵家的友朋宾客,多是有着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老辈文化人、学者。赵珩自幼浸润其中,渐渐地与诸多文化大家成了“忘年交”。
1986年,为了约稿,赵珩初次拜访王世襄,不经意间说起赵家上世纪50年代买的一个明代橱柜“气死猫”(一种储存食物的窗棂状橱柜,能使猫看到橱柜里的食物却吃不到,故此得名)。王世襄念念不忘,有天清早六点半就登门造访,手上还拎着从菜市场买来的大冬瓜:“我想看看您家那个‘气死猫’。”王世襄一生钟爱木器家具,如此执着,正是他深情真气之所在。
书法家启功与赵珩的父亲赵守俨同是受业于辅仁大学陈援庵门下,少年时代又都随戴绥之学习古文,二人一直以师兄相称。1971年春,赵守俨负责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工作,提出借调启功参与这项工作,启功借此摆脱了“文革”中的逆境。上世纪80年代后,启功名气越来越大,向他求字画的人络绎不绝。不少人知道赵守俨与启功有着二十多年的交往,托赵守俨向启功求字求画,但都被赵守俨回绝,理由是“不能给启先生添麻烦”。赵守俨未曾张口向启功要过字画,仅保存着一帧1974年启功送给他的扇面。上世纪90年代,赵守俨因肺癌住院,启功主动为他的主治医生写了字、画了画儿,为的是使他得到更好的治疗。由此可见启功之重情义。
文物专家、清史专家朱家溍住在简陋破旧的蜗居里,养了几只脏兮兮的猫,任凭它们在身上蹿上跳下,还在屋门下挖了个窟窿,方便野猫出入。然而朱家溍却将价值上亿的家藏碑帖、家具、书画、古籍悉数捐献给国家。很多人不理解朱家溍的做法,以朱家溍所捐献的文物而论,“随便拿出几件来,买几处豪宅也是绰绰有余的”。而赵珩从未听朱家溍说过这件东西值多少钱、那件东西值多少钱,“在他的眼里,文物只有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上世纪80年代,朱家溍曾应邀担任过几部影视剧的顾问,但拍出来的作品并没有按照他的要求还原历史,从此拒绝担任顾问工作,也极少参与文物鉴定类的活动,“他总是把自己的心捧得高高的”。
>> “翠微校史”的理想生活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是中国学术史和出版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历时近20年。因为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史书,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作时辍,影响工作的进度和质量。1963年,经中宣部批准,把承担点校的有关同志借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其中就有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
赵珩的父亲赵守俨自始至终参与并负责组织协调工作。1963年冬,专家先后到京,住进了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西北楼三号门,开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他们虽在大食堂吃三顿饭,但都是吃小灶。赵珩去食堂打饭,经常看到他们围坐在大圆饭桌前吃饭,鸡鸭鱼肉每顿都有,还经常能吃到外面买不到的大黄鱼、海参、对虾,这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很高的规格了。工作条件也好,人各一室,每人就在自己寝室工作,对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加规定。专家的生活习惯不同,有的睡得很晚,有的起得很早,有的习惯夜间工作,赵珩经常看到三号门的灯光彻夜亮着。
当年赵珩只有14岁,家住翠微路的机关宿舍里,与参加点校的学者们朝夕相见。虽然年幼的他对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不完全清楚,但对专家们的音容笑貌有着深刻印象。
那段时间,赵守俨的工作非常紧张,经常工作到深夜,几乎没有星期天。赵珩记得每个周日上午都有老先生到家里来,跟父亲谈点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其中来的最多的人就有王仲荦。王仲荦是章太炎晚年收的弟子,主持点校南朝五部史书,陆陆续续为点校二十四史工作了10年。他与负责北朝四部史书的唐长孺并称“南王北唐”,是影响卓著的史学家,但在赵珩的印象中,他总是“笑嘻嘻的,说话细声细气”,谦和慈爱,没有一点学术权威的架子。
卢振华负责点校《南史》和《梁书》。他家有个比赵珩小两岁的男孩,寒暑假常从济南到北京来看他,他也很宠爱儿子,有求必应。卢振华很少去赵家,但有一次特地为儿子买自行车的事登门造访,打听哪里能弄到自行车票,买二六的还是买二八的,买飞鸽的还是买永久的。卢先生一口湖南话,总是将二六自行车的“二六”读作“而流”,调皮的赵珩也学他说话,将二六自行车叫“而流”,成了家中的“典故”。
1966年,负责点校《金史》的傅乐焕投水自尽后,山东大学也来电要求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回校参加运动,自此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被迫中断。
>> “老饕”追逐美食又不失其雅
真正有学问的好吃之人,多半生活态度比较豁达、乐观,且具内秀。这种品格在王世襄、朱家溍、汪曾祺等人身上都可以见到。而许多人了解赵珩,是因为他在2001年出版的《老饕漫笔》,这本书使得赵珩跻身于唐鲁孙、逯耀东、王敦煌等美食文化作家之列。此后,赵珩又相继出版了《彀外谭屑》《旧时风物》《老饕续笔》等。
爱好美食的赵珩经常在家中请客,绝不敷衍。出入赵家餐厅的,不是文化收藏界的名人,便是学术界的朋友。有一年,赵珩请丁聪夫妇和黄苗子夫妇在家中吃饭,备了几个家中的拿手菜,如干贝萝卜球、清炒鳝丝、蟹粉狮子头、金钱虾饼、干炸响铃、南乳方肉等。92岁的黄苗子和88岁的丁聪吃得十分高兴,每人竟吃了两大块南乳方肉。
黄永年对赵家的饭菜也赞不绝口,跟友人多次提及,“比多少星级饭店要好出数倍”。赵家“菜好”“饮食精致”的声名远扬,不能不说黄永年是“始作俑者”。
除了家宴,赵珩常自制美食送给朋友。赵家食单上的点心“核桃酪”“八宝饭”等,每年都要做很多送人。朋友之间还经常交流品尝美食的好去处。赵珩记得王世襄曾专门打电话告诉他父亲,东直门外十字坡开了一家点心铺,叫做荟萃园,汇集了旧京许多老字号的传统点心。父亲说,“王世襄的话是不会错的。”果真,那时荟萃园刚刚开张,确实很地道,像奶油萨其玛、翻毛月饼、奶油棋子儿之类,都很不错。
>> 老辈文化人的学问不是“玩出来”的
尽管赵珩一再自谦赵家“算不得望族”,“比较寒素”,但稍具近现代史知识的人都会承认,赵家在近现代史上拥有特殊的地位。而赵珩却是以“名士”、“玩家”的名头自京城传遍全国。
“文革”年代,赵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这段时间,赵珩安安静静地在家里读自己喜欢的书,听音乐,还画油画,至今,家中还保存着他在1967年临摹的油画名作《吃葡萄和甜瓜的孩子》。1973年除夕夜颇显冷清,赵珩拿出笔墨纸砚画钟馗,母亲为画面补景,父亲则题了一首诗,留下了那个春节永恒而特殊的记忆。学生“大串联”开始以后,他弄了一张串联证,一个人出去游山玩水,为的是在“读万卷书”之后“行万里路”。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父亲赵守俨不希望儿子赵珩再去搞文史,而是希望学点儿经世致用之学,比如学医。后来赵珩真的当了大夫,却不喜欢,最后还是做文史,调到出版社工作。
赵珩爱好碑帖、书画、京戏、烹饪,也格外敬仰那些博通的学者。
考古学家陈梦家除了做研究工作,还有很多兴趣爱好。他是新月派诗歌的后起之秀,同时期的还有方玮德、卞之琳等,他能把西洋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美融为一体。王世襄每逢说起明清家具收藏,必提及陈梦家。小时候赵珩去他家玩,曾见到他家有个明代的脸盆架,平时就用。陈梦家最喜欢的是看地方戏,最多时一个月看十几二十场。
朱家溍和王世襄两人是发小,除了共同的文物方面的学问之外,爱好却不相近。朱家溍喜欢戏曲,还精通书画、碑帖鉴赏;王世襄更好动,喜欢架大鹰、驯獾狗,对蟋蟀、鸽子及古琴、木器等都有独到的研究。在个性上,两个人也有很多不同之处,赵珩感觉朱家溍更为豁达。1952年开始的“三反”运动中,朱王二人都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关到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这段经历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释怀的结。王世襄到晚年都不能提起这事,一提就义愤填膺。朱家溍却能泰然自若地给赵珩讲述当时他被抓捕的经过,还诙谐地说:“走的时候给我戴上手铐,我还来了一个《战太平》中华云在采石矶被俘的亮相。”
有人说王世襄、朱家溍的学问是玩出来的,赵珩并不赞同。很多不是正途出身的学者,知识素养往往来源于长期的实践,与家庭背景、读书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都有很深的旧学功底,包括经史、文献之学,是从小训练出来的。“今天他们的价值之所以体现,不是说王世襄有什么不同,而是今天社会变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变了,人们对他有了更多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