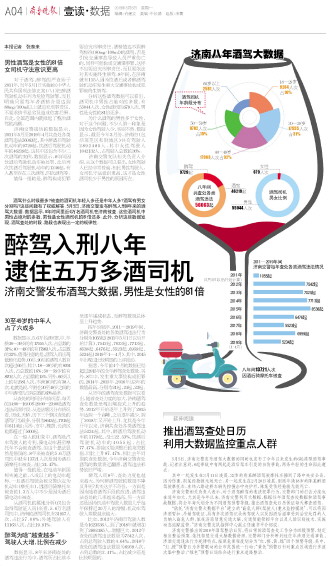□刘康宁
1984年秋,我独自乘火车到山东农学院报到。从我们小城到泰安,火车要慢吞吞跑4个多小时。等坐上学校接新生的客车,已至午后。那天的阳光相当炽烈,车窗两边闪烁着悬铃木的绿光,向北的方向,可看到黛青的泰山。在此之前,泰山在我心目中只是个概念,我对它的认识,源于那句“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现在它矗立眼前,巍峨又不失鲜活。
泰山的存在,让泰安成为极具文化底蕴的城市。在深厚的古文化包围中,俗世里的细节被粗疏化;经年的磨砺,人的性情包浆圆润,洞察世间。这种城市的气质是沉底的,平静而淳朴,是亘古千年的意思,任谁也撼之不动的。因此,描述泰安,只能从大处着眼。人间烟火也是腾腾燃烧,底下交织着蜂巢般缜密的,营营的人生。这是种难以溶入的缜密,让我感到了彻骨的孤独,就像面对着一个异常熟悉的陌生人,他的散淡的微笑让我难以招架。
游走在泰安的大街小巷,能感到平和下面隐藏戚容。周末的清晨,晨光渗透稀薄的白雾。在岱庙南门外古槐处,鸟儿在小心叽叽喳喳——仿佛不敢惊动岱庙里威严的神灵。古槐下的碑石上刻的“双龙池”几个大字,在白雾中显现出神秘,是不是碑旁石砌的深池中果真有两条龙的真身时隐时现?岱庙是古时供帝王参拜的地方。有堂皇的庙宇,威严的佛神塑像,精雕细琢的龟驮碑;遍布着蟠曲柔和、扭筋转骨的古柏。如今缭绕的香火烟气,摒弃了家国社稷的宏大意味,承载了更多具象的琐碎沉重。虽是平凡人的愿望,因在心底孕育,不停翻滚磨擦,被内心充盈的物质滋养,变得晶莹剔透,有了珍珠的质地。跪拜的人满心虔诚,肃穆的面孔微露戚容,将沉甸甸的心愿,虔诚地捧出。
近日重游泰安,从岱庙开始一路走去,循着大学时代的足迹。岱庙门外便是闹市,与我读大学时相比,反少了许多喧腾,有了曾经沧海的淡然沉静。市声虽也是笼罩性的强势,却敛住了气息,由下往上腾起在半空中,俯瞰着芸芸众生。青年路北尽头,有正在拆迁的楼房,残垣断壁被绿色网布围挡覆盖,这里曾是一家小旅馆吧?记不清了,它的戚容已然破碎,在午后微醺的阳光中沉寂。
来到母校礼堂附近,见一对夫妇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从台阶上走下来。妈妈对女孩说:这是你爸爸原来上学的地方。轻轻一句话,经年的沧桑,弹指一挥间。此时远眺泰山,轮廓未改,只是失了旧日的鲜活和层次分明的立体感,变得灰白、模糊,分明是被层层雾霾所遮掩,即便在这天气晴好的日子。不禁又老套地感叹一番:人类在得到的同时,失去了那么多美好。忽然想起,我有多久没登泰山了呢?
很久了呢!只大一时约同学登过一次泰山。隔了几十年的辛苦路回首往事,记忆不甚清晰。我们从红门处登山,沿历朝皇帝的登山御道行走,泰山的美慢慢在眼前呈现——乱石间松柏成荫,散发着清香,像一剂安神的气息。年轻气盛的我们,眼前只看到肤浅的美。在蜿蜒的石径上疾步行走,对目不暇接的碑碣石刻,扑面而来的怪松奇石,来不及细细端详,只忙着赶路了。登山只作为形式上的完成仪式,如同在青春版图插上一面小小的旗帜。漫长的岁月,风雨兼程,这面已褴褛暗淡的旗帜却一直在心头猎猎作响。
据记载,泰山山脉自西向东沿黄河南岸绵延二百多公里。“泰山安则四海皆安”,一个安字像定海神针,又像是中国画画法水墨的基调,“黑、白、浓、淡、干、湿”一路铺陈开去,任千变万化,总有个稳妥的布局,即便是留白,亦得细细推敲。